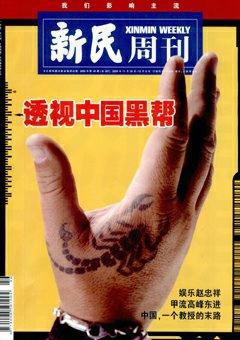“我們”如何做好群眾工作
鄧聿文
《解放日報》11月17日全文刊登了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接受媒體的聯合采訪。在我的印象中,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接受本地媒體的聯合采訪,這些年似乎是第一回。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訪談中,俞正聲沒有回避矛盾,不委過,不粉飾,少見官話、套話、正確的廢話,以及盛氣凌人的官氣、八股氣等,多是一些大實話,大白話,像是同群眾拉家常,很入心。
例如,在談到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釣魚執法”事件時,俞正聲說,此事說明“我和我們的同志們”法治意識淡薄;談到磁懸浮引起一部分群眾的強烈反應時,坦承“我們是估計不足的”。兩次都特別指明,“我們”包括“我”,這是一種謙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俞正聲在這篇訪談中,舉凡這些年上海的經濟發展和城市治理存在的問題,他都有所涉及,并且對所談到的全部問題,敢于亮明觀點。但我認為,訪談最值得人們關注之處,還是他對如何做好群眾工作的強調及其在這一問題上的真知灼見。這一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我們黨的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群眾,政府政策和措施的好壞,一個衡量標準是能否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出現了脫離群眾的危險,黨的群眾路線在一些地方和基層正在被閹割,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正在被淡化,這對黨的事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非常有害的。
如何做好群眾工作,俞正聲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要有制度性創新,用他的話說,新時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們的利益主體多元化,人們的流動性加快了。因此,不創新就不足以應對新形勢的需求。在這方面,上海進行了一些探索,以危棚簡屋的動拆遷為例,俞正聲指出,上海實行了兩次征詢的辦法。第一次征詢是動拆遷的意愿,必須絕大多數人贊成;第二次征詢是動拆遷的規則,也必須絕大部分人簽約。兩次都必須70%以上,達不到這個數字,這個地區至少3年不得動拆遷。另外,對動拆遷過程中的老上訪戶,他提出,可以聘請律師介入拆遷案件。
的確,隨著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逐漸多樣化,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紛繁復雜、突出多變,稍有處理不慎,很可能演化成群體事件。面對這種情況,政府負有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第一位的責任。但必須承認,目前我們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制度和機制還不夠健全,社會矛盾的處置力度較弱,政府花了很大成本,換來的卻可能是公信力的不斷下降。這無疑需要政府去創新化解矛盾,做好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對此,俞正聲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命題:怎么利用群眾的力量來做群眾的工作。
讓律師介入拆遷案件,實際上就是一種讓群眾教育群眾,靠社會力量解決群眾之間、群眾和政府之間各種糾紛的嘗試。政治學上,當兩種沖突的利益無法通過協商達到妥協時,就需要獨立的第三方來裁決。以前政府直接介入群眾矛盾的調解,由于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結果并不總很理想,有時反而使問題惡化。但如果讓調解主體由行業、部門主導轉向社會第三方主導,特別是讓律師和專業人士參與調解,由于他們所屬地位的中立,并具有法律和專業知識,有利于妥善處理糾紛。就此而言,引入第三方進入信訪調解過程,發揮社會力量在信訪調解中的積極作用,其實也是在鼓勵多元治理和社會自治,應該大力提倡。
上海是個大城市,世博之前有許多大型的城市建設項目,涉及到許多動拆遷,有些動拆遷的過程中涉及到法律與政府規章的沖突,使矛盾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越是這樣的項目,越是這樣的情況,越應該吸取俞正聲的這種思路,尊重法律精神,尊重各方利益,邀請獨立的第三方參與其事,避免政府與民眾的矛盾尖銳化。
另一方面,化解新時期的群眾矛盾和糾紛,我們還可使用協商民主的方式。正如俞正聲所說,新時期的特點要求更多地利用協商。現代社會只有合法的決策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才能將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而協商民主,強調在參與、討論和集體反思的過程中,尊重各種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觀點,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賦予立法和決策以合法性。它不僅重視民眾政治參與的權利,而且注重參與的過程和可操作性。從這一角度看,協商民主治理機制的存在,也有利于合理促進政府作用的發揮,避免政府作用過當,或不作為。因為,在政府和群眾的矛盾中,除極少數例外,多數都是由于政府過深地介入某個行業,損害群眾的利益所致。像房地產行業,政府卷入的程度就相當深,以致政府的很多房地產決策,不是從全社會的公共利益,而是從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出發,從而導致許多拆遷上的矛盾。
所以,要解決類似拆遷的問題和矛盾,最后還需要政府回復本位。而協商民主有助于政府的職能回歸,因為協商民主的程序化和透明性使民眾能夠有效地監督和制約政府,避免其超越責任范圍、法律界限。(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