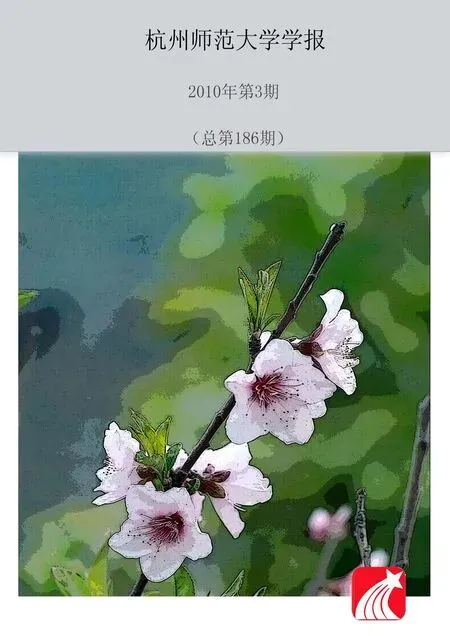重思智慧
張汝倫
(復(fù)旦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上海 200043)
雖然philisophy在古希臘文中是“愛智慧”之義,但在西方哲學(xué)中,除了古希臘哲學(xué)家還對(duì)它有所思考外,近代西方哲學(xué)家很少有人將它作為主要的思考對(duì)象。在哲學(xué)的諸研究領(lǐng)域中,有知識(shí)論,卻無智慧論。知識(shí)研究蔚為大宗,智慧卻少人問津。之所以如此,是因?yàn)閺囊婚_始,知識(shí)而不是智慧,才是西方哲學(xué)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從柏拉圖區(qū)分意見與真理開始,西方哲學(xué)的真理概念也基本是與知識(shí)有關(guān),而不是與智慧有關(guān),真理就是得到了證明的知識(shí)。到了近代,隨著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給人類帶來越來越多的福利,知識(shí)問題更是成了西方哲學(xué)的主要問題,在認(rèn)識(shí)論哲學(xué)家看來,哲學(xué)的主要功能就是研究知識(shí)的性質(zhì)、結(jié)構(gòu)、條件和可能,提供形式化的知識(shí)說明。而“知識(shí)就是力量”的說法,不僅反映了西方人對(duì)知識(shí)的理解,也反映了知識(shí)在西方思想中的霸權(quán)。
知識(shí)受到西方哲學(xué)和西方思想的極端重視,當(dāng)然不僅僅是因?yàn)樗膶?shí)用價(jià)值,各種知識(shí)不斷擴(kuò)展了人們對(duì)世界和對(duì)自己的認(rèn)識(shí),開闊人們的眼界和思路,成為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東西。此外,知識(shí)由于其客觀、普遍有效和可證實(shí)性,自然容易得到人們的信任。
近代西方的知識(shí)概念深受近代自然科學(xué)的影響,它的特點(diǎn)是追求規(guī)律性、追求確定性、追求可證實(shí)性(經(jīng)驗(yàn)或邏輯證實(shí))。知識(shí)是對(duì)一切對(duì)象的客觀認(rèn)識(shí),具有普遍有效性。只有對(duì)事物進(jìn)行高度抽象和一般化以及其他人為的技術(shù)操作得到的知識(shí),才能符合上述要求。上述知識(shí)要求也意味著知識(shí)必須是價(jià)值無涉的,即知識(shí)就是知識(shí),知識(shí)無禁區(qū),它及其應(yīng)用可能對(duì)人類生存造成什么后果,那不是知識(shí)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面,與人生有關(guān)的種種問題,也不屬知識(shí)的范圍。這就是知識(shí)的盲區(qū)。知識(shí)似乎無所不可知,卻唯獨(dú)不去思考和認(rèn)識(shí)它對(duì)人們的生活可能造成的各種后果。人們天真地認(rèn)為,知識(shí)的后果總是正面的,卻不去思考任何知識(shí)都會(huì)有的直接或間接的后果。由于將知識(shí)視為絕對(duì)正面的東西,對(duì)于知識(shí)的追求幾乎成了現(xiàn)代思想的唯一目的。其極端的結(jié)果,則是知識(shí)在造福人類的同時(shí),也給人類帶來莫大的危險(xiǎn)。例如,核裂變的知識(shí)。
在西方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知識(shí)與信仰互相制約的時(shí)代,但是隨著現(xiàn)代性的去魅過程,今天已經(jīng)不再有什么牽制知識(shí)的傳統(tǒng)力量了。人們從上天入地到心理問題都要請教專家,說明知識(shí)已然成為人類生活的絕對(duì)權(quán)威,它的影響無遠(yuǎn)弗屆,無孔不入。知識(shí)在現(xiàn)代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科學(xué)技術(shù),更是在許多人眼里將決定人類的命運(yùn)。人們越來越只知知識(shí),不知智慧,甚至以知識(shí)來代替智慧。智慧被人遺忘,至少被最不該將它遺忘的哲學(xué)家遺忘,是一個(gè)不容忽視的事實(shí)。
智慧從一開始就與知識(shí)不同,它固然不排除知識(shí),但與知識(shí)有很大的不同。在日常用法中,智慧首先指與日常生活有關(guān)的那種明智,如對(duì)生死的理解、對(duì)生命目的的反思、對(duì)行為方式的斟酌、對(duì)實(shí)踐事情的判斷和洞察以及對(duì)價(jià)值取向的決斷。蘇格拉底說“未經(jīng)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即表達(dá)了這種智慧。當(dāng)然,在東方,智慧還表示對(duì)宇宙奧秘的洞察。而在今天,人類恰恰缺乏這兩種意義上的智慧,結(jié)果是為學(xué)日益,為道日損(借用老子語,非老子原意),知識(shí)越多,智慧越少,不但生活越來越?jīng)]有方向,而且使知識(shí)成了一種威脅。
一
希臘人最初把一切知、教養(yǎng)、能力或機(jī)智稱為“智慧”,希羅多德和其他人就是在這個(gè)意義上稱有“七智”,梭倫是其中最著名者,但他既非哲學(xué)家亦非科學(xué)家,而是政治家和立法者。赫拉克利特說,“熱愛智慧者必須精通許多事情”(殘篇35)。而修昔底德則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借伯利克里的口告訴人們,智慧是怎樣的知與能:“我們愛美卻不揮霍,我們追求教育卻不溺愛。”在古希臘,智慧最初是指與直接的生活實(shí)踐有關(guān)的知與能,而非哲學(xué)理論。在古典時(shí)代,從事哲學(xué)的人會(huì)處于很大的壓力;當(dāng)時(shí)一個(gè)自由的男人值得做的事只是政治和戰(zhàn)爭,“教化”是奢侈,而不受信任的事情。傳說中泰勒斯的女仆嘲笑主人仰觀天文而失足落井,其實(shí)是當(dāng)時(shí)希臘人與一個(gè)社會(huì)最底層的人一起在嘲笑這個(gè)哲學(xué)的始祖。但是,到了畢達(dá)哥拉斯,“智慧”(sophía)就已經(jīng)專指理論知識(shí)了;畢達(dá)哥拉斯將爭名逐利與研究事物的本質(zhì)相對(duì)立。希臘人很早就開始強(qiáng)調(diào)“智慧”的沉思意義了,因此“智慧”在古希臘主要指與實(shí)踐的、尤其是政治活動(dòng)相對(duì)立的系統(tǒng)的理論活動(dòng)。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xué)中對(duì)照理論生活方式來評(píng)估政治生活方式,得出一個(gè)非常“非希臘”的結(jié)論:理論給予人完全的幸福。[1](PP.40-41)
到了希臘化時(shí)代,智慧成了生活的藝術(shù)。對(duì)于伊壁鳩魯來說,智慧就是擺脫恐懼和欲望,擺脫一切未經(jīng)思考的錯(cuò)誤想法,它是通向幸福的最可靠的指路人。人只有智慧、誠實(shí)、正義地生活,生活才會(huì)令人愉快。在斯多葛派那里,哲學(xué)具有實(shí)踐和治療的功能,它通過激發(fā)人自身的力量來治療人的靈魂,使其遵守智慧的規(guī)定。人必須努力規(guī)馴他的自然沖動(dòng)、目的和思想。塞涅卡和西塞羅一樣,都把智慧視為對(duì)神與人的事物之知。恩皮里克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就是智慧的操練,智慧是對(duì)神與人種種德性之知。對(duì)于普羅提諾來說,智慧是只有神之理性才有的知本身,它與存在同一。奧古斯丁也認(rèn)為智慧從根本上說是神才有的東西,它是從精神上把握永恒和神圣的東西。
托馬斯·阿奎那區(qū)分哲學(xué)知識(shí)與神學(xué)知識(shí),它們具有不同的出發(fā)點(diǎn)。哲學(xué)首先是從事物自身的原因得到它的論據(jù),再從那里進(jìn)到上帝的知識(shí)。哲學(xué)智慧即使也像神學(xué)智慧那樣處理神圣的問題,但它的原因不是由于神學(xué)的條理而是由于人的理性。哲學(xué)智慧與神學(xué)智慧的區(qū)分必然導(dǎo)致理性的范圍和科學(xué)知識(shí)的界限這些基本的問題。
近代西方智慧概念的重心轉(zhuǎn)到了自我認(rèn)識(shí)上,但這也起源于蘇格拉底的傳統(tǒng)。蘇格拉底要人反思自己的生活,而蒙田在其隨筆中引用西塞羅的話說:“愚者即使得到他所期望的東西還心猶未甘,而智者有了什么會(huì)心滿意足,決不再去自尋煩惱。”以此來表明人“第一件要學(xué)的事是認(rèn)識(shí)自己是什么樣的人,什么是他該做的事”[2](P.8)。他還引用歐里庇得斯的話“我討厭自己不智的智者”[2](P.124),來表示智慧首先與自己的行為有關(guān);智慧隨聰明而來。
然而,笛卡爾卻把智慧等同于知識(shí),他認(rèn)為哲學(xué)不僅研究在日常聰明意義上的智慧,而且追求對(duì)人能認(rèn)識(shí)的事物的完全知識(shí),通過純粹天生的理性對(duì)真理的認(rèn)識(shí)就是最高、最本真意義的智慧;最高的善和人類生活的完滿就在于這種智慧。但是,人類智慧的全知預(yù)設(shè)以倫理學(xué)為前提,它是智慧的最高階段,作為普遍智慧的第一規(guī)則而有效。斯賓諾莎同樣賦予智慧以道德意義,他在《神學(xué)政治論》中把所羅門作為智者的典范,說真正有智慧的人寧靜泰然地活著,不像壞人,內(nèi)心沒有一刻寧靜。[3](P.25)人真正的幸福在于智慧和對(duì)真理的認(rèn)識(shí)。
萊布尼茨把智慧定義為“一門幸福的科學(xué)”,沃爾夫以此定義為試金石來檢驗(yàn)中國的實(shí)踐哲學(xué),他認(rèn)為中國人的哲學(xué)基礎(chǔ)與他的哲學(xué)基礎(chǔ)完全一致。哲學(xué)的真正基礎(chǔ)就是與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而“中國人善于正確運(yùn)用自然的理論”[4](P.85),中國人同樣以最高的善為目的。在這篇演講的注釋中,沃爾夫還提到,萊布尼茨把智慧定義為精神的能力,它設(shè)定行為的最終目的和達(dá)到它的最可靠、最好的手段,安排中間目的的相互次序,以使它們共同作用達(dá)到最終目的。
康德把先驗(yàn)哲學(xué)的最高立場稱為“智慧學(xué)”,它完全盯著主體的實(shí)踐;但他意不在生活實(shí)踐,而是要用智慧概念來肯定追求真正的圓滿。這種追求是理性給自己的任務(wù),使自己在理論和實(shí)踐的目的中成為對(duì)象。然而,因?yàn)槔碚摾硇韵萦诙杀撤矗粋€(gè)給定的有條件者的諸條件的整體只能在物自身中遇到,但物自身只能作為現(xiàn)象被認(rèn)識(shí),這就使得實(shí)踐理性得在最高的善的名義下去尋求純粹實(shí)踐理性之對(duì)象的無條件的總體,那它作為我們理性行為的準(zhǔn)則。對(duì)于康德來說,這就是智慧學(xué),“而當(dāng)智慧學(xué)又作科學(xué)時(shí)就是固然所理解的這個(gè)詞的含義上的哲學(xué)。在他們那里,哲學(xué)曾是對(duì)至善必須有以建立的那個(gè)概念即至善必須借以獲得的那個(gè)行為的指示”。[5](P.148)康德堅(jiān)持傳統(tǒng)意義的哲學(xué)概念和智慧概念,理論思辨的基礎(chǔ)就是對(duì)智慧不停的追求,一切思辨的知識(shí)無不如此。
在康德那里,智慧學(xué)對(duì)于人來說還是太高了,因?yàn)樗⒉徽莆罩腔邸V腔壑皇窃谏系勰抢镒鳛橐磺欣碚摵偷赖?實(shí)踐)之知的最高原則。因此,康德根據(jù)傳統(tǒng),把哲學(xué)規(guī)定為“在任何時(shí)候都不會(huì)完成的對(duì)智慧的追求”。因?yàn)檎軐W(xué)仍只是人的智慧。[6](P.394)但是康德之后的德國觀念論者不再把智慧作為哲學(xué)的主導(dǎo)概念,因?yàn)橄裰x林與黑格爾等人都相信可以通過思辨來獲得絕對(duì)的系統(tǒng)知識(shí)。在黑格爾看來,智慧是屬于目的領(lǐng)域的東西,因?yàn)楹夏康牡男袨榫褪侵腔鄣男袨椋腔劬褪歉鶕?jù)普遍有效的目的行動(dòng)。智慧是上帝的力量,它表現(xiàn)為世界上的目的被理解為上帝的創(chuàng)造,它(上帝的力量)規(guī)定世界。作為“自我規(guī)定的自由力量”,智慧是精神主體性的關(guān)鍵。內(nèi)在的自我規(guī)定是由于“智慧的目的”,因?yàn)椤皟?nèi)在只是主體本身”。[7](P.13)
叔本華不滿黑格爾那里智慧的思辨化和理論化,在他看來,智慧是直覺的東西,智慧就是處世之道。真正的智慧的源泉是直觀,與直觀相比,抽象概念只是真正知識(shí)的單純影子。因此,智慧并不僅僅指理論的完善,而且也指實(shí)踐的完善。它作為處世之道無法學(xué),只能練。智慧成為真正的生活洞見,智者成為善于處世者,其優(yōu)點(diǎn)就在于完美的直觀知識(shí),因?yàn)檎_的洞見與切中肯綮的判斷來自人們把握直觀世界的方式。[6](P.394)對(duì)于叔本華來說,哲學(xué)是一種生活智慧的形式,是一種讓生活盡可能舒適和幸福的藝術(shù)。
然而,從尼采開始,一些哲學(xué)家在摒棄傳統(tǒng)“愛智慧”意義上的哲學(xué)的同時(shí),也不再將智慧作為自己思想的主題,而是將它作為負(fù)面的東西來對(duì)待(如維特根斯坦)。但也有西方哲學(xué)家不同意那種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而是主張如果因?yàn)檎軐W(xué)過于成為作為普遍科學(xué)的理論而將它摒棄的話,那么恰恰應(yīng)該恢復(fù)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地位(如古代哲學(xué)所昭示我們的那樣),而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xué),除了練習(xí)智慧外,豈有他哉?
西方哲學(xué)家對(duì)智慧的論述盡管有種種不同,但我們?nèi)匀豢梢哉f,“智慧”在西方哲學(xué)中主要有兩個(gè)意思:一是指總體性知識(shí),既完滿的知或全知;再就是智慧總是與人類的生活實(shí)踐有關(guān),是對(duì)于實(shí)踐和指導(dǎo)實(shí)踐的智慧,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倫理性,與道德有關(guān)。
二
在中國哲學(xué)中,“智慧”二字很早就出現(xiàn)了。《墨子·尚賢》:“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孟子·公孫丑下》:“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智慧”也寫作“智惠”,如《荀子·正論》:“天子者……道德純備,智惠甚明。”但單獨(dú)一個(gè)“智”字也有“智慧”的意思,如《國語·晉語》:“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侯。”在古漢語中,“知”與“智”通,《釋名·釋言語》:“智,知也,無所不知也。”西方的“智慧”概念也有“一切知識(shí)”的意思;但中國哲學(xué)中的“知”卻并非對(duì)事物的純粹認(rèn)識(shí),而是多少含有“實(shí)踐”的意思在。而中國哲學(xué)知行合一的根本要求,也使得其“知”的概念與西方近代的“知識(shí)”概念不可能完全契合;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西方的“智慧”概念。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中國哲學(xué)“知”的概念就是“智慧”的意思;而只是說,中國哲學(xué)中“知”的概念,在一定的語境下可以理解為“智慧”。
在日常語言中,“智慧”有“聰明”的意思,但是作為一個(gè)哲學(xué)概念,它卻與聰明有別。主要的區(qū)別在于,它總是與人整個(g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有關(guān),帶有明顯的倫理(實(shí)踐)相關(guān)性。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仁義禮智經(jīng)常并稱,更說明了這一點(diǎn)。在儒家思想中,“智”是一個(gè)基本的德目,它決不僅僅是聰明,而是相反——大智若愚,智慧主要并不表現(xiàn)為精明能干、善于處世或知性發(fā)達(dá)、反應(yīng)敏捷。智慧不是知性理智的結(jié)晶,甚至也不是亞里士多德phronesis(實(shí)踐之知)意義上的聰慧明智,而是超理性的、直觀的根本性洞見,也是一種澄澈無比的精神狀態(tài)。
《論語》中未出現(xiàn)“智慧”一詞,但據(jù)楊伯峻的統(tǒng)計(jì),“知”字在《論語》中共出現(xiàn)了116次,其中作“智慧”義有25次。[8](P.256)據(jù)此可以說孔子有其“智慧”概念。從《論語》一些名句中,可以大致了解“智慧”對(duì)孔子而言為何物。首先,智慧不是對(duì)事物的客觀知識(shí),而是一種澄澈無比的精神狀態(tài)。知者之所以不惑,就因?yàn)樗兄爸恰保催_(dá)到了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而上智與下愚的區(qū)分,也不在于有無理性。理性是人天生的能力,只有強(qiáng)弱之別,沒有有無之分。而上智與下愚之不移,說明智慧并非人皆有之的天賦能力,而是需要艱苦努力才能達(dá)到的精神狀況和境界。
作為智慧的“知”不是知物,而是“知人”(《顏淵》)。《書》云:“知人則哲”(《皋陶謨》),“哲即智也”。[9](P.1185)“知人”不是客觀地認(rèn)識(shí)或了解某個(gè)人,而是“舉直錯(cuò)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智慧實(shí)際是一種正確行動(dòng)并使事物朝正確的方向變化發(fā)展的實(shí)踐能力,而不僅僅是正確的認(rèn)識(shí)。作為一種正確實(shí)踐的能力,智慧不是按照所謂事物的規(guī)律機(jī)械或教條地行事,而是見機(jī)行事,能根據(jù)事情的特殊性作出正確的決斷與反應(yīng),“知者樂水”(《雍也》),就是因?yàn)椤爸哌_(dá)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10](P.90)清人黃式三亦云:“水緣理而行,經(jīng)歷險(xiǎn)阻,必達(dá)平海而后已;知者通天下事之條理,無拘執(zhí),無阻窒,故樂水。”[11](P.15)智慧的實(shí)踐特征決定了“知者動(dòng)”,即有智慧者并非如許多西方哲學(xué)家所認(rèn)為的那樣,沉湎于靜觀冥想,而是不斷地有所行動(dòng)。*《爾雅·釋詁》云:“動(dòng),作也。”
但這并不意味智者是沒有原則的機(jī)會(huì)主義者;相反,“知者利仁”(《里仁》),即“利于仁而不易所守”;“利”者,“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10](P.69)智慧的所有行動(dòng)都出于仁而又為了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里仁》)。但這不是教條地盲目堅(jiān)守,“利仁者非安,非勉強(qiáng),謂明乎仁道而順達(dá)之也”。[11](P.84)在孔子和后來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智(慧)總是與道德原理(仁道)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智是道德原理的一個(gè)主要特征和要素,它是指導(dǎo)道德實(shí)踐的原則。但仁是智的先決條件,“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這就從根本上規(guī)定了智慧的道德屬性。智慧不是像理智那樣的中性能力,而首先是一種道德認(rèn)識(shí)和道德實(shí)踐的能力,它不是可以天馬行空無限發(fā)揮的東西,而是必須合乎、而不是違背仁道的原則。這從根本上將它與一般的聰明相區(qū)別。
在孔子那里就像在蘇格拉底那里一樣,智慧意味著知道和承認(rèn)知識(shí)的有限性和盲目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分明說的是與“我知我之不知”一樣的意思。有智慧的人決不會(huì)因?yàn)樽约旱男┰S知識(shí)就沾沾自喜,甚至妄自尊大,而是永遠(yuǎn)會(huì)記得,在知識(shí)之上,還有它的指導(dǎo)者——智慧。
孟子在孔子的基礎(chǔ)上對(duì)智慧作了進(jìn)一步的思考。在《孟子》中“智”字多次出現(xiàn),但并不都是作為哲學(xué)概念。孟子也在一般的“聰明才智”意義上來用這個(gè)字,如“為是其智弗若與”(《告子上》)中的“智”字,便是如此。但孟子更多的是在“智慧”的意義上來使用“智”字。他把“智”定義為“是非之心”(《告子上》),也就是判斷力。這種對(duì)“智”的理解在孔子那里就有了,只是沒有明說。朱熹在詮釋“擇不處仁,焉得知”時(shí),就把“知”釋為“是非之本心”。*“擇里而不居于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也。”(朱熹《四書集注》,第69頁)孟子說“智”是“是非之心”,明確地把智慧作為判斷力的這一維度彰顯了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作為“是非之心”的“智”只是人心的善端之一,它與仁、義、禮一起構(gòu)成了道德的基礎(chǔ)和起點(diǎn)。“智”在孟子這里同樣有明顯的道德倫理屬性,它主要與生活世界的實(shí)踐有關(guān)。智慧就是對(duì)如何生活和要怎樣生活的洞見與判斷,是對(duì)倫理秩序朗然于心,而昭告于天下:“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戴震對(duì)此種意義之“智”有精當(dāng)?shù)脑忈專骸袄碚撸熘鴰孜⒈貐^(qū)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zhì),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于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于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jiǎng)t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yè)’,若是者,智也。”(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6冊第151頁,黃山書社,1995年)(《萬章下》)倫理秩序通過智慧而得以闡明。但這并不等于說智者是如康德的主體那樣的道德的立法者。相反,智者之智就在于順天理事宜而為,不窮逞機(jī)心,“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里婁下》)。
孟子同樣認(rèn)為,智慧不是對(duì)事物的個(gè)別知識(shí),而是全知,“知者無不知也”(《盡心上》)。這當(dāng)然不是說智者具有一切知識(shí),而是說智者對(duì)于所有知識(shí)有一種總體觀,知道輕重緩急,主次先后,“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wù)也”(《盡心上》)即此之謂也。這當(dāng)然也與智慧的判斷力有關(guān)。智慧的判斷力首先與是非判斷有關(guān),“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上》),知言就體現(xiàn)了這種判斷力。但是,在孟子那里,智慧不僅僅是一種精神能力,同樣也是一種道德實(shí)踐的能力,“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公孫丑上》)則表明了這一點(diǎn)。智慧就表現(xiàn)在當(dāng)仁不讓,當(dāng)為則為。是非之心只有擴(kuò)而充之,轉(zhuǎn)化為實(shí)踐行動(dòng),才真正是智。
荀子把知分為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和役夫之知。后兩種知共同的特點(diǎn)是言不及義,行不中矩,不講是非,不論曲直。*“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荀況《荀子·性惡》)只有前兩種知才稱得上智慧,它們或“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tǒng)類一也”;或“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荀子·性惡》),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它們發(fā)出的言行,無不中規(guī)中矩,恰當(dāng)合理。“言而當(dāng),知也;默而當(dāng),亦知也。”(《荀子·非十二子》)但智不僅僅是一個(gè)言而有當(dāng)還是無當(dāng)?shù)膯栴}。荀子同樣將智視為判斷是非之能力:“是是、非非謂之知”(《荀子·修身》),它是道德心的運(yùn)用:“人主人心設(shè)焉,知其役也。”(《荀子·大略》)仁與知不能彼此取代,缺一不可:“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荀子·君道》)
在荀子那里,智慧有亞里士多德phronesis的意思:“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xiǎn),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舉而不陷也。”(《荀子·仲尼》)但智慧更是對(duì)一般事理的洞察:“知惠足使規(guī)物”(《荀子·君道》);“知有所合謂之智”(《荀子·正名》)。但這不是要以其主體性來洞察事物的秘密,替天行道;而是順天而為,“不與天爭職”,“大智在所不慮”(《荀子·天論》),“不慮”的意思不是不思考,而是不把自己的主體性強(qiáng)加于事物。近代人以為憑仗自己的理性就可以無所不為,為所欲為;而古代人卻認(rèn)為智慧正在于有所為,有所不為。但另一方面,智慧也不是讓人無所作為;而是要“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dá)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dú)夂推剑疽鈴V大,行義于天地之間”,是為“仁知之極也”(《荀子·君道》)。荀子一方面賦予智慧以洞明宇宙真理的意義;另一方面同樣堅(jiān)持它的實(shí)踐特性。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強(qiáng)調(diào)了智慧對(duì)于人生的重要意義:“莫近于仁,莫急于智。”[12](P.202)智慧為人生所急需,沒有智慧,人生就沒有正確的方向和原則,人的種種才能如遇“邪狂之心”的話,“適足大其非而甚其惡耳”。[12](P.202)人光有仁心還不夠,還必須要有是非判斷的能力,也就是“智”,才能愛其當(dāng)愛,“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愛也”。[12](P.202)董仲舒顯然也把智慧看作是判斷善惡是非的能力。智慧是正確行為的指導(dǎo),經(jīng)過智慧規(guī)劃的行為,才會(huì)有好的結(jié)果。智慧不是一般的聰明才智,而是一種整體的實(shí)踐能力,它融對(duì)事物吉兇利害的預(yù)見,對(duì)事情前因后果的洞察,行事得當(dāng),語言精練中的于一體:“智者見禍福遠(yuǎn),其知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dá),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dòng)中倫,其言常務(wù)。如是者謂之智。”[12](P.203)可以說,智慧就是得道,得生活實(shí)踐之道。
從以上對(duì)早期儒家思想家關(guān)于智慧的論述來看,智慧是實(shí)踐之道,是對(duì)人對(duì)事的整體把握與判斷,是實(shí)踐的指導(dǎo),具有明顯的倫理特征,它不是對(duì)事物的旁觀者式認(rèn)識(shí)和客觀知識(shí),而是實(shí)踐的決斷。然而,智慧也不是一般日常意義的聰明才智,那只是一種中性理智能力;智慧總是與倫理道德相關(guān),與仁義相關(guān)。智慧不是理論推理,而是超理性,但不排斥理性的價(jià)值直觀,它一方面不離仁義;另一方面總是能就特殊事情作出適時(shí)適當(dāng)?shù)臎Q斷并付之行動(dòng)。智慧的落腳點(diǎn)在生活世界,但其觀照卻在天人之際,就此而言,它與亞里士多德的phronesis也并不完全相似,因?yàn)樗▽?duì)天道的某種洞察。
三
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哲學(xué)的巨大影響,幾乎沒有什么人將智慧作為哲學(xué)思考的對(duì)象,即便是那些談?wù)摗爸袊軐W(xué)的智慧”的書,也幾乎完全不涉及智慧的主題。人們熱衷的是知識(shí)問題,或本體論問題,而不是智慧問題。在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家中,只有馮契將智慧作為哲學(xué)的主要問題加以重新提出和討論,他的主要著作就叫《智慧說三篇》。
馮契最初是在從金岳霖學(xué)哲學(xué)時(shí)萌發(fā)他對(duì)智慧問題的思索的。金岳霖在其《論道》一書的緒論中區(qū)分了知識(shí)論的態(tài)度和元學(xué)的態(tài)度,大意為“知識(shí)論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學(xué)的裁判者是整個(gè)的人。研究知識(shí)論我可以暫時(shí)忘記我是人,用客觀的、冷靜的態(tài)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學(xué)就不一樣了,我不能忘記‘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我不僅在研究對(duì)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結(jié)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滿足”。[13](P.7)馮契對(duì)此表示疑問,在他看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認(rèn)識(shí)論也不能離開“整個(gè)的人”,金岳霖的做法是把認(rèn)識(shí)和智慧截然割裂開來了,從而難以找到由知識(shí)到智慧的橋梁,也無法解決科學(xué)和人生脫節(jié)的問題。[13](P.7-8,11)從此之后,“知識(shí)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關(guān)系到底如何,便成為我一直關(guān)懷、經(jīng)常思索的問題”。[13](P.9)
盡管馮契把他的《認(rèn)識(shí)世界和認(rèn)識(shí)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部著作稱為“智慧說三篇”,但真正系統(tǒng)論述他的智慧學(xué)說的是他求學(xué)期間發(fā)表的《智慧》*該文原發(fā)表于《哲學(xué)評(píng)論》第10卷5期(1947年),《馮契文集》第九卷,第1-68頁。一文。雖然他后來對(duì)該文中“以我觀之”,知識(shí)是“以物觀之”,智慧是“以道觀之”的提法有所不滿,認(rèn)為“單純從‘觀’來區(qū)分認(rèn)識(shí)的階段,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13](P.10)但那部著作還是奠定了他智慧學(xué)說的基礎(chǔ)。
馮契是在與知識(shí)相對(duì)照的語境下來定義“智慧”的,他心目中的“智慧”有中國古代“圣智”、佛家的“般若”和希臘人“愛智”之“智”的意思,它“指一種哲理,即有關(guān)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認(rèn)識(shí),關(guān)于性與天道的理論”。[13](P.413)在馮契那里,智慧也根本不是日常意義上的所謂聰明才智,而是特指哲學(xué)智慧:“認(rèn)識(shí)天道和培養(yǎng)德性,就是哲學(xué)的智慧的目標(biāo)。”[13](P.415)實(shí)際上馮契是從元學(xué)即形而上學(xué)上來理解智慧的:“智慧由元學(xué)觀念組成”,它是“關(guān)于宇宙或無限的認(rèn)識(shí)”。[14](P.25)這個(gè)思想他其實(shí)始終也沒有改變。馮契的這個(gè)思想,雖然在傳統(tǒng)中國哲學(xué)中有其根源,卻與西方作為“愛智之學(xué)”的哲學(xué)就是形而上學(xué)的思想若合符節(jié)。
但與西方哲學(xué)家的思路不同的是,馮契把元學(xué)看作是廣義的認(rèn)識(shí)論的一部分,他認(rèn)為“廣義的認(rèn)識(shí)論不應(yīng)限于知識(shí)的理論,而且應(yīng)該研究智慧的學(xué)說,要討論‘元學(xué)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yǎng)’的問題”。[13](P.8)但是,他也承認(rèn),智慧不等于知識(shí),因?yàn)橹腔垡J(rèn)識(shí)的是天道,而“所謂天道,實(shí)在就是全體現(xiàn)實(shí)的秩序,包括無量的個(gè)體與其間所有的條理”。[14](P.29)它不是一般意義的知識(shí),因此,“無論怎樣累積,無論累積得多么豐富,知識(shí)者總是得不到智慧的”。[14](P.29)只有揚(yáng)棄知識(shí),才能獲得元學(xué)的智慧。
天道既然不屬知識(shí),就只能體會(huì)。“體會(huì)可說是動(dòng)的智慧。動(dòng)的智慧是一種非知識(shí)活動(dòng)的認(rèn)識(shí),它以體驗(yàn)得的天道為對(duì)象,以領(lǐng)會(huì)得的元學(xué)觀念為內(nèi)容。”[14](P.31)體驗(yàn)與領(lǐng)會(huì)合在一起,是為體會(huì)。“體會(huì)以玄智為體,玄智以智慧為用。……以相對(duì)的認(rèn)識(shí)能力為能,玄智無能。……以相對(duì)的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為知,智慧無知。”[14](P.46)這就是說,智慧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認(rèn)識(shí),不以一般的事物為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它是“無能之‘能’,淵然凈,廓然虛,而全體瑩徹。無知之‘知’,通天道,照萬物,而不識(shí)不知”。[14](P.46)這樣的智慧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理論,包括形而上學(xué)理論,相反,只有“超越元學(xué)理論而得到智慧,遺棄形而下者而蹈乎形而上的領(lǐng)域”。[14](P.55)然而,超越絕不是說智慧自成一體,與知識(shí)和意見老死不相往來。馮契強(qiáng)調(diào):超越不是隔絕,“智慧、知識(shí)與意見,相齊、同一與至無,雖說層次不齊、階段不同,卻并非真有楚河漢界,封鎖了不相交通。揚(yáng)棄本有保存的意義,上升本以下層為基石。爬梯子必須一級(jí)一級(jí)地爬,登高山必須一步一步地登。正如從意見發(fā)展出知識(shí),從知識(shí)可引申出智慧。”[14](P.57)智慧雖然要靠體會(huì),但卻也是從意見和知識(shí)發(fā)展而來,雖然它又是意見與知識(shí)的揚(yáng)棄。有“動(dòng)的智慧”就有“靜的智慧”,“靜的智慧”是智慧的內(nèi)容,又稱“真諦”,“真諦是作為內(nèi)容的道”。[14](P.31)但是,馮契聲明:“智慧雖有動(dòng)靜之分,內(nèi)容與對(duì)象之辨,然而本來混成,本來同一,決不能析離成數(shù)片。”[14](P.31)也就是說,智慧既是體,也是用;既是天道的發(fā)用,也是天道的表達(dá)。
晚年馮契對(duì)智慧的論述不再借用傳統(tǒng)哲學(xué)的話語,而是使用流行的主流哲學(xué)話語,但是他關(guān)于智慧的論述與早年的論述并無太大的不同。他仍然認(rèn)為智慧是對(duì)天道,即絕對(duì)和無限的認(rèn)識(shí),可是,與《智慧》中的立場不同的是,他現(xiàn)在把智慧視為關(guān)于性與天道的理論,[13](P.413)而在早期他把智慧看作是對(duì)理論的超越。同時(shí)他還強(qiáng)調(diào)了智慧是對(duì)德性的培養(yǎng),這是《智慧》所沒有涉及的問題。如果說早年馮契把智慧等同于元學(xué)的話,那么晚年馮契則把智慧等同的哲學(xué),他說:“哲學(xué)的核心是性與天道的學(xué)說,而講性與天道,不僅在于求真,而且要求窮通。哲學(xué)要求把握會(huì)通天人、物我無不通也、無不由也的道,培養(yǎng)與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哲學(xué)要窮究宇宙萬物的第一因,揭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哲學(xué)探索的是無條件的、絕對(duì)的、無限的東西。”[13](P.424)而這也正是馮契筆下智慧的任務(wù)。
馮契關(guān)于智慧的晚年定論有三:(1)智慧是關(guān)于天道、人道的根本原理的認(rèn)識(shí),是關(guān)于整體的認(rèn)識(shí),這種認(rèn)識(shí)是具體的;(2)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的表現(xiàn),也就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和個(gè)性的自由表現(xiàn);(3)從人性與天道通過感性活動(dòng)交互作用來說,轉(zhuǎn)識(shí)成智是一種理性的自覺。[13](PP.119-420)這是一個(gè)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的全過程,這個(gè)過程分為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是從知識(shí)到智慧的飛躍;另一方面是德性的自證,在德性的自證中體認(rèn)了道(天道、人道、認(rèn)識(shí)過程之道),這種自證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體在返觀中自知其明覺的理性,同時(shí)有自主而堅(jiān)定的意志,而且還因情感的升華而有自得的情操。這樣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質(zhì)力量的全面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達(dá)到了真、善、美的統(tǒng)一,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識(shí)到我與天道為一,意識(shí)到我具有一種“足乎己無待于外”的真誠的充實(shí)感,我就在相對(duì)、有限之中體認(rèn)到了絕對(duì)、無限的東西。[13](PP.45-46)
可以看出,轉(zhuǎn)識(shí)成智的關(guān)鍵在于德性的自證。雖然馮契似乎并未將德性的自證與理性自覺相等同,但他所謂理性的自覺卻離不開德性的自證。[13](P.425)沒有德性的自證,光靠思辨的綜合,是無法領(lǐng)悟到無限和絕對(duì)的,因?yàn)樗急娴木C合怎么說也是一種理性的推理性活動(dòng),而頓悟恰恰是不憑推理而產(chǎn)生的洞見。雖然馮契以思辨的綜合和德性的自證來解釋理性的自覺,實(shí)際上他依靠的更多是后者,關(guān)于理論思辨如何能產(chǎn)生轉(zhuǎn)識(shí)成智的“飛躍”他并沒有給出太多的說明。
盡管如此,馮契還是中國哲學(xué)史上第一個(gè)對(duì)智慧給予系統(tǒng)論述的哲學(xué)家,他將智慧等同于哲學(xué)和形而上學(xué),實(shí)際上建立了一個(gè)以智慧學(xué)說為核心的哲學(xué)體系,大大豐富了中國哲學(xué)關(guān)于智慧的思想。他結(jié)合中西哲學(xué)的思想資源,闡明了智慧與知識(shí)和意見的關(guān)系,論述了獲得智慧的具體過程,突出了智慧的德性特征,確立了智慧作為哲學(xué)的基本任務(wù)和目標(biāo)的地位。凡此種種,都是馮契對(duì)于人類智慧思想的重要貢獻(xiàn)。
與傳統(tǒng)中國哲學(xué)家相比,馮契智慧學(xué)說的現(xiàn)代特征十分明顯。傳統(tǒng)哲學(xué)家總是由智(慧)統(tǒng)知(識(shí));由智(慧)說知(識(shí));而馮契剛好相反,他的以知(認(rèn)識(shí))說智(慧),將智慧納入廣義的認(rèn)識(shí)論,顯然與近代西方哲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中國的影響不無關(guān)系。也由于將智慧視為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過程的最高階段,傳統(tǒng)智慧學(xué)說那種明顯的實(shí)踐特征在馮契的智慧學(xué)說中很難找到。智慧在他那里充其量與個(gè)人的品格或人格培養(yǎng)有關(guān),但他沒有論述它與人類實(shí)踐的關(guān)系,更沒有將它視為實(shí)踐的一個(gè)根本要素。因此,在馮契那里,智慧純粹是對(duì)性與天道的認(rèn)識(shí),絲毫沒有亞里士多德實(shí)踐之知的意思。雖然他也說“明智與智慧,也要應(yīng)機(jī)接物”,[14](P.66)但那也是在知識(shí)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實(shí)踐的意義上說的。由于始終強(qiáng)調(diào)智慧是認(rèn)識(shí),他最終還是將智慧定義為“關(guān)于性與天道的理論”,[13](P.413)而在早期,他還認(rèn)為必須超越元學(xué)理論才會(huì)有智慧。[14](P.55)
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xué)家那里,智慧當(dāng)然也是一種總體性、根本性的知,但這種知必須體現(xiàn)在具體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它是有智者的實(shí)踐活動(dòng)的基本要素和根本條件,是實(shí)踐之道。它不是知識(shí)與意見的揚(yáng)棄和飛躍,它與它們不存在階段性上升的關(guān)系。它是實(shí)踐的指導(dǎo)和準(zhǔn)則,可以容納知識(shí)和意見,但不是認(rèn)識(shí)發(fā)展的最終結(jié)果。智慧不是性與天道的理論,而是性與天道的發(fā)用或功能。它不僅是體會(huì),更是身體力行;不是認(rèn)識(shí),而是“行義于天地之間”;它在培養(yǎng)個(gè)人人格的同時(shí),也在建立一個(gè)仁道的世界。西方哲學(xué)家的智慧學(xué)說雖然沒有像儒家思想家那么突出智慧的實(shí)踐性,但他們更多地將智慧理解為與人的生活實(shí)踐有關(guān),而不是與理論認(rèn)識(shí)有關(guān)。智慧在中西哲學(xué)家那里強(qiáng)烈的實(shí)踐特性,在馮契那里基本消隱了。
由于將智慧理解為知識(shí),理解為理論,而不是實(shí)踐,因此,智慧在他那里也不再是一種判斷是非的力量,不再是是非之心。相反,他認(rèn)為智慧應(yīng)該“超越是非之域而抵于無是無非之境”,[14](P.55)因?yàn)槭欠沁€是相對(duì),而不是作為智慧目標(biāo)的絕對(duì)。因此,“遺是非則得元學(xué)的理論”[14](P.56)不但要遺是非,還要忘彼我,因?yàn)橛斜宋遥皠t是非隱然在。欲徹底地?zé)o是非,必須一并忘其彼我。忘彼忘我,則超越元學(xué)理論而得到智慧”。[14](P.55)是非之心不但不是智慧,而且還是智慧的障礙。馮契一直到晚年仍然堅(jiān)持這個(gè)觀點(diǎn)。[13](PP.429-432)智慧的目標(biāo)只是要達(dá)到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自覺超對(duì)待的“現(xiàn)實(shí)之流”。雖然晚年馮契強(qiáng)調(diào)智慧培養(yǎng)德性的功能,但絲毫未及智慧的判斷功能,這不能不說是他智慧學(xué)說的一個(gè)很大的缺憾。由于道家思想的影響和將智慧定位為認(rèn)識(shí),智慧作為價(jià)值判斷和是非判斷的機(jī)制被完全忽視了。
馮契由于深受道家天道思想以及現(xiàn)代西方知識(shí)論思想的影響,認(rèn)為天道或者說“世界的統(tǒng)一原理和發(fā)展原理”應(yīng)該是無對(duì)待的,也就是與價(jià)值無涉的,因?yàn)橐簧鎯r(jià)值,就是有對(duì)待而不是無對(duì)待了。但是,對(duì)于儒家思想家來說,天道體現(xiàn)了天理,這種天理的秩序和法則就是原始的公道和正義,就是最根本的仁與義。人世的公道與正義,人間的仁義,則天法地而來,人間正當(dāng)?shù)闹刃蛟醋蕴炖恚从钪姹緛淼闹刃颉V刃蚓鸵馕吨鴮?duì)待,意味著有正當(dāng)與不正當(dāng)之對(duì)待,否則就無所謂秩序。因此,對(duì)于儒家來說,天道具有倫理的意味,源于天道的人道就更不用說了。中國哲學(xué)根本的實(shí)踐性的一個(gè)主要理論根據(jù),就是這種天道觀。以洞見天道與人道的智慧就要求能在具體生活實(shí)踐中,根據(jù)所面對(duì)的特殊情況,作出有針對(duì)性的正確決定。馮契由于將智慧定位為“關(guān)于性與天道的理論”,因而他的智慧概念始終游離在具體生活實(shí)踐之上,根本不是實(shí)踐的智慧,而只是理論。
因?yàn)槿寮沂紫劝阎腔劭醋魇钦_實(shí)踐的一個(gè)要素,智慧為實(shí)踐所不可缺,是實(shí)踐的當(dāng)務(wù)之急,即董仲舒所謂“莫急于智”,所以他們一般都把智慧視為實(shí)踐的指導(dǎo),仁義的行為離開智(慧)的指點(diǎn)是不可能的。智慧不僅僅是對(duì)天理人道的洞見,更是能人的實(shí)踐行為的指導(dǎo)。馮契由于將智慧定位為認(rèn)識(shí)(知),就無法顧及它行(實(shí)踐)的相關(guān)性。
在現(xiàn)代世界,知識(shí)已經(jīng)成了一個(gè)帶有絕對(duì)正面意義的東西,人們在推崇和追求知識(shí)的同時(shí),卻沒有對(duì)現(xiàn)代知識(shí)形態(tài)和知識(shí)本身有足夠的省視。但智慧本身要求我們對(duì)知識(shí)作出批判的反思,智慧本身就暗示了知識(shí),尤其是現(xiàn)代意義的知識(shí)的盲點(diǎn)和不足。現(xiàn)代意義的知識(shí)總是局部的、專門的、條塊分割的、甚至是技術(shù)性的。現(xiàn)代知識(shí)標(biāo)榜價(jià)值無涉,只是對(duì)事物的“客觀”認(rèn)識(shí),即便是人類事務(wù),也被這種知識(shí)規(guī)范當(dāng)作“物”來研究。人生活的方式、目的、態(tài)度、質(zhì)量和意義,則完全被這種意義的知識(shí)排斥在外。人最重要的問題——如何活,不干知識(shí)的事!知識(shí)的增進(jìn)不但沒有從整體上增加人類的幸福,反而使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類生命,陷于空前的危機(jī)。
在此情況下,重新思考智慧,對(duì)人類來說就十分緊要。針對(duì)上述知識(shí)的盲點(diǎn)和弊端,的確有必要強(qiáng)調(diào)能洞見和思考性與天道的智慧,因?yàn)樗伎夹耘c天道意味著我們將整個(gè)宇宙作為一個(gè)休戚與共的有機(jī)整體來思考、來把握,而不是將它分為無數(shù)的“領(lǐng)域”和“范圍”來認(rèn)識(shí)。因?yàn)橛钪嫒f事萬物都與我們息息相關(guān),所以它不可能是一個(gè)客觀的“物件”。相反,我們對(duì)任何事物的態(tài)度和做法,都會(huì)影響人類的共同命運(yùn)。性與天道這兩個(gè)中國哲學(xué)的概念就表明,宇宙本身不是現(xiàn)代知識(shí)所理解的“自然”,而是具有原始的倫理在。理解和把握性與天道,就是理解和把握這種源始的倫理,這樣才能“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dá)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dú)夂推剑疽鈴V大,行義于天地之間”。這種既有形而上學(xué)意味,又有實(shí)踐品質(zhì)的智慧觀念,與西方的智慧概念也相去不遠(yuǎn)。
現(xiàn)代知識(shí)概念注定了只告訴我們據(jù)說是無關(guān)我們命運(yùn)的某些領(lǐng)域或某些事物的“知識(shí)”,它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只有一個(gè),就是真還是假。可是,人類不但要知道真還是假,還得知道對(duì)還是錯(cuò)、善還是惡。然而,按照韋伯的說法,知識(shí)(理性)可以告訴我們真假,但是無法告訴我們善惡對(duì)錯(cuò)。這是信仰的問題,而不是理性和知識(shí)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善惡問題上,我們只有訴諸各人的信仰,沒有別的辦法。充斥當(dāng)今世界的價(jià)值虛無主義和道德相對(duì)主義已經(jīng)表明現(xiàn)代的知識(shí)中心主義的根本缺陷和危害。在理性和信仰之外,還有智慧。智慧是兼具理性與信仰的某些特征的精神能力。它是“是非之心”,但不是像康德的理性意志或基督教的上帝那樣獨(dú)斷的道德立法者,而是性與天道的洞見者,它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能在各種特殊的情況下作出正確的是非判斷和行動(dòng)決斷。
最后,智慧也必須是如馮契所言,乃一種德性的能力。對(duì)于人類的生活實(shí)踐來說,是非判斷往往不難得出,難的是按照正確的是非判斷的結(jié)論來行動(dòng)。人類的悲劇就在于明知故犯,我們都知道什么是對(duì)(正義)的,可往往在行動(dòng)時(shí)卻選擇了錯(cuò)誤(不正義)的行動(dòng)。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之誠,為馮契的智慧學(xué)說一再強(qiáng)調(diào),[13](PP.440-445)這的確是智慧的關(guān)鍵。不能付諸實(shí)施、不能見諸
行動(dòng)的智慧其實(shí)還是知識(shí),至少無法從根本上有別于知識(shí),彌補(bǔ)知識(shí)之不能和不足。智慧的確不僅是處世的能力,更是自我完善(成德)的結(jié)晶。
智慧本來應(yīng)該是哲學(xué)的本分,但由于近代知識(shí)中心主義和唯理性主義的發(fā)展,它漸漸淡出哲學(xué)思考的視野,與此同時(shí),哲學(xué)自身也開始走下坡路,它不僅不再是“科學(xué)的科學(xué)”,而且連自身存在的理由都成問題,不止一位哲學(xué)家宣布過“哲學(xué)終結(jié)”。不管哲學(xué)是否終結(jié),它在今天已不復(fù)當(dāng)初的生氣,日益成為無聊的學(xué)院里的智力游戲,卻是一個(gè)普遍的事實(shí)。只有恢復(fù)智慧在哲學(xué)中的核心地位,哲學(xué)才能恢復(fù)它的活力。這不是哲學(xué)自身的要求,而是人類對(duì)哲學(xué)的要求,人類今天面臨的種種根本問題,只有靠智慧,而不是知識(shí),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1]Cf. Herbert Schn? delbach, “ Philosophie ”, Ekkehard Martens/Herbert Schn? delbach, Philosophie: Ein Grundkurs[M].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5.
[2]蒙田.蒙田隨筆全集:第1卷[M].馬振聘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3]斯賓諾莎.神學(xué)政治論[M].溫錫增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4]沃爾弗.關(guān)于中國人道德學(xué)的演講[M]//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愛政,等 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5]康德.實(shí)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Cf.HistorischesW?rterbuchderPhilosophie[M]. Bd. 12,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4.
[7]Hegel,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ReligionII[M]. Werke 17,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8]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5.
[9]阮元.論性篇[M]//程樹德.論語集釋: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10]朱熹.四書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1]黃式三.論語后案[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12]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M]//董仲舒集.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03.
[13]馮契.智慧說三篇·導(dǎo)論[M]//馮契文集:第1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
[14]馮契.馮契文集:第9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