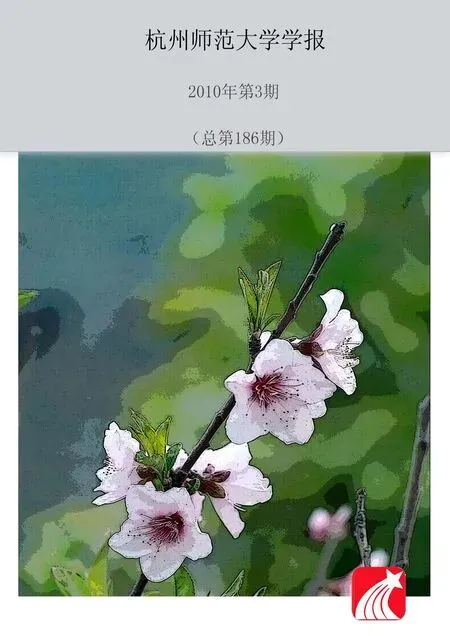一個概念與一種文學史圖景
——讀吳秀明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
俞 潔
(浙江傳媒學院 影視藝術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就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重寫文學史”的呼聲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漸趨高潮。如果從1917年開始算起,中國現當代文學走過的歷程迄今其實也還不滿百年。但時間上的短暫并不能化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復雜性。由于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諸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共和國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這一系列事件又構筑起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整個中華文明處于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之中。因此,從一開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語境就落在了由民族、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因素交織而成的網絡之中,其關系錯綜復雜;而作為大學教育體制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其成立,在一開始,顯然也有賴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促成。正是這樣,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文化、經濟之間的關系,乃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大問題。80年代以后學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其表現于學科層面的致力點,固然是要將文學史從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或影響中解脫出來,從而使文學史敘述建立在其自身的軌道、范疇之內;但另一方面,隱藏于背后的另一大原因也在于,借助于文學史的梳理來清理發生“文化大革命”一類社會事件的思想基礎。正是這樣,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將其起點還原到了五四時期思想啟蒙的語境之中。
將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中解脫出來,這樣的學術取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來說,無疑具有一種獨立的姿態。這樣的姿態有助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真正挺立,但在具體文學現象的研究或史的勾勒中,假如僅僅滿足于以“啟蒙主義話語去翻覆了革命史的話語,我們所做的只是‘調換/顛倒’了一種意識形態的憑借”,而缺少一種“內化的批評”,“缺少內化環節的批判,往往會追認既有的話語,用距離話語的遠近來對某個對象進行批判,而無法阻止自己傾斜于這種暴力性”。[1]這樣的學術警惕提醒我們,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將近百年之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還需要作更進一步的“內化的批判”。這意味著,對文學作品的評判與文學史的建構,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學史教學,都需要超越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即需要將自己的研究立場從“一元化地回收到位于對象對立面的意識形態中(在同為意識形態這一點上,其實并不兩樣)”[1]擺脫出來,而從由政治、文化、經濟等全息的文學史語境出發,在文學本身所處的場域中來加以研究。從這樣的學術立場出發,吳秀明教授的近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2]從生態學的角度重新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時代環境的關系,無疑是一項極富價值的學術工作。
作者在這本著作中所借重的“生態場”概念,最早屬于生態學范疇,由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勒提出。“生態場主張把整個自然都納入一個大系統中,研究整個自然系統內所有現象和所有能量的流動及與生物特別是與人的互動關系及其規律。”[2](P.333)但作者在書中無意糾纏于“生態場”的概念內涵及其演變等諸多問題,而是直入主題地將“生態場”理解為一個相對寬泛的學術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將文學生態學研究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生態文學與文學生態研究。作者認為,文學與生態的關系是多方面的,可作多維立體的研究。“文學生態研究”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文化研究,但卻“從一個獨到的角度對當代文學或文化現象作了概括和透視,并因此不僅賦予當代文學新的內涵,而且也為其分析研究提供新的參照和評價標準”。[2](P.346)這一研究取向的價值在于可以“擺脫以往人文與科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為當下文學創作和研究尋找新的突破點,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方法和途徑”。[2](P.329)在這樣的研究設計中,文學生態研究所致力的,恰恰就是一種全息文學語境的還原與考察。就是說,對文學現象的考察,乃至于文學史的建構,都要求我們擯棄一種先驗的價值立場,排除一種一元化的邏輯思維方式,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場域中,綜合考察與此一文學現象共存的多種社會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樣一種研究立場的確立基于以下觀察。在作者看來,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生態環境“殊為復雜且相當嚴酷”。在現代文學階段,“它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動蕩的戰爭中度過的,血和火的惡劣環境不僅規約了它的題材、主題,而且也深刻地制約著作者的思維理念”;在當代文學階段,“由于相當長時期受‘左’傾文藝思想的指導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使政治上‘解放’了的現當代文學在為政治服務之時逐漸喪失了學科屬性特點”;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魔力也使它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又陷于另一種不自由,從整體上被日趨邊緣化了”。[2](P.2)基于這樣一種狀況,對文學對象的“內化批判”,就不能單從文本出發作出結論,而需要在文本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影響文學創作的諸多外部力量——如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等等。即是說,導致文學生態異常“嚴酷”的諸多因素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不但不應被摒棄在研究對象之外;相反,想要深入理解文學對象本身的形成與價值,就必須綜合地考察文學與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避免相互之間以一種二分的方式作對立的觀察。
以“十七年”文學的研究為例。新時期以來,人們對政治意識形態濃厚的“十七年”文學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甚至否定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以為文學脫離政治就“純粹”了,就是“回到文學自身”。作者認為這種“非政治化”的傾向其實是對文學現象的簡單化處理,因為“當代文學即使在政治化的時代,往往也會與社會的主流觀念形成一種矛盾碰撞的張力,而對原有的僵硬的思維理念有所僭越”,“倘若我們以意識形態為由,對以往政治化時代的文學采取一概貶斥的態度,就有失簡單,也不利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及其有關歷史經驗的總結”。[2](P.57)這樣的觀點是中肯的。事實上,假如我們對“十七年”時期作家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略作考察,就會發現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即作家本人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召喚下,努力想要寫出為政治服務的作品,但這些作品中有相當的部分,最后卻也還都逃脫不了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批判的命運。在這樣的錯位中,我們其實正可以看到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與角逐,從而修正之前文學史所描述的,政治對于文學的單向度的作用;而假如我們注意到這樣一些錯位的存在,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無疑將豐富起來。這就是說,從“生態場”的角度進入文學研究,我們的研究對象就不會僅僅局限于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或文藝思潮之上,而會把研究的目光投射到整個中國現當代的文學空間。在文學生態視野下,“我們可知文學生態系統中的各個主體因素,它們各自都有獨立意志和自覺的能動性,但又各自受著自身生態環境的制約,彼此形成或協調或沖突或磨合的復雜關系,并由這些關系決定著生態系統的最終效應”。[2](P.348)
在這本著作中,作者對這樣的研究理念作了很好的實踐。全書主要分上下兩編探討中國現當代文學:上編為“文學史論與學科建設”,從全球化語境、歷史與現實境遇、整體性格與矛盾性特征、文學史編寫等方面探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作者對現當代許多文學現象(包括海外漢學研究、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史編撰等等)做出了全面而中肯的評價;下編為“生態場域與生態文學”,立足當下文學生態現狀及其生態文學熱潮,并借鑒“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位”等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從文學現狀、文化領導權、經典重構、生態文學等方面探討中國現當代文學所處的生態場域和生存狀態。這樣一種框架設計的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樣兩個不同的視角,觸摸在全球化(特別是西方化)文化生態場域中現當代文學背后豐富復雜的內涵,把握文學與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倫理、道德之間排往迎拒的關聯,總結經驗教訓,為現實和未來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啟迪”。[2](P.3)通過這樣一些論題的研究,文學生態研究的指向在實踐的層面得以展開,它們不但讓我們更為深切地理解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多重面影,同時也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更為豐富的文學史圖景。
在2002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3]中,吳秀明教授即將“客觀寫真”作為這部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宗旨,采用“你說、我說、他說、大家說”的多元視角,將同一段文學事件、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的評論進行歸納,強化編寫的文獻性和客觀性。這種兼容并蓄的開放式的文學史編寫方式,其實已經涉及“文學生態研究”,其理念與實踐都為這本《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的撰寫奠定了基礎;而這部著作的出版,則可以認為是對《寫真》編寫體例的一次理論化提升。或者說,前者是史料的準備與積累,是多重聲音的提供;而這一部著作,則著重闡釋看取史料的眼光,是這多重聲音的串聯與解讀。這兩者,原是二合一的工作,即只有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我們才能夠真正避免一種單一化的研究立場,而深入到文學對象的內部,作一種更為豐富的“內化的”批判。從這一層面來說,這部著作對研究者來說,其價值恐怕更在于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示。
[1]坂井洋史.關于“后啟蒙”時期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41.
[2]吳秀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吳秀明.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