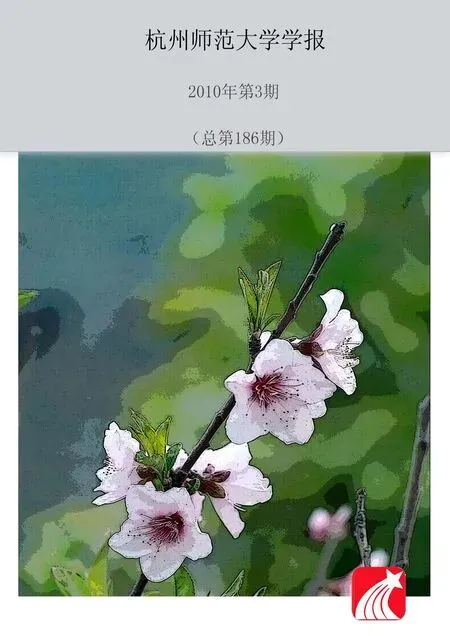社會-文化遺傳基因(S-cDNA)學說
閔家胤
(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紀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發生了一系列轉向,如語言轉向、解釋轉向、后現代轉向,直至文化轉向。我們確實迎來了一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也是一個研究文化的時代。
英國伯明翰大學于1964年成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人類學家R.威廉斯在該中心對文化做專門的研究,他在《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中指出,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上半葉,有五個單詞——industry(工業)、democracy(民主)、class(階級)、 art(藝術)和 culture(文化)在英語中變成了常用詞。他認為“文化可能是上面提到的所有詞匯中最引人注目的”。[1](P.18)在做了幾十年研究之后,他又發現:“英語中有兩三個最為難解的詞,culture即是其中之一。”[2]可能是知難而退吧,《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10卷)和《西方大觀念》(第1-2卷)之類大型工具書,都沒有“文化”和“文明”的單列詞條。
為了適應國際文化競爭,中國學術界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學和文化哲學。
首先應對“文化”和“文明”這兩個基本概念做出區分和定義。
歐美文化學學者對“culture”的定義做過精細的統計研究,發現有160多個定義。從詞源學上講,英文詞“culture”是從法文移植來的,而法文詞“culture”又來自拉丁文“cultura”。現在能查到的最早使用“cultura”這個詞的是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前106-前43),他講過一個拉丁文的論點“cultura anima philosophia est”,譯成中文是“文化是心靈的哲學或修養”。[3]他意識到:文化產生和存在于人的心靈。“culture”的本義則是耕種,法國人安托萬·菲雷蒂埃1690年編撰的《通用辭典》這樣定義“culture”:“人類為使土地肥沃、種植樹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1](P.5)由此可知,文化的起源是農業勞動知識的積累,特別是用文字記錄下來的知識;而在此之前,在采集-狩獵社會,人類靠天吃飯,生產技能靠演示和口口相授,無法用文字記錄知識。
近代,文化人類學家們最早致力于文化和文明的研究。文化人類學家泰勒在1871年寫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將“文化”與“文明”兩個概念混同,并定義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和習慣的復雜整體。”[4]這個定義是有代表性的,因為歐美學術界后來涌現的160多個定義大類于此:要么“文化”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要么把“文化”定義為平列的同樣含糊的概念“整體”“總和”“總成績”“模式”“方式”“樣式”等等。
邏輯學上標準的定義方法是種加屬差定義。據此,我們要尖銳地提出問題:為什么300多年以來,始終不能給“文化”下一個標準的種加屬差定義呢,這究竟是為什么?
從人類知識體系的角度可以這樣回答:直到20世紀末葉,人類知識體系有多方面的缺失,這些缺失決定了人們不可能給“文化”下一個種加屬差定義。概括地說,這些缺失包括缺少本體論的相應范疇,缺少恰當的社會系統模型,缺少社會系統內部的通訊系統模型,缺少對“文化”和“文明”進行聯系和區別的科學認識。
首先來談本體論的缺失。自從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在17世紀用拉丁文 “Cogito,ergosum”提出“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之后,整個西方哲學來了個“認識論轉向”;本體論研究不是被根本否定、就是被撇在一邊。然而,實際上人類知識體系是不能沒有本體論承諾的。后來,也有一些哲學家討論本體論問題,可是錯誤地借用笛卡爾討論認識論的“主體-客體”二元框架來討論本體論問題,結果得出“存在”和“意識”或“物質”和“精神”的二元論本體論,甚或得出更偏執的物質一元論或精神一元論。在這種一元或二元的哲學本體論框架中,哪里會有“文化”的位置,哪里會有“文化”所屬的范疇即它的上位概念呢?
因此,在本體論問題上,我們應當糾正西方哲學家們的錯誤,跳出笛卡爾主客兩分的框架,回歸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進化多元論框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同時,20世紀科學革命的成就——相對論、量子力學、生物遺傳基因(DNA)理論、大爆炸宇宙論和系統科學,改變了人類的認知圖像,使我們有可能站在當代科學的宇宙廣義進化的客觀立場上,拉開科學認識必須要有的同被認識對象的距離,透視宇宙進化、銀河系進化,太陽系進化、地球進化、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進化,得出“進化的多元論”:場→能量→物質→信息→意識,它們是依次進化出來的宇宙的五種元素,地球人類至少是生活在這五種元素的多元世界上;或者說,當代的科學思維和科學的哲學思維必得采用這樣五個本體論范疇。[5]而用“奧卡姆剃刀”不可能剃掉其中任何一個范疇,也不可能歸并其中任何兩個范疇。
只要把“文化”放到進化的多元論的本體論框架中,原來一直缺失的“上位概念”或文化所屬的本體論范疇就能被找到:“文化”屬于“信息”這個種范疇,或者說“文化”的上位概念是“信息”。“文化”的本體論缺失因而得以消除。
社會系統的第一個模型、同時也是最著名和影響最大的模型,是馬克思在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闡述歷史唯物論原理時建立的模型。筆者在馬克思模型的基礎上,吸收系統哲學家E·拉茲洛在《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一書中建立模型[6]的一個思想,把“文化信息庫”(culture-information pool)放在中央位置;繼而吸收錢學森社會系統模型[7]的一個思想,把“人”放在核心位置;進而把馬克思模型中的“生產”分成“人的生產”、“物質產品生產”和“文化信息生產”三大塊,由此建立了一個社會系統的新模型:[8]

圖1 社會系統的新模型
按照這個新模型,筆者把社會系統定義為在自然生態系統基礎上進化出來的由人組成的自復制-自創新系統,人不斷地從文化信息庫中提取信息并進行人的、文化信息的和物質的生產和創新,從而實現系統的自復制-自創新,維持自身的存在和進化。從這個社會系統的新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信息庫”中的“文化”被安放在社會系統的中央位置;而文化的創造者“人”又被安放在核心位置,以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
通信系統的問題,則由當代信息-通信理論和分子遺傳學為我們彌補了缺失。在信息論中,通信系統的最簡模型為:

圖2 最簡通信系統模型
當代分子遺傳學揭示了生物遺傳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則。比照最簡通信系統模型,可以把中心法則擴大、轉換成生命的通信系統模型:

圖3 生物遺傳的通信系統模型
對“文化”和“文明”的區分。英文詞“civilization”(文明)來自法文,法文來自拉丁文“civis”,拉丁文又來自希臘文“πολιτηs”,指生活在古希臘“城邦”中的“希臘族”人(“citizen”,公民),以別于生活在城邦之外的“蠻族”(barbarians)。根據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英國希臘學專家基托的《希臘人》,“城邦”的希臘文原詞(πολιs )譯為英語 “city-state”是不太好的譯法。漢語隨英語亦然,因為這個譯法讓人誤以為“城邦”是個地理學概念,其實“城邦”是個社會學概念——城邦是當時的社會組織。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動物”也是誤譯,正確譯法應當是“人是生活在城邦中的動物”。
“城邦”是古希臘時代進化出來的基于血緣關系而又超出血緣關系的、由語言-文化關系構成的社會組織——社會系統。生活在這個社會組織中的是希臘族人,講希臘語,有“共同的社會生活——婚姻關系、氏族祠壇、宗教儀式、社會文化生活”。[9](P.40)最后這一項很重要,包括政治、軍事、道德、講演、辯論、戲劇、體育和經濟生活等。總之,生活在城邦中的citizen(公民)是接受希臘文化的文明人,生活在城邦之外的是沒有接受希臘文化的barbarians(蠻族)。他們或是奴隸——俘虜來自外族人,或是移民——遷徙來的外族人;他們不會講希臘語,只會像野獸一樣bar bar(巴巴)地叫——至少希臘人聽來如是,故名barbarians(蠻族)。[10]當時也有特許入籍(歸化)的公民(ποιητοι πολιται),可直譯為“制造成的公民”。[9](P.110)怎么制造呢?當然是用希臘語和希臘文化制造。
“文明”一詞在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中皆為Civilization。這個詞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是由法文Civil(英文Civis)一詞演變來的。Civil一詞原意是指在城邦中享有合法權利的公民。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把當時由封建習俗轉向資產階級化的演變稱為Civilizer,它的原意為:“公民化過程”。到法國大革命時代,人們把體現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新的文化氣象稱為Civiliz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它是西方公民社會中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種新的氣象和新的趨勢。
在彌補了這四個缺失之后,我們就會明白:“文化”正是社會系統內部的“遺傳基因”(DNA)!“文明”則是文化經過生產過程物化出來的“蛋白質”,或者說是各種各樣由“文化蛋白質”組成的“文化表型”。“文化”同“文明”的關系恰好就是“基因型”(genotype) 同“基因表現型”(phenotype) 的關系。這樣,我們就得到了“文化”和“文明”的標準的種加屬差型定義:文化是社會系統內的遺傳信息——社會-文化遺傳基因,文明則是文化的社會表型。
論及二者的區別,可以直觀地說,從人的頭腦中出來、還可以回到自己或他人頭腦中去的屬于文化;而從人的頭腦中產出的、通過勞動加工成為物品,因此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或他人的頭腦中去的,則屬于文明。文化是信息產品,由語言和文字編碼,可以轉錄和翻譯,并由文化遺傳而永存;文明則是物質產品,不能轉錄和翻譯,只能隨時間衰敗和瓦解。已經消失了的文明,其尚未完全瓦解的遺存,有時被考古學家們挖掘出來加以研究,以推斷其中隱藏的文化。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社會系統內社會-文化遺傳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則:“文化→生產→文明”。我們稱之為文化“中心法則”,是因為從我們建立的社會系統新模型看,盡管社會系統內有各個方向的信息流,并且都是雙向互動的,可是“文化→生產→文明”是社會系統內主導的、最強大的和持續不斷的信息流,它維系著文化的傳承和社會的自復制。
我們進而嘗試把“社會-文化遺傳基因”的英文拼寫Social-culture DNA縮寫成S-cDNA。還可以把教育(education)縮寫成S-eRNA,把科學縮寫成S-sDNA,把技術縮寫成S-tRNA,然后即可構制出“社會文化遺傳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則”之示意圖:

圖4 社會-文化遺傳的通訊系統模型
社會-文化遺傳的通信系統模型(圖4)是普適性的,適用于各個時代的社會。我們進一步加上S-sDNA和S-tRNA,把它擴展成只適用于現代社會的“工業社會-文化遺傳的通信系統模型”見圖5:

圖5 工業社會的社會-文化遺傳的通訊系統模型
這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價值所在就體現得非常清楚了。同時也直觀地表明,在現代工業社會里,社會-文化遺傳過程要比以往復雜得多。
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展開了的文化定義:文化是社會系統內社會-文化遺傳基因(S-cDNA)的總和,是歷代社會成員在生存和生產過程中心靈創造的積累,是社會的靈魂。其核心是所有成員共同的圖騰、信仰、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和行為準則,其外圍則是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生活常識和生活技能。文化為社會系統個體的心靈結構和行為編碼,為社會系統的結構和行為編碼,以確保他們能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生存,并且通過生產不斷復制和創造相應的文明表型。文化是社會系統內的最終決定因素,它最終決定社會系統的存在、停滯、變革和進化,決定歷史。
我們把“文化”定義為“社會系統內的遺傳基因”,“文明則是文化的社會表型”。由此,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決定文明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又把社會系統定義為“在自然生態系統基礎上進化出來的,由人組成的,并由人從文化信息庫中提取信息進行人的、文化信息的和物質的生產之自復制-自創造系統”。按照這個定義,社會系統內的三種生產——人的生產、文化信息的生產和物質產品的生產,是社會系統內部的功能過程,既構成了文明,也構成了社會;既是文明的自復制-自創造,又是社會系統的自復制-自創造。換句話說,文明是社會系統的全部內涵,社會系統則是全部文明的外延,它們的所指是同一社會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文明”等同于“社會”或“社會系統”。據此可以得出結論,既然文化決定文明,那么文化也決定社會;或者說,最終是文化在社會系統中起決定作用。
我們還可以用類比法論證這個命題。在金岳霖主編的《形式邏輯》教科書中,[11]關于類比法是這樣寫的:“我們觀察到兩個或兩類事物在許多屬性上都相同,便推出它們在其他屬性上也相同。”并將其圖示為:
A與B有屬性a1,a2,…,an
A有屬性b
所以B也有屬性b
中山大學林定夷近年研究類比法的一篇論文,[12]首先引英國貝弗里奇《科學研究的藝術》“類比是指事物關系之間的相似,而不是指事物本身之間的相似”之說,然后論證我國現行邏輯教科書的不足,最后得出結論:
類比是一種從特殊過渡到特殊的思維方式。它借助于對某一類對象的某種屬性、關系的知識,通過比較它與另一類對象的某種相似,而達到對后者的某種未知屬性和關系的推測性的理解和啟發。
他給出了類比法的兩個程式:程式甲和程式乙。將兩個程式與本文的論證對照,筆者傾向于相信本文采用的類比法接近“程式乙”:
程式乙:已知A對象的屬性a、b、c之間 有某種函數關系f(a,b,c)=0
預感到:B對象的屬性a′、b′、c′在 數量關系上與a、b、c有些相似
猜測:a′、b′、c′之間存在同一形式的函數關系f(a′、b′、c′)= 0”。
筆者發現:在生命系統A中,DNA有本質屬性a 和相關屬性b、c、d、e、f、g,且DNA對其生命系統的表型有決定作用;在社會系統B中,S-cDNA有與a相近的本質屬性a′,有與b、c、d、e、f、g相同或相近的相關屬性b′、c′、d′、e′、f′、g′;于是可以推測S-cDNA對社會系統表型也有決定作用。
對最后這個論點,還可以用排除法證明,就是說用事實證明。例如,曾被認為是社會-歷史的決定因素的強權政治、強大武力、強人意志在同先進文化的較量過程中,最終都是先進文化取得勝利。即便是經濟決定論,分析到最后依然超不出文化最終決定論的表現形式。“人心向背”可以一時決定政權的更迭,可是唯有“文化”決定社會系統的演化,決定歷史。把曾經和可能被視為社會系統中的決定因素的這五個因素都排除之后,剩下的“S-cDNA在社會系統中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因素卻是不可能被排除和推翻的。
如繼承古希臘文明的羅馬,把歐洲古典文化推向新的高度。羅馬三次被只學它的技術,特別是只學它的軍事技術的蠻族打敗。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公元455年汪達爾人先后攻陷羅馬。羅馬遭到三次洗劫,帝國走向分裂和衰亡。然而,羅馬依然是最終的勝利者,因為它的文化“充當從蝴蝶到蝴蝶之間的卵、幼蟲和蛹體”,[13]在后世重放光芒,而那三個武力強大的蠻族則依然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中國。中國古代文化在宋朝達到高峰,可是宋朝在軍事上非常軟弱,被史家稱為“無兵的文化”。在同強大的遼金和蒙元的長期對壘中,節節敗北。最后宋朝滅亡了,漢人遭受蒙古人100年的奴役。然而,漢人是最后的勝利者,因為漢文化延續至今,而且還繼續發揚光大,而蒙古人則如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所說,由于蒙元實行民族分治,拒絕接受漢族文化,結果他們來的時候是什么樣子、100年后被趕回草原還是什么樣子。
強大武力斗不過文化,強權政治斗不過文化,強人意志依然斗不過文化!秦始皇留下千古偉業,可他焚書坑儒,徹底清除前朝及六國文化,這就做不到了,只留下千古罵名。再看,“文革”期間,林彪和“四人幫”一伙蒙騙幾億中國人,握幾百萬大軍,指揮幾千萬紅衛兵,要消滅所有封資修的黑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結果只瘋狂了10年,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了。正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至于“經濟決定論”,我們承認和繼承馬克思唯物史觀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學說。在圖1“社會系統的新模型”中,“物質生產系統”仍然放在基礎的位置,而包括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物質生產全過程就是“經濟”。在圖4“社會-文化遺傳的通信系統模型”中,“生產”決定和制約整個“文明”,而“文明”即“社會”。筆者所做的補充是,在社會的“物質生產”之前總得有“人的生產”和“文化的生產”。如馬克思自己所說,“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因為“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15]在圖5“工業社會的社會-文化遺傳的通信系統模型”中,本文所做的補充是,“生產”要有“技術”(S-tRNA),而“技術”源于“科學”(S-sRNA)。在工業和信息社會,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決定“生產”,科學技術決定“經濟”,當然現代科學技術文化最終決定了現代社會。
最后來談“人心決定論”。中國的史家向來有“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口頭禪。那么,是否“人心”是社會系統的最終決定因素呢?首先,我們承認,“人”或者說“人心”,是社會系統中的原始變異點;人心變了,人心喪盡,一個政權肯定會滅亡。中國史家的斷語是不錯的。賈誼的《過秦論》就基于這個信條。1949年國民黨人心喪盡而失政權,共產黨人心所向而得政權。可是,它畢竟只決定政權的更迭,就是說只決定社會系統的一個方面、只決定一時一事。其次,“人心”是什么?這里談論的“人心”決不是一團團的血肉,而是文化信息的接收器。絕大多數人要么接受傳統文化,要么接受外來文化,要么接受新出現的流行文化——某種社會思潮,結果,具有共同文化取向的“人心”占到社會的大多數,就會形成推動社會變化和歷史進程的力量。然而,“人心”畢竟只是社會-文化思潮的工具,而且經常是盲目的工具,例如外國有十字軍、黨衛軍、塔利班,中國有義和團、紅衛兵,他們都曾充當過某種文化-社會思潮的盲目工具。因此,最終還是社會-文化遺傳基因(S-cDNA)在背后決定著社會的變化。
因此, “S-cDNA在社會系統中起最終決定作用”,必須強調“最終”二字。在社會系統中,帝王的強人意志、專制的強權政治、蠻族的強大軍力,都可以殺害文化人、暫時毀滅文化,都可以一時決定社會的興衰存敗,可是從長遠來看,最終還是文化決定社會,文化決定社會的命運和社會的進化。經濟固然是社會的基礎,可是,在現代工業-信息社會,有比經濟更基礎的基礎,那就是教育和文化;沒有具有原創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教育和文化做基礎的經濟,就只能進行來料加工和組裝,僅僅是世界工廠而已。人心向背固然可以決定政權的存亡更迭,可是人心不過是社會-文化思潮發揮最終決定作用的工具,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工具。
因此,我們觀察全球社會,首先看到的是大國之間軍事力量的競爭。可是,一位深刻的觀察者應該在軍事后面看到政治,在政治后面看到經濟,在經濟后面看到科技,在科技后面看到教育,在教育后面看到文明,在文明后面看到文化。在人類社會中最終是文化遺傳基因(S-cDNA)的競爭,一如在生物界最終是生物遺傳基因(DNA)的競爭。
將以上論述提高到抽象的理論上和科學的理性高度,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在 “社會系統的新模型”(圖1)上,“人”被放在核心位置,環繞“人”的是“文化信息庫”,可見“文化”也被安放在中央位置。那么,最后的結論為什么不表述為“人”或“人心”是社會系統的決定因素,而是說“文化”(S-cDNA)是社會系統中的決定因素呢?
歷史哲學講的“人心”是人腦-神經系統和心臟-血液循環系統耦合成的復雜系統的涌現,表現為自我意識,被稱為“心靈”。人的心靈中的“意識”是宇宙進化和人超越其他生物特有的第五種元素,人的心靈具有獲取環境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能力,具有以靈感形式產生突變的能力,以此成為社會系統中的文化創新之源,文化反思之源,文化選擇之源。
可是,盡管“人”是社會系統的基本元素,人的“心靈”作為認知主體具有創造文化的能力,有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具有在多種文化當中做出選擇的能力,可是作為社會-文化遺傳基因的“文化”是前人“心靈”創造的積淀,是歷史的遺產,是社會系統中最穩定的因素和最保守的勢力。因此,任何人在進行文化反思、批判、創新和選擇的時候,總是受到自己接受的文化遺傳的支配,而他做出的反思、批判、創新和選擇最終又融入文化傳統繼續支配自己,支配他人和支配后人。因此可以說,個人“心靈”是即時的文化,而“文化”又是歷時的心靈。
這樣一來,我們討論的問題就變得更明晰和更尖銳了:人心創造文化,人心反思-批判文化,人心選擇文化,而文化又遺傳性地輸入人心,控制人心,支配人心,社會系統的狀態、結構和行為的演化就在文化和人心的相互作用中前進。可是,為什么說“文化(S-cDNA)在社會系統中起最終決定作用”呢?可以明確地說,在20世紀末完整的系統科學體系出現以前,任何人都無法解決和回答這個問題,而現在則可以。在哈肯的協同學中有一個“序參量和役使原理”,它科學地、嚴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許國志的《系統科學》這樣概括上述原理:
在描述系統狀態的眾多變量中,有一個或幾個變量,它在系統處于無序狀態時,其值為零,隨著系統由無序向有序轉化,這類變量從零向正有限值變化或由小向大變化,我們可以用它來描述系統的有序程度,并稱其為序參量(order parameter)。序參量與系統狀態的其他變量相比,它隨時間變化緩慢,有時也稱其為慢變量,而其他狀態變量數量多,隨時間變化快,成為快變量。
在系統發生非平衡相變時,序參量的大小決定了系統有序程度的高低;它還起支配其他快變量變化的作用。序參量的變化情況不僅決定了系統相變的形式和特點,而且決定了其他快變量的變化情況,在這個意義上講,序參量也可以稱為命令參量。”我們知道,序參量的英文詞是“order parameter”, 恰好即可以翻譯成“序參量”,也可以翻譯成“命令參量。
系統相變過程是一個由系統狀態變量形成系統序參量,序參量又役使系統其他狀態變量的過程。哈肯將相變過程中系統狀態變量里序參量與其他快變量之間役使、服從關系稱為役使原理。序參量確定以后,我們討論系統的演化可以只研究序參量即可,序參量將整個系統的信息集中概括起來提供給我們,序參量給我們了解、認識系統提供了一把鑰匙。[15]
社會系統無疑是最復雜的系統。在我們建立的“社會系統新模型”中,每一個子系統都可以看作是一個狀態變量。在眾多狀態變量中,“文化”無疑是“整個系統的信息集成體”,無疑是慢變量,因而文化就是社會系統中的序參量或命令參量,而其他變量(包括人、物質產品生產、人的生產、文化信息生產和管理系統)都是快變量。眾多快變量形成“文化”慢變量(即序參量),而文化作為社會系統中的序參量又反過來支配和役使眾多快變量,所以文化(S-cDNA)就成為社會系統中的最終決定因素。
將“心靈”和“文化”兩相比較,個人的心靈(即便是最偉大的心靈)不過是歷史長夜中的流星,而文化則是無數流星匯成的照亮歷史長夜的永恒之光。
倘若在筆者做了這么多論證之后,你對“S-cDNA在社會系統中起最終決定作用”這個命題仍舊有疑慮,那么就讓筆者引導你想象地球-人類文明在未來發生的兩種極端情況:一是地球-人類文明現在突然滅絕了,只留下殘骸;二是在遙遠的將來,在滅絕之前,人類成功地將自己的文明復制到一個類地行星上去了,讓你看清“文化”是不是起“遺傳密碼”的作用。
我們知道,美歐已經發射伽利略探測器(Galileo Probe)尋找地外文明。設想在今后的某個時候,人類在遙遠的宇宙空間找到了一顆類地行星,按其自然條件的基本數據,適合復制地球生物、人類和人類社會。可惜的是,那顆類地行星太遠了,宇宙飛船要飛300年才能到達,人飛到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能靠智能機器人攜帶克隆設備,攜帶地球動植物主要物種的DNA, 攜帶地球四個人種的DNA, 到那里去克隆。怎么復制那地外的第n+1個地球-人類社會呢?顯然只須智能機器人攜帶一張芯片——五維記錄,信息量是現有芯片的一萬倍,上面轉錄有占人類社會文化遺傳基因(S-cDNA)5%的功能基因。待新人類克隆出來之后,由智能機器人用那5% 的S-cDNA按圖4和圖5的程序教育,和他們一起學習、設計、建造和生產,地球Sn+1社會肯定就在遙遠的類地行星上復制(翻譯)出來了。
抽象地從理論上講,筆者的意思是,如果我
們已經對地球上現有n個社會系統進行考察,證明“S-cDNA在社會系統中起最終決定作用”這個命題為真命題,而且以上又證明它對未來地球上或地外類地行星上的n+1個社會系統仍然是真命題,那么我就用絕對可靠的完全歸納法對這個命題做了最終證明。
這回,你信服了吧!
[1]維克多·埃爾.文化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蕭俊明.文化轉向的由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
[3]D.Paul Schafer.The Cosmological Conceptfon of Culture[M].world culture project,Markham, Canada.1988.
[4]莊錫昌,顧曉鳴,顧云深.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99.
[5]閔家胤.進化的多元論——系統哲學的新體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71.
[6]E·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103.
[7]魏宏森,曾國屏.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182.
[8]閔家胤.社會系統的新模型[J].系統科學學報,2006,(1).
[9]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H. D. F.基托.希臘人[M].徐衛翔,黃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
[11]金岳霖.形式邏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5.
[12]林定夷.科學邏輯與科學方法論[M].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245-258.
[13]湯因比(Toynbee,A.T.).文明經受著考驗[M].沈輝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91.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202.
[15]許國志,顧基發,車宏安.系統科學[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24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