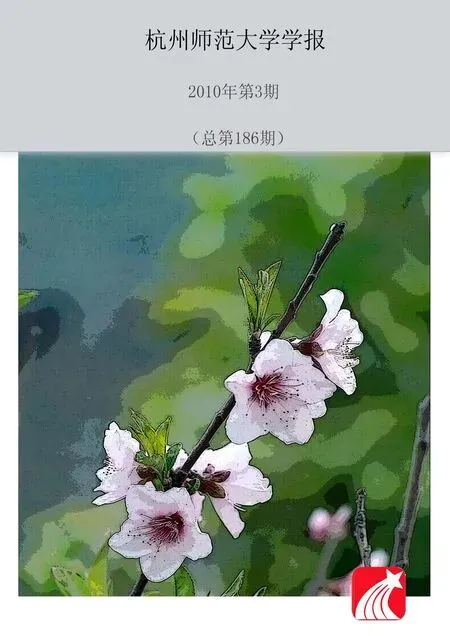以教育為手段
——杜威眼中的教育與社會
袁德潤
(杭州師范大學 初等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作為哲學家、教育理論家、激進的社會改良主義者,杜威的教育理論與其社會改造的理想之間存在著唇齒相依的關系。本文將從教育、社會和人的關系的視角,對杜威的教育目的觀進行重新解讀,以闡釋其教育理論和社會改造理論之間的關系,同時嘗試探究其教育目的論中存在的局限。
一 教育目的:教育之外無目的
“教育的過程,在它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1](P.58)杜威式的宣言,把自教育存在以來負載于學校教育和學生身上的社會重任,似乎一下子完全拋掉,唯余教育對人的發展價值:“教育的過程是一個繼續不斷的生長過程,在生長的每個階段,都以增加生長的能力為其目的……除了更多的教育,沒有別的東西是教育所從屬的。”[1](P.63,59)因此,他認為良好的教育目的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特征:“(1)一個教育目的必須根據受教育者的特定個人活動和需要(包括原始的本能和獲得的習慣)。(2)一個教育目的必須能轉化為與受教育者的活動進行合作的方法。(3)教育者必須警惕所謂一般的目的和終極的目的。”[1](PP.119-120)
概而言之,杜威的教育目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教育目的內在于教育活動 “教育之外無目的”,這一觀點與傳統的以社會需要為目的的教育目的觀相對立,即所謂的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抗衡。這一點在學界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第二,教育目的是內生性的 他反對用比較的觀點(即把成人的成熟狀態和兒童的未成熟狀態進行比較,把成人的成熟狀態當作兒童未來發展的方向和標準)來看待兒童的發展,從而把發展看成是填補未成熟狀態和成熟狀態之間空缺的行為,這正是外在目的論所強調的教育的特征;相反,他強調要用內在的觀點來看待兒童的發展,把兒童本身的未成熟狀態看成是兒童發展中的積極的、建設性的力量,是兒童發展的基礎和依據。
第三,教育目的是動態發展的 他所提供的目的不是靜態的、可以占有的標的物,而是隨活動的進程和需要而不斷進行觀察、判斷、計劃、調整并選擇合適的行動方案,以保證活動能夠連續不斷地進行下去的指導。這種具有內在連續性的教育目的必然是具體的、動態的、靈活的、預見性的,這樣的目標可以為活動提供激勵、指導和繼續活動的動力,引導活動不斷向前發展。
第四,教育目的是現實定向的 傳統的教育目的強調為學生的未來生活、完滿生活或道德生活打基礎,以傳遞、繼承歷史上人類積累的知識和培養相對抽象的“美德”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在杜威看來,這種目的以“追溯既往”為特征,是“使未來適應過去的過程”;他認為自己的教育目的是從兒童的現在和活動的現在出發,以促進兒童現在的生長為手段、以一種連續不斷的經驗改造的方式直接走向兒童的未來生活,而不僅僅是為了未來生活做準備。在他看來,未來是現在創造的,而不是現在設定的。可以說,他的教育目的定向于現在、指向于未來,教育要“成為發展中的將來的一種力量”。
第五,教育目的體現了手段與目標的統一性 手段即目標,目標即手段,兩者在活動過程中難以分開,每一個前面的結果都是后一個行為的條件,根據這個條件所達成的結果又成為下一個行動的條件,目的和手段構成一個永無止境的連鎖,這個形成連鎖的過程就是兒童連續不斷的生長過程。在目標和手段的統一性方面,杜威所強調的是相互銜接的活動之間意義上的聯系,他認為由別人指定的、連續的、機械的動作或者行為,是沒有目的可言的。基于此,它給了教育獨特的定義:“教育就是經驗的改造或改組。這種改造或改組,既能增加經驗的意義,又能提高指導后來經驗進行的能力。”[1](P.87)
杜威教育目的凸顯了經驗主義實質,追求教育目的的“實然”性而非“應然”性,是他與傳統教育的理性主義教育目的在哲學基礎上最大的區別。他的教育目的建立在當時心理學發展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并深受生物進化論觀念的影響。在他教育目的的核心概念“生長”上,生物進化思想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他把生長描述成一個不斷進行、沒有終點的過程,正常狀態的成人和兒童都在成長,只是由于具體的情況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成長;成長是沒有目的的,沒有最終標準的,成長本身就是成長的目的;生長是不依靠外在力量的強制的,而是活動過程自己的結果,是一個朝著后來結果的行動的累積運動。
不難看出,如果僅僅從杜威的教育思想分析的話,他眼中的教育是一個自足的系統,是一個不需要來自外界的影響、尤其是壓力的自循環系統,因為“生長”是教育中人的自然行為,兒童的經驗和生活為他們的“生長”提供了資源和條件,教育所該做之事,就是“改組或改造”兒童的經驗,使他們更好、更多地“生長”。“改組或改造”經驗的最佳方案,是“做中學”。然而,作為杜威哲學思想“實驗室”的教育,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社會的功能系統之一,杜威可以把教育目的限定在教育之內,可以主張兒童為了生長而生長,但他不可能主張為了教育而教育。實質上,杜威之所以作如此極端之論,除了他對傳統教育忽視兒童的強烈不滿以外,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激進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
二 社會理想:民主共同體
杜威社會思想的基調首先是對他所生活的美國社會現狀的不滿和強烈抨擊。他看到,在資本主義壟斷經濟和財富飛速增長的背景下,美國的民主已經成為“一場不堪入目的鬧劇”: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結果只服務于“舊的人剝削人的目的”,而不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狀況”,導致“平等這一偉大的美國原則已成為神話”;[2](PP.128-129)政治屈從于大的商業集團利益的驅使,這些有權有勢的經濟集團“利用一切行政與立法機關服務于自己的目的”,他們實際上統治著美國人民;美國民眾在狂熱與失望的交織中普遍存在著對政治生活的“伴隨著陣發性的沖動與痙攣的冷漠”,使美國社會淪為“迷茫的”“混亂的”“不安的”“漂浮的”“分裂的房子”。[2](PP.137-139)
雖然杜威對當時美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有切膚之痛,并極力抨擊;但是,他對作為美國社會基礎的西方式民主還是基本認同的。他認為,盡管存在著諸多的社會問題,但通過改良、改造,可以保證民主社會的良性發展。而要想挽救當時美國社會“混亂”“分裂”與“漂浮”的可悲現狀,恢復社會生活中民主的生命力,“美國人必須盡快拋棄那些陳舊的民主教條,使他們的信仰、道德、欲望、情感乃至整個文化迅速適應工業革命以來所發生的社會巨變”。[2](P.146)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首先要改變社會生活的個體,因為在杜威看來,社會是由單個的人按照一定的關系、組織、規范構成的群體,其質量取決于個體的聯合方式和個體對于群體生活的參與自由度、對群體生活的影響方式和影響力等因素;同時,群體一旦形成之后,其運行的機制和方式也決定了生活于其中的個體的生活質量。
杜威理想中的社會形態是“民主共同體”。[2]其共同體有兩個基本特征:(1)共同體的成員必須共同具備“目的、信仰、知識——共同的了解——和社會學家所謂志趣相投”。[1](P.9)(2)組成共同體的各社會群體之間不僅自由地相互影響,而且通過應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產生的新的情況,不斷改變和重新調整社會習慣。也就是說,具有不斷生長、更新的能力應該是共同體的特征之一。民主是形成共同體的前提條件,共同體成員目的的共享和興趣的溝通以民主的生活方式為依托。在杜威的社會學思想中,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組織形式和政府管理方式,它的真正意義在于,它是一種社會的和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社會生活中,它以全體成員可以共享的共同利益的多寡以及充分和自由交往的程度為尺度;在個人生活中,它以個體依據自己的信仰、判斷、愿望和選擇而生活和自由表達的程度為尺度。民主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它也處于不斷地發展、成長和完善的過程之中;相應地,具有民主生活方式的個體所組成的“民主共同體”是一個需要建設的社會理想,它不可能是天外來客,而只能從現有的“非民主共同體”的社會中逐漸培養出來。
構建理想的“民主共同體”,需要具有民主生活習慣的成員;具有民主生活習慣的成員,又需要現實的教育來培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公立學校已被現狀的衛道士們接管”。[2](P.137)要擺脫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必須在這三者之間尋找突破點。而在這三者之中,教育可以說是當仁不讓的最佳選擇。于是,杜威便為自己的社會理想設計出了“發動機”——具有新質的一代新人。沒有教育所培養的具有民主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的新人,其理想的民主社會只能成為烏托邦;培養新人的教育當然不能以當時的社會要求為目的,因為它與真正民主的意義背道而馳。為了實現他的社會理想,他必須重新設計教育,以學校為實驗室,來檢驗他恢宏的社會改造思想,于是,他把教育目的限定在“教育之內”,也就理所當然了。
三 教育與社會改良:手段與目的
雖然杜威多次強調“教育過程除了自己以外,沒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但很顯然,他的教育“內部的”目的所指向的是教育之外的理想,教育成為杜威實現社會改良目的的手段,教育的目的指向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民主生活方式。
杜威設想的教育這個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的“動力”又是如何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呢?杜威給出的答案是:改組和改造經驗。其基本路線可以簡單描述為三個環節:第一,社會為兒童的發展提供全面、良好的刺激,使他們有全方位地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第二,學校教育利用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通過目的的共享和興趣的溝通,對來自于生活的經驗進行連續不斷的改組和改造,以實現兒童持續不斷的生長。經驗的改組和改造方式表現為:在兒童的活動中,通過兒童的活動并為了兒童能夠進行繼續有意義的活動。活動是杜威最為鐘情的教育方式,通過兒童的活動他連通了教育與理想的民主社會之間的關系:通過共同的活動,兒童們分享共同的興趣、目標、信仰、情感、理想,了解活動的意義以及每個人在活動中的作用,為了共同的目標而互相幫助、互相激勵;在行動中學會考慮、參照別人的行動來協調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動與他人的行動有共同的意義和方向等等,這些素質正是“民主共同體”成員應該具備的。第三,理想的民主社會通過理想新人的培養而逐漸形成,反過來又能對其成員施加教育的影響,生生不息,延綿不絕,民主社會就會像日漸成長的兒童一樣不斷地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前進。通過以上三個在時間、空間上并行的環節,杜威的教育目的才能說是真正實現了。
可見,杜威的教育目的是其社會目的論中的一個重要且必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他既是現實主義者,又有教育決定論的傾向。他注重現實社會在教育活動中的基礎和條件地位,確認“社會在指導青少年的過程中決定青少年的未來,也因而決定社會自己的未來”,同時又認為“教育和社會生活的關系,正如營養和生殖和生理的生活的關系一樣”。[1](P.49,14)教育是社會的過程和功能,社會的發展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為了實現“不僅闡明兒童和青年的發展,而且闡明未來社會的發展”的力量,教育是杜威實現社會理想的不竭的原動力。他甚至認為,柏拉圖哲學的成敗完全在于“他不信任教育的逐步改進能造成更好的社會,然后這種更好的社會又能改進教育,如此循環進步以至無窮”,[1](P.101)這種評價從反面印證了杜威對教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看法。
其實,他的整部《民主主義與教育》都在論述教育與他的社會理想之間的關系。在他理想的“民主共同體”中,教育的內在目的和外在目的是完全統一的:“如果民主主義具有道德的和理想的含義,那么就要求每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同時,給每個人發展特殊才能的機會。個人發展和社會效率這兩個教育目的分開,是對民主主義的致命打擊。”[3](P.138)
四 杜威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盡管杜威對世界現代教育的貢獻到目前為止尚無人堪與匹敵,但他的本意始終不在教育,而在他的社會理想。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常常使人產生杜威的教育存在著相互糾纏和自相矛盾的錯覺”,“在社會中心還是兒童中心,教育究竟有無目的等問題上引起后人爭論不休”。[4](P.28)杜威對傳統教育目的論的批判和反叛,既是他對教育史的貢獻,也是他教育目的論局限性存在的原因之一。
首先,杜威對其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概念“生長”缺乏清晰的表述,這一點從他的教育理論問世開始,一直引起不同領域批評者的質疑,他的命題被認為是語焉不詳的“難解的謎團”(祁爾德)。為了應對詰難,杜威也曾對他的“生長”概念不斷修正,先后用“一般的生長或總的生長”(general growth)、“最高限度的生長”(maximum growth)、“遠期的結果”(the later result)等說法來應對。杜威堅持生長的無方向性的觀點,深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生物進化論認為生物個體的變化可能導致物種的更新,但物種的更新(結果)并不是決定生物個體發展過程的因素,當然也不可能是生物進化的外在的目的,它只是生物個體發展的副產品。杜威把這種觀點在教育中做了類比,認為兒童的生長也不存在外在的方向,生長本身就是生長的目的。他的這種類比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可比性:生物的進化是一種自在的行為,是一種自然發展,而學校教育則是人類社會有意識的社會傳遞和更新行為,它不可能沒有對受教育者的要求和限制,盡管這些要求和限制可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體現為不同的方式和內涵。杜威絕對地把教育的外在目的和內在目的對立起來,在批判傳統教育的弊端方面,確實有它積極的建設性意義,但把教育的外部目的絕對地假定為與學生的實際情況和需要相反的、至少是完全不相適應的東西,這樣的說法無疑欠妥,而且從思維方式上講,他試圖消弭教育中存在的二元對立,卻最終又陷入了二元對立的窠臼之中。
其次,杜威“教育即生長”的目的論,給學校教育帶來的最大的挑戰是教師問題。作為理論,它是教育史上的重大突破,但從實踐的角度看,它又無疑是失敗的。從學生立場出發,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參與度和學生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對發揮學生積極性、主動性、獨立性、培養合作意識和能力意義重大;但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則不但退出了“中心”地位,而且逐漸淡出,成為學生活動的觀察者和輔助者,教學活動的指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淡化或失去了方向性。
同時,他也忽視了教育、教學活動對于教師的生命意義,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完全異化成了工具。在“教師與學生”“教材與經驗”和“課堂與活動”幾個方面,他與赫爾巴特是站在二元對立的兩個極端,他批判赫爾巴特的觀點的缺陷,卻忽視了審視其對立面也可能存在的不足。他的以經驗為中心的教材理念,增加了學生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的聯系,但隨意性較大,因而經常被批評“缺乏系統性”,甚至導致一部分受這種學校教育的學生抱怨自己是“沒有讀過書的人”。對實踐過程中不斷反映出來的問題,杜威試圖進行修正,在晚年所著的《經驗與教育》中指出:“經驗和教育不能直接相等”,教師要根據經驗對當前活動的效用、還要根據經驗對未來生長的影響,來對兒童的經驗進行選擇;同時,他還把經驗的內容從個體性的范疇擴大到社會性的范疇,強調教師對群體負有責任,那就是他們必須有超前性的理解,根據社會方向去領導兒童,把兒童現實生長的連續性和他們的未來銜接起來。要有效地完成這個任務,教師既需要是心理學專家、社會問題專家,也必須是教育學專家和教材問題的專家。他對教師委以如此重任,而教師是否有能力和可能完成這樣的重任,則又是他無力顧及的問題了;這無疑導致他教育理論實踐一翼的殘損。美國教育哲學家喬·R.伯內特對杜威的教育理論曾經有過這樣的評論:“杜威的教育學在當時或現在,不可能在學校中得到廣泛應用。因為從來就沒有培訓過進行這種教育的教師,學校也沒有這方面的人力物力,家長和政客們也不支持杜威的教育學。”[5](P.187)永恒主義教育哲學主要代表人物赫欽斯也曾經說過,“在今天的任何教育制度中,我知道沒有一個蘇格拉底。我們不得不根據普通教師的能力來設計美國的中小學、學院和大學的課程”,[6](P.11)對這一缺憾,杜威在晚年也有過明確地表示。
第三,從教育與社會關系上來說,杜威沒有關注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互動作用,單方面強調教育對于社會改造的作用,完全否定來自社會的外部教育目的,走向了問題的另一個極端。教育存在于社會之中,它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的影響和需求,簡單地排斥外部的教育目的將使整個教育活動舉步維艱。杜威以個別的、具體的教育目的否定一般、抽象的教育目的,并非消除了對立,只是掩蓋了對立中的一極,否定了兩者之間的關系、聯系、層次、互補、轉化的可能與途徑,體現了他的教育目的論脫離教育和社會實踐的理想主義特征。
最后,從總體看,杜威的教育目的論具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氣息。杜威首先是一位哲學家,其次才是一位教育家,他把教育作為哲學思想的試驗田,作為實現他社會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卻在一定意義上忽視了教育自身的獨特性以及系統知識在人的個性化和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1957年前蘇聯科學實驗衛星上天,給屢受責難的進步教育理論以致命的一擊,此后一度勃興的要素主義、永恒主義等教育思潮以及1958年《國防教育法》的頒布,基本上否定了進步教育的主張,杜威的教育理論也在二戰之后的美國教育界和社會上飽受詬病。
然而,歷史不會遺落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杜威的教育理論雖然不再有昔日的風光,但它在現代世界范圍內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上的影響,一直不絕如縷,這正體現了杜威教育理論的生命力,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學上給后人在認識廣度、深度、角度、維度上的拓展和思維方式上的啟發與教益,在教育史上是少有人與之比肩的。
[1]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孫有中.美國精神的象征——杜威社會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約翰·杜威.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M].孫有中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4]葉瀾.基因-“生命·實踐”教育學引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喬·R.伯內特.如何評價杜威[M]//陳友松.當代西方教育哲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
[6]赫欽斯.民主社會中教育上的沖突[M].陸有銓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