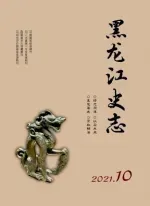黑龍江冰雪文化禮贊(四十七):馬背上的英雄民族蒙古族
龔 強
(六)蒙古族的音樂
蒙古族是一個酷愛音樂又能歌善舞的民族,因此,素有“音樂民族”、“詩歌民族”之稱。蒙古民族的音樂歷史悠久,其內容也極為豐富。據歷史文獻記載,成吉思汗曾“征用舊樂于西夏”。元太宗窩闊臺于十年(1238年)曾征集燕京和南京的金朝遺樂和樂官。元憲宗蒙哥于即位后第二年(1252年)三月,下令制作鐘磬、,始用登歌樂祀天于日月山。元世祖忽必烈在藩邸時,命宋周臣管理樂工。即位后,于中統元年(1260年)用登歌樂祭祖。又命王鏞作《大成樂》,并制作了一整套元朝宮廷樂器。明代時,蒙古封建牧主進行歌舞仍以蒙古樂器演奏。清代時,宮廷中所演奏的蒙古樂曲,也是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時期的。其樂器有笳、管、箏、琶、弦、阮、火不思等。清政府還設有管理蒙古樂曲的什榜處。
縱觀蒙古族音樂傳承的脈絡,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發展時期,即山林狩獵音樂文化時期、草原游牧音樂文化時期、亦農亦牧音樂文化時期。
在山林狩獵音樂文化時期,其音樂風格以短調為代表,特點是結構短小、音調簡潔、節奏明了、詞多腔少。整體音樂風格具有敘述性與歌舞性,抒情性較弱,這也是原始時期人類音樂藝術的共同特征。一些明顯帶有這一時期音樂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間流傳,如《追獵斗智歌》、《白海青舞》。
伴隨著狩獵生產方式向游牧生產方式的轉變,第二個時期的音樂風格也發生了從短調民歌向長調民歌風格上的演變,形成了蒙古族音樂史上的草原游牧音樂文化時期。從公元7世紀至公元17世紀的千年歷史中,蒙古族民歌發展的總趨勢可概括為:以短調民歌為基礎,以長調民歌為創新,長調民歌逐漸占主導地位的時期,也是蒙古族整體音樂文化風格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
大約自公元18世紀(清朝中后期)以后,北方草原與中原內地的聯系進一步增強,各民族間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文化交流更為頻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短調敘事歌、長篇說唱歌曲等得到了新的發展,形成了蒙古族亦農亦牧音樂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的音樂風格特征可概括為:短調民歌重獲新生快速發展,長調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
1.蒙古族民歌
蒙古民歌具有民族聲樂獨有的風格和魅力,不論高亢嘹亮,還是低吟回蕩,都充分表現了蒙古族人民質樸、爽朗、熱情、豪放的性格。蒙古民歌洋洋灑灑,浩如煙海,其品位之高,數量之巨,令世人嘆為觀止。蒙古族民歌可分為長調民歌和短調民歌兩種。具體地說主要有狩獵歌、牧歌、贊歌、思鄉曲、禮俗歌、短歌、敘事歌、搖兒歌和兒歌等。蒙古族民歌以聲音宏大雄渾、曲調高亢悠揚而聞名。其內容非常豐富,有描寫愛情和娶親嫁女的,有贊頌駿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頌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這些民歌生動地反映蒙古社會的風土人情。
(1)長調民歌
蒙古人有三件寶:草原、駿馬和長調,這三件寶是其精神家園的主干。長調歌詞絕大多數描寫的是草原、駿馬、駱駝、牛羊、藍天、白云、江河和湖泊等自然景物,也有歌唱愛情的。
蒙古族主要生活在遼闊的草原,這一獨特的居住環境,孕育出長調這種民族特色濃厚且震撼心靈的演唱形式。蒙古長調旋律優美,韻味獨特,透射出蒙古人開闊的胸襟。長調民歌是蒙古族音樂之魂,它與草原、與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承載著蒙古民族的歷史,其高亢悠遠的風格宜于敘事,又長于抒情,是蒙古民族生產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標志性展示。
2005年11月25日,“蒙古族長調民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第三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這充分顯現了蒙古族長調民歌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其不可估量的藝術性及世界性的價值。
長調民歌節奏舒緩自由,字少腔長,且因地區不同而風格各異。錫林郭勒草原的長調民歌聲音嘹亮悠長,流行的有《小黃馬》、《走馬》等。呼倫貝爾草原的長調民歌則熱情奔放,有《遼闊的草原》、《盜馬姑娘》等。阿拉善地區的民歌節奏緩慢,流行的有《富饒遼闊的阿拉善》、《辭行》等。科爾沁草原的民歌以抒情為主,流行的有《思鄉曲》、《威風矯健的馬》等。昭烏達草原民歌富有朝氣,流行的有《翠玲》、《孟陽》等。
長調一般為上、下各兩句歌詞,演唱者根據生活積累和對自然的感悟來發揮,在一些長音的演唱上,可以根據演唱者的情緒自由延長,從旋律風格及唱腔上具有遼闊、豪爽、粗獷的草原民歌特色。長調民歌的襯詞是“嗒咿”、“咿喲”等。高音的襯詞一般為開口音或半開口音,中音的襯詞較靈活,結尾處的襯詞一般是半開口音或閉口音。長調在馬頭琴伴奏下更具韻味,如同引起人們無限遐想的白云一樣,飄動在草原上空。
長調民歌有其深刻的文化、藝術價值。“他的歌聲橫過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動,地上的風忘了呼吸;氈房里火爐旁的老人忽然間想起過去的時光,草地上擠牛奶的少女忽然間忘記置身何處;所有的心,所有靈魂都隨著他的歌聲在曠野里上下回旋飛翔,久久不肯回來……”這是著名詩人席慕蓉在1996年拜訪一代長調歌王哈扎布后,為其演唱的蒙古族長調而深深傾倒,即興寫下的贊文。
筆者作為地質測繪隊員,長期工作、生活在野外,在內蒙古大草原上曾經聽過長調,深為其藝術魅力所感染。傾心聽一曲悠揚的長調牧歌,猶如站在蒼茫草原聆聽大自然的傾訴,而眼前常常會呈現這樣一幅畫面:碧綠的草原,蒼茫遼闊,它的盡頭與天合一。白云朵朵懸于藍天靜靜地浮動著,牛羊悠閑地吃草,乳白色的蒙古包群像是撒落在翡翠盤里的珍珠。夕陽西下,遠山披上了晚霞的彩衣,牛羊如同鍍上了一層金邊,天邊的云朵也變成了火焰一般鮮紅。此時耳邊響起蒙古族長調,高亢悠遠、舒緩自由,既敘事,又抒情,表達著草原兒女獨有的深情。這種藝術境界無疑是“天籟與心籟的完美統一”,而美學家則稱之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統一”。此時再有伴著長調的呼麥(一種“喉音”藝術。運用特殊的聲音技巧,一人同時唱出兩個聲部。后面專門介紹),一人領唱長調旋律,三五個人以持續低音“潮爾”,就會產生莊嚴肅穆、聲勢浩大、輝煌壯麗的氣勢;如果再加上一首馬頭琴曲,就會有排山倒海之氣概。長調伴以呼麥和馬頭琴,能使人產生一種雄渾壯美的崇高體驗。
“呼麥”又名“浩林·潮爾”,是蒙古族和聲唱法潮爾(chor)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種“喉音”藝術。運用特殊的聲音技巧,一人同時唱出兩個聲部,此外,還可以伴以口哨聲音,形成罕見的多聲部形態。演唱者運用閉氣技巧,使氣息猛烈沖擊聲帶,發出粗壯的氣泡音,形成低音聲部。在此基礎上,巧妙調節口腔共鳴,強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帶有金屬聲的高音聲部,獲得美妙的聲音效果。
有關呼麥的產生,蒙古人有一種傳奇的說法:古代先民在深山中活動,見河汊分流,瀑布飛瀉,山鳴谷應,動人心魄,聲聞數十里,便加以模仿,遂產生了呼麥。新疆阿爾泰山區的蒙古人中,至今尚有呼麥流傳。呼麥的曲目大體有以下三種類型:一是詠唱美麗的自然風光,諸如《阿爾泰山頌》、《額布河流水》之類;二是表現和模擬野生動物的可愛形象,如《布谷鳥》、《黑走熊》之類,保留著山林狩獵文化時期的音樂遺存;三是贊美駿馬和草原,如《四歲的海騮馬》等。從其音樂風格來說,呼麥以短調音樂為主,但也能演唱些簡短的長調歌曲。從呼麥產生的傳說,以及曲目的題材內容來看,“喉音”這一演唱形式,應該是蒙古山林狩獵文化時期的產物。
長調牧歌的典范之作《遼闊的草原》,音樂語言、曲式結構簡潔精煉,全曲只上下兩個對偶樂句旋律,但卻熱情奔放,達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統一,同樣給人以遼闊、豪放的陽剛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個美》,僅在一首單樂段淳樸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個美的事物。歌中列舉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駿馬、候鳥鴻雁、陽光云靄、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風光、怒放的鮮花、清澈的流水、彈撥的琴弦、嘹亮的歌聲、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義、長者的訓導、天下的太平……這種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獨特意境和神韻,在人類進入大工業時代,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今天,更凸顯出蒙古族長調民歌高度的美學價值。
愛是長調的基本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愛就沒有人類世界,也難以產生藝術。但因各民族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及生存環境的差異等,對愛的表達方式自然不會一致。蒙古族的生存環境歷來是地廣人稀,加之游牧的獨特生活方式,使他們對愛有著自己的思考和表達方式,長調民歌即是在這種愛的原動力作用之下產生與發展的。因此,長調民歌中無時無刻不體現著這種愛的本質與內涵,這也恰是長調民歌的生命力之所在。
在長調藝術史上大師輩出。一代歌王哈扎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聲國內外,其《小黃馬》高音區的演唱令人拍案叫絕。1955年,“長調歌王”寶音德力格爾以一曲《遼闊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奪得金牌。20世紀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爾多斯長調民間歌手扎木蘇震驚了北京舞臺,許多專家高興地稱贊為“草原美聲唱法”。90年代初,80多歲的扎木蘇歌喉依舊,顯示出堅實而科學的歌唱功底。這充分說明,長調演唱藝術不僅有其獨特的美學本質及其風格,而且具有獨特而科學的歌唱技術。
(2)短調民歌
短調民歌簡稱短調,是最早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歌體裁。主要在東部蒙古族中盛行。愛情歌曲在短調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森吉德瑪》、《達古拉》、《小情人》等,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其次,反映蒙古族人民反抗侵略,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行徑,以及在革命斗爭中產生的革命民歌,如《獨歸龍》、《反日歌》等都是短調民歌的代表作。
與長調民歌明顯不同的是,短調一般是兩行,有韻的兩句式或四句式,節拍比較固定。歌詞簡單,但不呆板,其特點在音韻上廣泛運用疊字。短調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漢雜居的半農半牧區。往往是即興歌唱,靈活性很強。在草原上流行的有《錫巴喇嘛》、《成吉思汗的兩匹青馬》、《美酒醇如香蜜》、《拉駱駝的哥哥十二屬相》等。
獵歌:來源于原始狩獵歌舞,有時是寓言性的動物敘事歌。蒙古族獵歌經常與舞蹈或表演相結合,內容大多直接模擬古代獵人們的勞動生活或模仿各種飛禽走獸的動作神態,如流行的《追獵斗智歌》、《海青拿天鵝》等,多為兩人分別扮演獵人和動物,模仿獵人和動物的動作神態,代表作有呼倫貝爾盟的民歌《小白兔》、《三百六十只黃羊》等。
牧歌:牧歌以歌唱草原、贊美駿馬、贊美生活,充滿對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等為其主要內容。牧歌的歌詞既善于抒情,又注重寫景,情景交融,表現人和大自然的和諧關系。所謂蒙古族音樂的草原風格就是指牧歌風格。牧歌的曲調高亢、嘹亮、寬闊、舒展,節奏悠長,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節奏。一般情況下,牧歌的上行樂句節奏悠長徐緩,而下行樂句則往往采用活躍跳蕩的三連音節奏,形成絢麗的華彩樂句。草原牧歌這一獨特民歌體裁及其風格的形成,對蒙古族民歌的各個領域如頌歌、宴歌、思鄉曲、婚禮歌、情歌乃至器樂曲,均產生了巨大影響。
贊歌:其內容主要是歌頌蒙古族歷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贊美家鄉的山川湖泊,贊美駿馬牛肥羊壯等。多在那達慕大會或其他集會、慶典等特定場合演唱。如《成吉思汗頌歌》、《遼闊清秀的故鄉》、《西遼河頌》等。贊歌的曲調簡潔有力,節奏規整鮮明,較少華彩性裝飾音。旋律的起伏不如草原牧歌大。演唱形式有獨唱、齊唱、重唱與合唱。有些古老的贊歌,還有簡單的和聲。這種民間合唱即前面提及的“潮爾”,由兩名男歌手演唱,男低音唱出粗獷的固定低音,男高音則演唱悠長的曲調。
思鄉曲:蒙古族民歌中極為普遍的一種形式,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蒙古族享有盛譽的《母子歌》、《阿萊欽伯之歌》等,便是窩闊臺汗時期的思鄉曲。思鄉曲的內容有兩類,一類是武士思鄉曲,即指從軍出征,在外作戰的蒙古武士們所唱的懷念故鄉的歌曲。如錫林郭勒盟民歌《曠野中的蓮松樹》。另一種是婦女思鄉曲,即遠嫁他鄉的青年女子所唱的思念故鄉親人之歌。如科爾沁民歌《諾恩吉婭》等。思鄉曲的藝術性較高,曲調優美流暢,節奏舒展,結構嚴謹,調式運用豐富而大膽,轉調離調手法很多。
禮俗歌:禮俗歌是在特定場合演唱,帶有生活風俗性、實用性的民歌,如宴歌、婚禮歌、安魂曲等。宴歌主要演唱于節日集會、招待賓客的飲宴場合。婚禮歌在婚慶上演唱,曲調熱烈、歡快。這類歌曲數量大,難度高,風格多樣,主人們愿意聘請那些有名望的歌手在結婚儀式上演唱。安魂曲是在舉行葬禮時演唱的。曲調悲切哀婉,莊重肅穆。多為齊唱或合唱。摔跤歌是在那達慕大會上舉行摔跤比賽時演唱的。每當雙方摔跤手跳躍出場時,由男高音歌手領唱,其余人以固定低音式的和聲予以伴唱。
敘事歌:敘事歌產生和發展于內蒙古東部農業地區。曲調簡短,結構規整,帶有濃厚的說唱性。其演唱形式均為自拉自唱,用四胡或馬頭琴等樂器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據情節、刻畫人物的需要,隨時插入評述性的對白。反映的題材主要有歌頌人民起義斗爭和英雄人物的,如《嘎達梅林》、《英雄陶克圖之歌》等。表現愛情悲劇故事的,如《諾麗格爾瑪》、《達那巴拉》等。反對宗教束縛,向往世俗生活的,如《東克爾大喇嘛》、《寶音賀西格大喇嘛》等。
黑龍江地區的蒙古族,因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不同,習慣唱短調歌曲。宴歌中以祝酒歌為最,如《天上的風》、《喜宴歌》、《祝酒歌》等;情歌中以遠嫁最多,如《諾恩吉婭》、《達拉古》、《九十玲》等;贊歌中以贊馬為主,如《我的駿馬》、《棗紅馬》、《海騮馬》等,此外,還有許多宗教歌曲。黑龍江的蒙古族民歌多達千余首。目前已出版了《黑龍江傳統民歌集》和《黑龍江蒙古民歌選》。解放后,新民歌的創作蓬勃發展,如《富饒的杜爾伯特》、《牧民一步一層樓》、《草原戀歌》等在群眾中廣為傳唱,許多還在舞臺上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