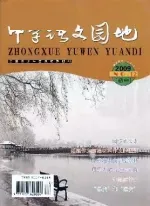論生命教育的場(chǎng)域——基于語文教學(xué)的視角
楊定勝 楊定云
[作者通聯(lián):楊定勝,玉溪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楊定云,云南騰沖縣曲石中學(xué)]
生命的產(chǎn)生、存在及其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問題一直伴隨在教育過程中,因?yàn)榻逃哪康闹苯又赶蛉说陌l(fā)展。“生命是教育之本,是教育存在的根本性依據(jù),離開了生命,再發(fā)達(dá)、再繁榮、再重要的教育,都因?yàn)槭チ烁荆鴨适Ы逃谋菊妗!雹俣裉煳覀冇址磸?fù)地強(qiáng)調(diào)生命教育,是因?yàn)槟壳暗慕逃霈F(xiàn)了一些異化現(xiàn)象:第一,在教學(xué)內(nèi)容上注重知識(shí)的識(shí)記而輕視理解和運(yùn)用,注重技能訓(xùn)練而忽視了學(xué)生的意愿和態(tài)度問題,注重理性思維訓(xùn)練而忽視生命體驗(yàn);第二,在教學(xué)方式上,重灌輸而輕理解,重分析而輕感悟;第三,在教學(xué)的價(jià)值取向上,重結(jié)果而輕過程,重考試對(duì)于將來生活的重要意義,而輕視學(xué)生當(dāng)前生活的獨(dú)特意義。在這樣的教育價(jià)值取向下,學(xué)生成為了知識(shí)的容器,訓(xùn)練的工具,思想和情感被忽視,生命價(jià)值被漠視。因此,在課程改革背景下實(shí)施生命教育具有重大意義。生命教育是一項(xiàng)復(fù)雜的工程,它涉及到四個(gè)方面的場(chǎng)域問題。
一、生命教育的內(nèi)部場(chǎng)域
人的生命是通過生活表現(xiàn)出來的,但不能簡(jiǎn)單理解為“活著”的狀態(tài)。他不僅是人生理機(jī)能的新陳代謝,而且內(nèi)部有一個(gè)復(fù)雜的場(chǎng)域:機(jī)體、心理、情感、思想、政治與倫理。因此,生命教育關(guān)注人生命本身的復(fù)雜性,了解其內(nèi)部場(chǎng)域的各種要素,進(jìn)而才能通過外在的生命活動(dòng)現(xiàn)象認(rèn)識(shí)它自身。認(rèn)識(shí)生命的內(nèi)部系統(tǒng)價(jià)值何在?可以通過學(xué)生現(xiàn)在的一些反映來認(rèn)識(shí)其生命的存在狀態(tài)。
學(xué)生個(gè)體生命內(nèi)部場(chǎng)域的因素如何激發(fā)呢?我們可以通過肖川先生所說的一個(gè)案例來認(rèn)識(shí)這個(gè)問題。
有一個(gè)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中:國(guó)人心中為什么有那么多仇恨?素不相識(shí)的人們往往因?yàn)橐稽c(diǎn)點(diǎn)摩擦和沖突,而拳腳相向大打出手,甚至欲置對(duì)方于死地。依我個(gè)人體驗(yàn),我覺得是因?yàn)樯钪械臉O不便利,在人們心中積累著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消極情緒,一旦有契機(jī)能發(fā)泄,就會(huì)像火山一樣噴發(fā)。而生活極其的不便,又是因?yàn)榇蠹已壑兄挥凶约旱睦妫苌贋樗酥耄瑖?yán)重缺失人文關(guān)懷。
——肖川《讓教育充滿生命情懷》②
上面談到了部分國(guó)人丑陋的一面,以及這些丑陋產(chǎn)生的原因。其實(shí)涉及到了生命的內(nèi)部系統(tǒng)要素,以及這些要素被激發(fā)的外界因素。有機(jī)體做出的行為受心智的影響,源自于內(nèi)心的消極情緒,而消極情緒又源自于生活中的不便利。從這些系統(tǒng)要素的彼此關(guān)系來看,情感、思想、行為、心理都組成了生命的復(fù)雜體,雖然觸發(fā)因素是社會(huì)生活中的“不便利”,其實(shí)是源自他們狹隘和自私的內(nèi)心。
這個(gè)案例反映的是我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反映的是生命在生活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文學(xué)是生活的反映,類似的問題其實(shí)已出現(xiàn)在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魯迅先生在《孔乙己》中就關(guān)注到了國(guó)人生命內(nèi)部場(chǎng)域中丑陋的一面。孔乙己本來和穿短衫站著喝酒的人一樣,都屬于社會(huì)上的弱勢(shì)群體,相互之間本應(yīng)“同病相憐”,但孔乙己卻受到他們的嘲笑,而孔乙己也不愿與他們?yōu)槲椋瑤в兄R(shí)分子對(duì)勞工的鄙視心理。其實(shí),在孔乙己的生命內(nèi)部場(chǎng)域中有善良、仁愛的一面,體現(xiàn)在他分茴香豆給小孩子吃上,也體現(xiàn)在他教“我”寫字上,但是小孩子也取笑他,社會(huì)大眾身上的冷漠心理已通過環(huán)境遺傳到了下一代身上,這才是深層次的悲哀。在作者塑造的群像里面,大家都是冷漠之人,沒有寬容,沒有同情,只有著一顆顆冷漠的心。
如果個(gè)體不懂得寬容和理解,就不會(huì)尊重別人的生命。生命教育一定要了解生命本身的復(fù)雜性,從外部行為看內(nèi)心世界,培養(yǎng)學(xué)生健康的心理、謙遜的品質(zhì)和仁愛之心。
二、生命教育的文化場(chǎng)域
人從出生到死亡都處在一定的社會(huì)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家庭和社會(huì)都在人身上打下文化的烙印。無論是卡西爾的“人是符號(hào)的動(dòng)物”,還是帕斯卡的“人是思想的蘆葦”,都表明了文化是融在人的生命中的。雖然文化的定義多種多樣,但是我們可以從兩個(gè)方面來認(rèn)識(shí):其一,文化指人類對(duì)自然的認(rèn)識(shí)、改造及其成果;其二,“文化指人類對(duì)人類社會(huì)和自身世界的認(rèn)識(shí)、理解、改造和建構(gòu)。”③人并不是一出生就具有了文化,而是在后天的家庭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慢慢養(yǎng)成的,教育就是通過向個(gè)體傳授知識(shí)與文化,使個(gè)體生命融入到周圍的文化環(huán)境中,并逐漸地適應(yīng)文化。文化一經(jīng)進(jìn)入生命,就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影響因素,而是成為生命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生命教育一定要將結(jié)合在生命中的文化因素作為主要內(nèi)容,因?yàn)槲幕膬r(jià)值取向常常決定教育所要培養(yǎng)的人的規(guī)格和質(zhì)量。因此,文化場(chǎng)域決定生命教育的質(zhì)量,而文化場(chǎng)域主要包括這樣幾個(gè)方面:
1.歷史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場(chǎng)域
人類常常有一種尋根的文化心理,常常想考證自己先祖的事跡和精神,從而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找到精神的皈依,于是就有了“祖先崇拜”。歷史文化在傳承的過程中,有的內(nèi)容長(zhǎng)期規(guī)約著人們的行為,并為人民所接受并代代傳承下去,成為我們傳統(tǒng)的東西,于是部分歷史文化就轉(zhuǎn)變成了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文化影響著當(dāng)代人的生活,比如倫理文化。中國(guó)是一個(gè)禮儀的國(guó)度,這套禮儀是在儒家文化長(zhǎng)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歷史中形成的,它滋養(yǎng)著我們?nèi)A夏民族的精神,也影響著國(guó)人的生活方式。由于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社會(huì)特殊的歷史境遇,傳統(tǒng)文化在發(fā)展過程中有過中斷和變異,于是導(dǎo)致部分人的生命系統(tǒng)缺失了生命意識(shí)。下面的新聞就很能說明這個(gè)問題。
一名20歲在校大學(xué)生,杭州市內(nèi)超速飚車,結(jié)果在人行橫道線上撞死一名25歲白領(lǐng)青年。駕車者的朋友面對(duì)慘劇,非但毫無驚悚,反而說笑一旁。這條新聞,除了再次教人領(lǐng)會(huì)生命的脆弱外,更折射出一些人對(duì)他人生命的漠視和踐踏,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信息來源:《解放日?qǐng)?bào)》2009年05月14日)
新聞體現(xiàn)的是當(dāng)代部分大學(xué)生對(duì)生命的漠視,反映出在這名大學(xué)生的生命中缺乏悲憫情懷和社會(huì)責(zé)任感。由此觀之,傳統(tǒng)文化在這些人身上已經(jīng)消失,因?yàn)闊o論是儒家還是墨家,都是尊重人的生命的,特別是儒家將社會(huì)責(zé)任感化成知識(shí)分子的生命意識(shí)。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古代知識(shí)分子身上體現(xiàn)出三種文化:儒、道、釋。儒家思想要求人要敢于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并化責(zé)任感為憂國(guó)憂民的生命精神;道家講究個(gè)人的修心,提升個(gè)體的生命品質(zhì),以“圣之清者”為目標(biāo);佛家講“因果輪回”,盡管對(duì)人的精神有一定的麻痹作用,但它引導(dǎo)人的生命走向“善”的維度。佛家也講“普渡眾生”,其實(shí)是從抽象的精神層面引導(dǎo)信徒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培養(yǎng)社會(huì)責(zé)任感。
文化具有“化人”的功能,所以,生命教育應(yīng)注重文化場(chǎng)域,讓傳統(tǒng)文化滋養(yǎng)學(xué)生的生命,學(xué)生才能綻放出多姿的生命之光。
2.民族文化場(chǎng)域
人的生命是具有民族性的,因?yàn)閭€(gè)體需要?dú)w屬感,這與馬斯洛的“需要理論”人有歸屬感的需要相吻合。民族文化體現(xiàn)人的精神生命的歸屬,不同的民族文化滋養(yǎng)出不同的生命個(gè)體。中國(guó)文人在情感深處有“傷春悲秋”的意識(shí),傷春多與愛情有關(guān),悲秋多與感嘆易逝的生命有關(guān),這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對(duì)自然和社會(huì)的認(rèn)知方式,總結(jié)來說就是情感與生命的延續(xù)問題,這既是生命的內(nèi)部場(chǎng)域,同時(shí)也是生命的文化場(chǎng)域。比如關(guān)于杜鵑鳥啼聲的認(rèn)識(shí),中國(guó)文學(xué)中有“杜鵑啼血”一說,中國(guó)人聽到杜鵑的叫聲時(shí)有一種悲傷的感覺,而西方人覺得杜鵑的啼聲是歡快的,其實(shí)是兩個(gè)民族對(duì)于生命的不同理解。這說明民族文化對(duì)個(gè)體生命具有塑造作用,生命教育不可忽視民族文化場(chǎng)域。
3.“他律型”的社會(huì)文化場(chǎng)域
學(xué)者一般認(rèn)為西方的社會(huì)文化是“自律型”的,中國(guó)的是“他律型”的,前者注重生命的個(gè)性發(fā)展,后者注重的是生命的群體性特征。當(dāng)探討中國(guó)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為何不如西方人時(shí),往往將原因歸咎于“他律型”的文化上,這是有失公允的。“他律型”的文化按照社會(huì)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人的行為,能引導(dǎo)個(gè)體生命走向“禮”與“德”,利于培養(yǎng)有教養(yǎng)的人。生命價(jià)值觀念受周圍社會(huì)因素的影響,因此生命觀念也會(huì)有所不同,在生命教育中最好是將“自律型”與“他律型”結(jié)合起來。
生命個(gè)體對(duì)文化具有選擇權(quán),所以教育者的工作目的不是灌輸文化,而是幫助學(xué)生理解文化,然后學(xué)會(huì)選擇文化,最終完成精神生命的建構(gòu)。
三、生命教育的實(shí)踐場(chǎng)域
1.課堂教學(xué)實(shí)踐場(chǎng)域
學(xué)校是最重要的教育場(chǎng)所,學(xué)生在學(xué)校里度過的時(shí)間最多,而課堂教學(xué)是學(xué)校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因此,課堂教學(xué)應(yīng)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場(chǎng)域。在課堂上,教師應(yīng)當(dāng)以教材為依托,引導(dǎo)學(xué)生感悟生命。
下面是筆者于2009年上半年在華寧縣通紅甸中學(xué)支教時(shí)的一個(gè)課例,和學(xué)生一起分析品味陸游的《卜算子·詠梅》:
師:在陸游筆下塑造了一株什么樣的梅花?
生1:不屈的。
生2:凄苦的。
生3:悲涼的……
師:有同學(xué)說是不屈的,你們是從哪里看出來的呀?
生:“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師:也有同學(xué)說是凄苦的,又從哪里看出來呢?
生1:它長(zhǎng)在斷橋邊,不易被人發(fā)現(xiàn)……
生2:它“開無主”,沒有人欣賞……
生3:它是寂寞的……
……
師:現(xiàn)在我們來總結(jié)一下大家的感悟。梅花是凄苦的,第一層是出身不好,長(zhǎng)在驛外斷橋邊,無人欣賞,像陸游考上進(jìn)士,卻因名次排在秦檜孫子之前而不被錄用。第二層苦是寂寞無知音,不知為誰開,遠(yuǎn)大的抱負(fù)沒人理解。第三層苦……第四層苦是,還受到了風(fēng)雨的摧殘,陸游當(dāng)時(shí)不停地受到朝庭主和派的排擠……
(此時(shí),一個(gè)女孩子眼淚汪汪,呆呆地出神,我不禁詫異。下課時(shí)我找時(shí)機(jī)單獨(dú)與她談,她說:“老師,我是從梅花的身世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我也像梅花一樣出身不好,家里窮困家人多病,生活費(fèi)都很難湊,來到學(xué)校里,像風(fēng)雨摧殘一樣地受到同學(xué)的嘲笑……”我聽后也很難過,開導(dǎo)她要像不屈的梅花那樣堅(jiān)強(qiáng)地生活。)
那次上課,筆者感覺到課堂教學(xué)可以成為學(xué)生生命教育的重要場(chǎng)域。其實(shí),在那次課上,主要展示的是作者的生命,但是學(xué)生通過對(duì)課文的理解,聯(lián)想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凄苦,也理解了父母生存的艱辛,實(shí)現(xiàn)了情感、態(tài)度和價(jià)值觀目標(biāo)。
2.班級(jí)與家庭生活場(chǎng)域
班級(jí)生活中充滿了學(xué)生與學(xué)生、學(xué)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dòng)與交流,而互動(dòng)與交流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方式,因?yàn)閷W(xué)生在交往過程中確證自己的生命存在和價(jià)值。因此,老師要在班上樹立平等意識(shí),首先是師生平等,老師不得打罵或體罰學(xué)生,要關(guān)心和呵護(hù)學(xué)生,讓學(xué)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其次,建設(shè)團(tuán)結(jié)友愛的班風(fēng),同學(xué)之間要寬容,家庭富裕的同學(xué)不能取笑貧困學(xué)生,不給同學(xué)起外號(hào),不挖苦諷刺身體有缺陷的學(xué)生。在一個(gè)人的人格形成期,如果有過嚴(yán)重地被人欺侮或欺侮別人的經(jīng)歷,就不太容易形成正直、光明、健康的人格。只有在充滿溫情與仁愛的氛圍中,才能生長(zhǎng)出和煦、細(xì)膩、體貼的心靈。最終讓學(xué)生學(xué)會(huì)尊重他人的生命,豐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格。
家庭教育對(duì)于學(xué)生的生命教育也非常重要,一方面,父母的人格氣質(zhì)影響著學(xué)生,長(zhǎng)輩的為人處世也會(huì)影響學(xué)生的生活觀。家長(zhǎng)應(yīng)給孩子講社會(huì)中的人和事,并進(jìn)行安全、責(zé)任意識(shí)等方面的教育,讓學(xué)生學(xué)會(huì)在現(xiàn)實(shí)中生活,體現(xiàn)出生命教育的時(shí)代性。家長(zhǎng)也可以給孩子講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讓孩子感覺到豐富的人文精神,在歷史中與古人的精神相遇,從而體現(xiàn)出生命教育的歷史性。
四、生命教育的規(guī)約場(chǎng)域
生命教育要求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的自主性,給學(xué)生以生命的自由,讓他們充滿想象展翅飛翔。在新課改后,許多教師看似都能做到充分地尊重學(xué)生的生命,集中表現(xiàn)在尊重學(xué)生的理解和感悟上,不隨意地否定學(xué)生。但是也容易走向放任自流的極端。下面的課例也是剛才曾舉過的《卜算子·詠梅》,我們看看另一個(gè)學(xué)生在課堂上的表現(xiàn)。
師:哪位同學(xué)能談?wù)勀銓?duì)“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的理解?
(一生自覺舉手并踴躍站起,我很高興這位學(xué)生積極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就讓他談理解。)
生:梅花很寂寞,想開開門找人斗地主。
(學(xué)生邊說邊用眼看周圍的同學(xué),一臉地笑著,話音剛落,教室里笑聲響起,回答問題的學(xué)生臉上浮現(xiàn)得意之色。)
本來我想給學(xué)生充分展示自我的機(jī)會(huì),也想讓他認(rèn)識(shí)自己生命價(jià)值的存在,結(jié)果卻發(fā)現(xiàn)他的回答和表情是在嘩眾取寵。從理性的角度看,該同學(xué)對(duì)生命個(gè)性的了解呈膚淺化的狀態(tài),沒有很好地認(rèn)識(shí)到老師對(duì)他的尊重;其次,這位同學(xué)把自己生命的價(jià)值放在取悅別人上,這種生命價(jià)值觀是不正確的。此時(shí),老師應(yīng)該怎么辦?是放任學(xué)生嗎?如果不進(jìn)行否定,那才是真正對(duì)學(xué)生生命的不尊重,教師需要在方向上進(jìn)行引導(dǎo)。
從這個(gè)案例可看出,學(xué)生的生命需要被尊重,需要自主和自由,但是同時(shí)也需要規(guī)約和限制,限制錯(cuò)誤的理解,規(guī)約生命發(fā)展的方向。生命的自主、自由和規(guī)約性會(huì)出現(xiàn)矛盾的一面,這里就需要教師結(jié)合學(xué)生特點(diǎn)進(jìn)行引導(dǎo)。
生命教育有時(shí)會(huì)走入誤區(qū),因?yàn)槿藗儗?duì)自身的認(rèn)識(shí)常常是抽象的、符號(hào)化的,而人的生命活動(dòng)卻是具體的、感性的。生命是理性與感性的結(jié)合體,理性使人全面認(rèn)識(shí)自己,確定方向;感性使人詩(shī)意的生活,只有關(guān)注到內(nèi)部場(chǎng)域、文化場(chǎng)域、實(shí)踐場(chǎng)域和規(guī)約場(chǎng)域的問題,生命教育才會(huì)收到理想的效果。
— — ————
注釋:
①馮建軍:《生命與教育》,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yè)。
②肖川:《教育的使命與責(zé)任》,岳麓書社,2007年版,第49頁(yè)。
③曹明海:《語文教育文化學(xué)》,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