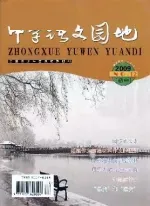評課之后話語文
鄧木輝
[作者通聯:貴州福泉中學]
日前,全州高中語文優質課競賽在我校舉行。所上的課文有高一第一冊(人教版,下同)的《胡同文化》《我有一個夢想》《勸學》《燭之武退秦師》,高二第三冊的《故都的秋》《燈下漫筆》《淚珠與珍珠》《我為什么而活著》《六國論》《游褒禪山記》。每位參賽教師大約有兩星期的準備時間,準備得較充分。競賽中,每位參賽教師均展示了扎實的業務功底和高超的教學技能(特別是嫻熟的多媒體運用技術),注意落實新課改理念,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自主學習與合作探究,較好地激發和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課上得熱鬧而極富觀賞性。這是我作為評委評課之后的最大感受。但也感到有不足之處,如:有的文言文只有架空分析;有的文言文光講語法知識;有的現代文在微觀的關鍵點和宏觀的整體把握上不夠恰當……總之,在教學內容的選取和教學方法的采用等方面還有可商榷之處,它反映了新課改背景下一些深層次的認識問題和觀念問題。下面談談對這些問題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關于教學內容的選取
1.關于文言文教學內容的選取
文言文主要教什么?怎么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有的認為應主要教誦讀,故試圖通過反復誦讀讓學生培養語感,自己感悟;有的認為應主要教語法,故試圖通過知識講解讓學生掌握規律,舉一反三;有的將其等同于現代文,故著重講主題思想、人物形象、結構技巧……這些看法和做法自有其合理之處,但都有明顯弊端。第一種做法忽視了文言文的“文言”特點,且夸大了“誦讀”和“感悟”的作用。文言文不同于現代文,有很多文字障礙,很多文章光靠“誦讀”是不可能“感悟”的,通常是“書讀百遍”而“其義不見”!這類現象很多,不必舉例。既如此,怎一個“讀”字了得?怎一個“悟”字了得?即便是現代文,光“讀”也不能解決問題,適當的講解分析是必要的。關于“讀”和“悟”的局限性,福建師大教授孫紹振在《朗誦不可濫用》(《中學語文教學》2008年第4期,《語文學習》2008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得很透徹、很全面。北京師范大學王寧教授也指出:“光憑語感并不能解決培養語言運用能力的問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很多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理論邏輯,如果完全不從語言方面分析,懸空而無據地感悟,采用完全經驗性的學習,學生是學不會自己分析鑒賞的,更不能達到通過別人的作品來提高自己語言能力的目的。語感不是毫無依托的感悟,不能帶有隨意性,要有理性的理解做基礎。”(《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文教學》,《語文建設》2008年第9期)這些精辟的見解,深刻地論述了缺乏理性理解做基礎的盲目的“讀”和“懸空而無據”的“悟”的局限性,能給我們啟發。第二種做法聚集了文言文“文言”的難點,且未充分估計到學生的知識缺陷。由于教學“淡化語法”,學生語法知識十分欠缺,缺少最起碼的知識基礎,再加上語法知識較抽象難懂,純粹的語法知識講解會將難點集中,不利于學生激發和保持學習興趣。第三種做法偏離了文言文的學習重點,將文言文等同于現代文。文言文學習的主要任務是了解文言文的詞句基礎知識,積累文言詞匯,以便“讀懂”文言文,培養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進而受到思想熏陶,繼承文化遺產,弘揚優秀文化。故文言文學習不宜架空分析,一般不把主題思想、人物形象、結構技巧等作為教學重點(這些主要是現代文教學的任務)。我認為,文言文教學還是“中庸”一點,將幾種做法“結合”起來好些——誦讀不放棄知識講解,誦讀中穿插知識講解;講解與誦讀結合,不滿堂灌“語法知識”;主題思想、人物形象、結構技巧的分析在讀懂文章的基礎上進行,且只作適當點撥,不作重點講解。文言文教學要關注是否“讀懂”,要掃清文字障礙,要分散教學難點,要注意“讀”“譯”結合。“譯”是文言文教學的一個抓手,是宏觀感悟與微觀理解的一個結合點,它“上”可以促進整體感悟,“下”可以促進詞句理解。“譯”可以鞏固知識:在“譯”的過程中,記憶中較熟悉的詞句知識將進一步得到強化與深化。“譯”可以暴露問題:疑難詞句是否理解,關鍵之點是否落實,一“譯”就得到檢驗,問題會暴露無遺。“譯”可以彌補不足:問題一暴露,自然會促使學生針對問題去探究、去詢問,從而彌補不足。“譯”可以分散難點:“譯”不只涉及對詞句語法知識的理解,還將涉及對語句、語段、語篇內容的理解與欣賞,這就避免了只學語法容易產生的繁瑣感、畏難感、枯燥感,分散了教學難點。如果“譯”得準確通暢(信、達、雅),文言文學習的所有問題差不多都能得到解決,更不要說對付考試了。文言文課文,適宜采取讀一讀、譯一譯、議一議的做法。較淺易的語段語篇,以學生自譯為主,教師講解(針對難譯之處)為輔;較難譯的語段語篇,教師可以搞點“串譯”,同時讓學生練習鞏固。筆者主張文言文教學要注重理解,如果能夠,應該做到“字字落實”,只不過要注意“讀”“譯”結合,要注意分散難點。具體論述,參見拙文《文言文教學要注重理解》(《語文教學之友》1998年第4期)。
2.關于現代文教學內容的選取
一篇現代文教什么?王榮生博士將課文分為“定篇”“例文”“樣本”“用件”四類,認為“定篇”是經典文本,應全面掌握,可以處理為“教教材”,其余的可以作為教學憑借“生成”教學內容,應該處理為“用教材教”。我認為,教材中的課文幾乎都是經典文本,幾乎都可以處理為“教教材”,故一般來說,既要讓學生了解“寫什么”,也要讓學生了解“怎樣寫”,即內容形式都要引導學生了解。一般應遵循“點面結合”的原則——“點”即知識點、疑難點、關鍵點,“面”即全文的內容與形式。一方面,要有微觀意識,要關注“點”,備課時要有起碼的語言敏感,對課文中可能是疑難點或關鍵點的地方給予重視,教學中要引導學生關注這些“點”,理解這些“點”,從而提高對文本的解讀和品味的質量。如《胡同文化》中寫北京人易滿足一段:“有窩頭,就知足了。大腌蘿卜,就不錯。小醬蘿卜,那還有什么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蝦米皮熬白菜,嘿!”這個“嘿”字韻味十足,傳神地表達了北京人“易滿足”心理,值得朗讀玩味(宜用升調朗讀);這一段“滿足程度”依次加深,朗讀情感也應逐漸增強;這一段用北京方言土語,寫北京特定的食物風俗,具有濃郁的京腔京味,值得引導學生體味。再如寫北京人“忍”的一段中的“下黃土”,形象地突出了北京文革時期的“亂”,能很好地反襯北京人的“忍”;“睡不著瞇著”也形象地突出北京人的“忍”;“北京人,真有你的!”表達了作者對北京人“忍”的復雜態度……對這些“點”,教學不應忽視,應引導學生體味,從而提高解讀深度和品味質量。再如《故都的秋》中的虛詞及短句的運用,增強了抒情性,烘托了濃濃秋味,教學也不應該忽視……另一方面,要有宏觀意識,要關注“面”,教學要引導學生把握全篇的內容要點與形式特點。如演講詞《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邏輯(集會目的——斗爭策略——夢想內容——呼吁追夢),散文《我為什么而活著》的“總—分—總”結構,散文《淚珠與珍珠》的“串珠式”結構,等等,很有必要引導學生關注,使他們能在作文之中學習、借鑒。
“教教材”與“用教材教”是新課改背景下的一組時髦用語,也可以說是一對矛盾。在“教教材”與“用教材教”的問題上,新課改是主張“用教材教”的。在新課改的強大輿論下,一般來說,“教教材”會被看作傳統觀念,做法保守;而“用教材教”則被看成新潮觀念,做法新穎。故老師們一般來說口頭上會贊成“用教材教”而反對“教教材”,不敢承認自己是在“教教材”,擔憂被譏笑為觀念落后,做法保守。筆者是主張“教教材”的,認為能教好教材就不錯(參見拙文《不應忽視“教教材”》,《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06年第6期》),但很希望看到“用教材教”的課例。但很遺憾,即便是競賽評優課,也沒有看到“用教材教”的課例,所有參賽課都是“教教材”,都是教完課文后搞點拓展延伸,即都是非常傳統和常規的做法。看來,事實上大家比較認可“教教材”,比較熟悉“教教材”;當然,或許因為“用教材教”要求更高,操作更難,大家還欠缺相應的技能。
二、關于教學方法的采用
每位參賽教師方法多樣,特別注重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學生自主探究與合作學習。于是,幾乎每位教師都安排有讓學生分組討論的環節。但這一環節安排的時間多為兩三分鐘,時間太少,很難提出有價值的問題,更談不上深入展開討論。故這一環節質量不高,有效性差,觀賞性大于實效性,象征意義大于實質內容。因此,筆者認為:這一環節要么給足時間,保證質量;要么取消,不必為了體現所謂新課改理念而作秀。平心而論,我們平時看書看報看文章,只需集中精力閱讀文本即可,并不需要任何花哨的形式。高中生的學習也不例外。有疑難問題,他們可以自主探究解決,可以問問老師,可以問問身邊的同學,大可不必一定要前后左右分成若干小組瞎折騰!當然,教師們讓學生“分組”,或許得到專家們的理論指導——我就親耳聽到有的專家主張“分組”,親眼見到有的專家上示范課有“分組”環節;但“分組”到底有何特殊作用,似乎沒有專著或理論文章論及。
“預設”與“生成”也是新課改背景下的一組時髦用語,也可以說是一對矛盾。在“預設”與“生成”的問題上,新課改理論是主張“生成”或主張“預設”與“生成”相結合的,故在新課改的強大輿論下,大多數教師也接受這樣的觀點,不敢單純主張“預設”,唯恐被譏笑為“做法老土”“觀念落后”。筆者是主張“預設”的,因為教材體系“預設”了教學目標(參見拙文《不應忽視“教教材”》,《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06年第6期》);但很希望看到“生成”或“預設”與“生成”相結合的課例。但很遺憾,即便是競賽評優課,也看不到課堂臨時“生成”教學內容的課例,所有參賽課均為純“預設”課,均嚴格按教師課前設定的目標和程序進行,沒有絲毫“生成”的影子。看來,臨時“生成”教學內容的課不好上!
總體上看來,這些競賽評優課以及我所見到的其他競賽評優課,完全不同于常規課,它熱鬧、好看、觀賞性強,遠不像常規課那樣樸樸素素;但不能不說,或許是受時間限制的原因,這些競賽評優課都上得還比較淺,文本解讀和語言品味都還沒有“到位”,其深度、廣度、效度都還不夠,如果要對付考試(特別是高考),課后還需要做許多補救性的工作。而這絕非個例,這是競賽評優課的普遍現象與共性問題。看來,我們應該正視和思考這一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