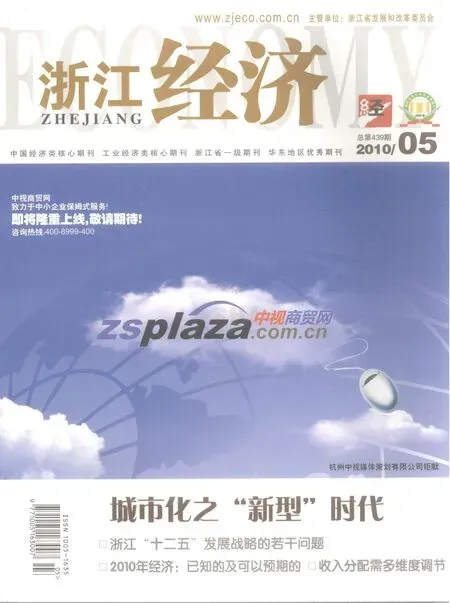經濟空間集聚發展:國際國內經驗
文/浙江省發改委課題組
大都市區、城市群以及城市連綿帶已成為空間上主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顯著地呈現出城市經濟的競爭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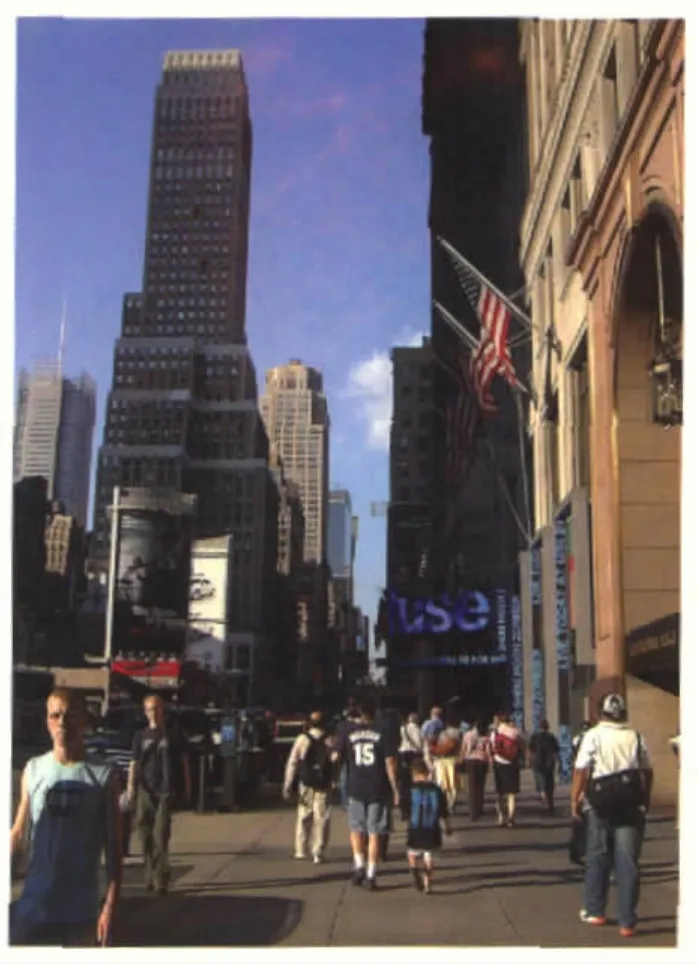
城 市經濟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集中表現,城市經濟空間集聚則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特別是在20世紀中期以后,城市經濟尤其是以大都市經濟圈或城市群為主要載體,成為了發達國家或地區城鎮空間布局最為集約、產業競爭最為強勁、要素配置最為高效的經濟空間組織形態。
國際經驗
20世紀中期以后,交通運輸和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產業布局模式。70年代以后,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日趨成熟及其日新月異的發展,空間距離對于市場、交易和消費等經濟過程的影響顯著降低,產業布局的空間尺度沖破了單個城市的約束,開始走向多種形態的城市群體。大都市區、城市群以及城市連綿帶等成為空間上主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顯著地呈現出城市經濟的競爭實力。
美國——兩大城市群的經濟空間集聚模式。進入20世紀,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從西歐轉移至北美。美國的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和北美五大湖地區,大量人口集聚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以及匹茲堡、克利夫蘭、托利多、底特律等城市,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板塊核心區,形成了兩個巨大的城市群,集中了20余個人口達100萬以上的大都市區和全美70%以上的制造業,構成一個特大工業化區域,成為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區。經濟空間集聚的多樣性和分工合作的緊密性,是美國兩大城市群發展的基本特征。如在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中,紐約是經濟和對外聯系中心;華盛頓表現出鮮明的政治特色;費城是東海岸主要的煉油中心和鋼鐵、造船基地,主要承擔產業及對外交通運輸職能;波士頓則是著名的文化城,并以128公路環形科技園區而承擔高技術工業發展職能等。這些“高能量”的城市聯系緊密,各種經濟要素在城市群中自由流動,形成一種巨大的“內吸力”,促進人口等要素更大規模地向該地區集聚。戈特曼將這種組合體結構稱為“馬賽克”,形象地反映出美國城市群中各種元素的密集交織關系。
日本——三大都市圈的經濟空間集聚模式。日本高速經濟增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70年代初達到人均6000美元的發展階段。與美國城市沿交通線軸向輻射形成城市群的特征不同,日本的大城市以近域蔓延和同心圓式輻射為主,形成了獨特的圈層狀大都市區空間結構,即大都市圈。到1985年,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以占全國31.7%的國土面積,集中了全國63.3%的人口和68.5%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后,三大都市圈開始進入結構調整期,主導產業轉向知識密集型,人口以近距離流動和都市圈之間的相互流動更為多見,區域結構趨向均衡化。以東京圈為例,在上世紀70年代,東京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制造業中心向服務業中心的轉變,其區位商高于15的產業有9個之多,且都屬于服務產業,在空間上高度集中于中央商務區。同時制造業生產環節逐步外遷,其區位商已略低于周邊三縣。周邊地區通過產業承接和分工協作得到積極發展,東京大都市圈整體開始形成比較明顯的區域職能分工和有效協作。
韓國——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集聚模式。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僅用30年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并于1990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韓國經濟空間集聚的重點特征之一,是依托工業化,優先發展大城市。即把產業區位發展中心區設在首爾、仁川地區和東南地區,在京仁地區集中建設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園地,在東南地區集中進行大規模重化學工業園地的開發,從而促進核心地區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協同發展和資源要素的高度集聚。1970-1990年,每年全國約有一半的遷移人口進入首爾,而接近60%的人口遷入首爾是出于就業因素。到1990年,面積僅占全國0.6%的首爾市,常住人口高達1060.3萬,約占全國人口的1/4。20世紀90年代后,首都圈邊緣地區迅速增長,中心城市規模繼續擴大,同時經濟要素開始向周邊的衛星城市集聚,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相對穩定的發展格局。
國內趨勢

城市經濟尤其是都市圈、城市群、縣域城鎮已成為經濟空間集聚發展的組織形態,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空間上融合發展
跨入21世紀,我國積極實施區域協同化、產業集聚化、要素集約化、環境生態化的國土開發戰略,以區域中心城市、沿江沿海和交通要道城鎮群為依托,逐步推進形成多個跨省區市的經濟區域,特別是以都市圈、區域中心城市、縣域城鎮為依托,產業布局、生產要素、人口分布出現了集群集聚集約發展的趨勢。
——城市群戰略:引領區域競合發展的主導力量。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以及中部有條件的城市密集地區,如長株潭地區、武漢都市圈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加快經濟一體化步伐,出現了省際、城際之間打破行政界限的束縛,謀求經濟上融合共進的局面。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國家“十二五”規劃《思路》提出,“以陸橋通道和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以國家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的城市群為主要支撐點,構建形成‘兩橫三縱’城市化空間格局。”“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依托,著力培育若干大的城市群,形成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在這些空間發展戰略指引下,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確定的重點開發區域和優化開發區域,基本上是以城市群為空間組織形態作為國土開發的重點地區,突顯集約、和諧、統籌發展的理念。
——沿海開發戰略:構筑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競爭的新平臺。在基本完成陸域國土空間開發布局之后,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的發展規劃》,相關區域開發相繼上升為國家開發戰略。在這些區域規劃中,天津濱海新區、江蘇沿海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等,均是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屬于新的戰略部署;而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大沿海板塊,長三角和珠三角則再次被重新部署,賦予其全新的發展詮釋。
從國際國內經濟空間集聚的趨勢來看,有三個方面引起我們的思考:一是城市經濟尤其是都市圈、城市群、縣域城鎮已成為經濟空間集聚發展的組織形態,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空間上融合發展。創新型經濟、服務型經濟已成為城市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城市功能提升與產業結構調整相促進,提升了區域競爭力。二是區域、城市之間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城市群體之間的競爭,大都市經濟圈和城市群將主導城市化空間形態的變化,城市、區域既競爭又融合成為熱點,以贏得更加有利的發展地位和資源配置效果。三是結構決定功能,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提升,經濟重心必然加快向城鎮密集區轉移,特別是當經濟發展階段出現重大變化后,需要空間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要素結構等與之進行相適應的調整,以滿足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浙江新一輪城市經濟或區域經濟轉型,應以大都市經濟圈或城市群為主導,集中更多的資源、政策向大都市經濟圈配置,以提高產業發展、資源利用水平,形成新的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