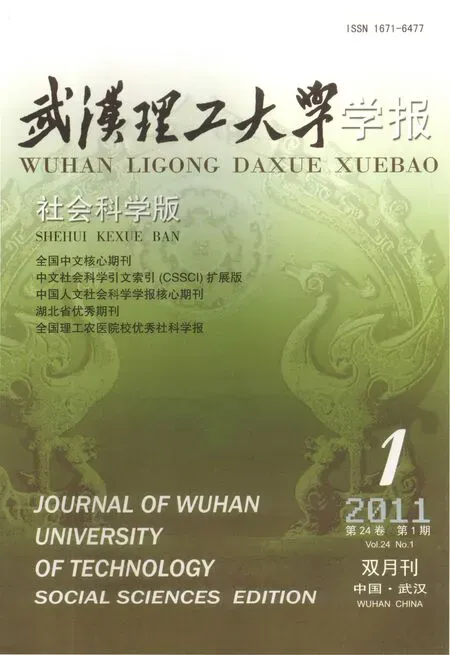境外安全文化研究20年評述*
郭 飛
(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境外安全文化研究20年評述*
郭 飛
(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根據研究的主體不同,最近20年來的安全文化研究以1998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安全文化理念被引入安全問題開始,到1998年安全文化專刊發行,其間以機構主導型的安全文化研究為特色;后一階段,從1998年至今,逐漸轉變為學者主導型的安全文化研究。安全文化研究關注了安全文化的定義、性質、內容、測量、模型,以及如何建立積極的安全文化等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的共識較少,安全文化在促進安全的實踐中處于起步階段。建立安全文化共同認可的理論前提,有效地標識和測量組織的安全文化,構建有說服力的安全文化模型,通過建立積極的安全文化在實踐層面提高組織的安全績效,是安全文化研究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安全文化;國外;研究進展
安全文化最初被關注,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切爾諾核電站事故報告[1]之后。1986年的切爾諾核電站事故顯示了技術的弱點,強調組織安全的必要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核委員會對高風險產業中的安全文化研究表明,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致因的重要方面之一。1988年,國際核安全咨詢小組在其“核電安全的基本原則”[2]中,把安全文化列為基本的管理原則。從那時起,安全文化日漸擴展到融合領導原則和共同的價值觀,提高交流和組織學習,關系到個人和團隊的行動等方面。安全文化理念目前正在被一些大公司、職業和管理機構、政府管理部門以及其他有影響的組織承認和提倡。同時,安全文化理念被廣泛運用在重大事故的致因調查和分析中,例如北海的派普艾爾法石油平臺爆炸,倫敦的克拉彭鐵路災難的事故分析調查報告都認為,組織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發生的重要致因[3]。
安全文化理念在減少和預防災害、事故、傷害方面的積極意義,使得安全文化在過去20多年中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重視。近年來,安全文化理念在中國也開始引起學術界和產業界的關注。為了促進安全文化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的發展,本文以最近20年來(1986-2009年)安全文化研究的英文文獻為素材,對產業(尤其是高危產業)中的組織安全文化研究進行綜述,把這20年來的安全文化研究分為兩個階段,并重點介紹安全文化的定義、性質、內容、測量、模型和積極的安全文化及其建設等問題,最后,對安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趨勢進行了評述。
一、安全文化研究的兩個階段
根據研究主體的不同,過去20年來的安全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1986-1998年),以機構為主導的研究階段,從安全文化術語被引入安全問題,到1998年安全文化研究的專刊(期刊)發行;第二階段(從1998年至今),以學者為主導的研究階段,其間安全文化被大量地研究,從以機構的報告為主要形式演變為以學術論著和論文為主要形式,并不斷重視安全文化的理論和實踐探討。下面分別具體來考察安全文化研究的上述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6-1998年。
具體而言,這一階段的研究特點表現為,安全文化問題以機構的關注為主,尚未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只有極少數的學者關注了安全文化問題[4-6],他們的研究反響不大。除了少量的文章之外,這一時期以書籍形式存在的著作主要是機構的報告,例如國際核安全咨詢小組的報告、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以及相關機構組織的會議和論文集。除了國際原子能等相關機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在這一時期較早地關注了產業中的安全文化問題。在研究內容上,這一階段的主要貢獻在于把安全文化理念引入安全問題的研究中,標志著人們開始關注安全中的管理和文化問題。而不足之處在于,總體上過分關注安全文化應該包括的細節,很少提供可接受性的總體標準,沒有指出安全文化與人的績效或人的可靠性之間的聯系,對安全文化與安全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的假定過于簡單[7]。
第二階段:1998-2009年。
第二階段的安全文化研究,其標志是Work and Stress雜志于1998年和 Safety Science于2000年推出的兩期“安全文化”研究專刊。這兩期安全文化研究專刊的發行,開啟了學術界研究安全文化的熱潮。隨后出版了大量的相關著作,其中,除了少量作為一些機構重視安全文化的繼續之外[8],其他大量的著作都是以學者為主導的學術論文和著作——而非由機構發行的報告和文件。此階段,除了國際原子能機構之外,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諸如美國[9]、澳大利亞[10]、英國[11]、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12]等——開始在政府和機構的層面關注安全問題,并出臺了相應的機構調查報告和文件等。安全文化研究的領域相對前一個階段有所擴大,從原子能、核領域擴展到海上石油化工[13]、食品[14]、交通等產業領域。但是總體而言,在上述各種產業中,對核工業領域的安全文化研究仍然最多,這很可能因為核領域是高危、高風險領域,同時也是安全文化最先關注的領域。
二、安全文化研究的現狀與內在邏輯
總體而言,安全文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都很緩慢。研究者對“安全文化”一詞的解釋給予了太多的關注,并引發了不少爭論。長期以來,安全文化方面有代表性的綜合性論著較為缺乏,可喜的是,最近的情況有所改善,例如學者Antonsen于2009年出版了《安全文化:理論,方法和發展》[15]。
安全文化研究從安全文化的定義和性質擴展到安全文化的標識和測量。與安全文化的標識和測量密切相關的是對安全氛圍的研究,這些研究旨在通過安全氛圍來標識和測量組織中的安全文化,其默認的前提是:安全氛圍是安全文化的指示和表征,安全氛圍能夠展現安全文化。
盡管安全文化通常被假定與好的安全績效相聯系,但是,在研究的最初階段,這種聯系很少在具體的產業領域得到證實。因此,一些學者對具體產業中的安全文化與安全績效的關系進行了經驗性的研究,逐步證實了這種聯系,即擁有安全文化的組織與缺乏安全文化的組織之間,以及具有強烈的安全文化的組織與擁有較弱的安全文化的組織,在安全績效方面存在差異。這里涉及的問題是,安全文化是組織中包含的要素,還是組織呈現出的特性?如果是前者,在衡量組織的安全文化問題上,則是該組織是否擁有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擁有安全文化;如果是后者,問題則表現為該組織呈現出何種特性。因此,需要關注什么是積極的好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要素,如何發展積極的安全文化,建立積極的安全文化的原則等與此相關的問題正在受到學界的重視。
下面具體從安全文化的定義、性質、內容、測量、模型,以及如何建立積極的安全文化等方面對過去20年來的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逐一進行介紹。
(一)安全文化的定義和性質
有關安全文化的代表性定義,見表1。

表1 安全文化的代表性定義

續表1
安全文化的上述定義大多是概括性的,多數定義認為對安全的態度、價值、信念是安全文化定義的重要方面。但是學界并沒有關于安全文化共同認可的定義,在此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
關于安全文化的性質,更多的研究來自組織文化以及與組織文化相關的安全文化研究。安全文化的觀念來自組織文化,從組織文化的角度看,安全文化是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安全文化影響員工和組織持續的健康和安全績效相關的態度和行為[22]。安全文化是組織的關鍵要素之一,它設定了工作場所中安全操作的基調。安全文化通常被看作是組織管理活動中與安全相關的能力[16]。
Pidgeon認為[3],安全文化可以被看作意義的建構系統,通過特定的工人或工人團隊,理解他們在所處環境中的危險,安全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并非隨時都在變化。學者 Richter和 Koch發現[24],文化并非凝固不變,在社會現實面前,文化被不斷地創造和被創造,因此,應該在特定的環境中理解安全文化,隨著物質條件和社會關系的發展,安全文化會相應地變化。
(二)安全文化的要素和內容
安全文化由認識和情感構成,這些認識和情感成為小組、組織的個性特征;安全文化是組織靜態持續性的特征[20]。學者 Thompson等認為[17],安全文化的要素包括高層管理者對安全的承諾,好的交流,組織學習、獎勵發現安全問題的環境,參與式的領導方式。安全文化中對硬件、物理環境、軟件、人、行為的安全態度至關重要。
安全文化包括三個層次或水平——外層、中間層、核心層,其中的每個層次都可以被獨立地研究[19]。安全文化的外層是器物,由特定的可見的事物組成,在研究對象上是具體的。安全文化的中間層由信奉的價值觀構成,被可操作化為態度。安全文化的核心層由基本假設(如關于真理與實在、時間、空間、人類、人類活動、人際關系等性質的基本假設)構成,它是潛意識的和抽象的,滲透于整個組織之中。
信任問題是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信任作為有效交流的基礎,在核設施顧問委員會中被看作安全文化的特征之一。Hale認為[26],好的安全文化在于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信任,在這種環境中的個人不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也密切關注其他人,為其他人提供事故和意外方面的支持。Hale同時解釋了創造性的“不信任”概念,認為員工應該維持與風險控制系統之間的關系。例如,員工需要預測他們可能遇到的新問題或者新情況下的老問題,而不應該輕信安全文化或安全績效是完美的[8]。在理論上,創造性的“不信任”可以導向更加質疑的態度,幫助避開因盲目信任技術、系統、操作導致的潛在事故或者接近事故。通過質疑的態度,創造性的“不信任”可以避免群體思維忽視和曲解活動者意圖的情形[26]。
盡管信任問題在安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安全文化中的安全氛圍研究卻較少關注信任的測量問題。以英國天然氣公司為案例,M eanrns和M cGeorge運用明確的(直接的)和隱含的(間接的)方法測量了組織中的信任。研究結果顯示,工人對工友、監督者、高層領導者表示出明確的信任,同時對他們的工友表示出含蓄的信任。M eanrns和M cGeorge把明確的信任看作安全文化的表層部分,把隱含的信任看作安全文化的深層部分,認為應該關注高危產業中的安全文化、信任和不信任(distrust)問題[27]。Clarke也認識到相互信任在發展積極的安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28]。另有研究關注了風險、信任、安全文化的案例(英國火車運營公司為例),安全相關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功能等問題[29-30]。
領導問題和員工參與是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者不斷認識到:領導在建立、促進和評價安全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1],通過管理的方式能夠改變安全文化[32],管理者及其職能對安全文化的實踐(如安全文化的建設和維持)有重要影響。因此,安全文化研究中的領導問題日益受到學界關注。
員工參與對安全績效有重要意義,組織的領導氛圍直接影響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對組織技術系統的正確發展是基本的,因為人的因素在組織的安全績效中占有重要地位。當員工意識到自己是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領導重視他們的意見和貢獻時,員工就會減少曠工,提高自己的滿足感和斗志。強烈地認同使他們致力于所在的組織,為組織的發展作貢獻[33]。
(三)安全文化的測量和安全文化模型
調查問卷和人類學方法是測量安全文化的常用方法[16]。調查問卷主要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它正在被綜合、定量的測量方法取代和補充。人類學方法通常是昂貴和費時的,提供的往往是發現性的數據,而不是能夠被加入管理的行動計劃中的硬數據[17];不適合識別文化元素對安全的影響,在缺少事故的情況下,人類學方法僅僅思考或者假定組織文化對安全的影響。
安全氛圍和安全管理被看作安全文化的反映,安全氛圍是安全文化更為具體的表現。很多研究通過測量安全氛圍來測量安全文化。通過測量安全氛圍來測量安全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安全氛圍是安全文化的結果,安全氛圍依賴于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不能僅僅被看作安全氛圍的替代[17]。通過測量安全氛圍考察安全文化,往往單獨關注人們的思考方式(人們的觀念),沒有展現出安全文化的多個方面,忽視了與此相關的安全環境、安全管理系統、人的安全行為等內容。
安全文化模型展示了動態的整體的安全文化的性質,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建立安全文化。Geller的整體安全文化模型區分了三種動態和相互作用的因素:人、行為和環境。當員工理解和接受整體安全文化的原則時,整體安全文化能夠被建立起來;這些原則包括:文化應該促進安全過程;關注過程而非結果,把安全從優先轉變為價值等。整體安全文化對領導者的素質有專門的要求,領導者應該關注過程或程序,把傾聽放在第一。然而,此模型沒有指出其適用于哪種產業組織,或者哪種先決條件對于此模型的成功運用是必要的,沒有界定其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區分出這些部分的優先級別。
Cooper提出了相互作用的安全文化模型[22]。態度和認識通過安全氛圍問卷來測量,與安全相關的行為通過一系列清單來評估,情境性的特征通過安全管理系統監督和檢查來測量。在該模型中,個人的態度、觀念和信念、行為、安全管理系統是形成組織安全文化的要素。人們既不能通過他們的環境決定性地被控制,也不能整個被自我決定。但是他們及其環境影響在動態的相互作用下彼此影響。Cooper認為,相互作用的模型包括整體安全文化模型[22]。此模型把安全文化定量化為相關的各個部分,為獨立地或綜合地測量和分析安全文化提供了可能,提供了測量和分析安全文化的理論和實踐框架。
Kennedy的安全文化的危險與可操作性模型旨在識別:其一,安全管理過程中容易失敗的地方;其二,安全管理失敗的潛在后果;其三,與安全管理失敗相關的潛在的(安全文化)的“失敗機制”;其四,影響安全管理失敗出現的可能因素。危險與可操作性程序由三個階段組成:表達安全管理;選擇危險與可操作性小組、向導詞、性質詞語;舉行危險與可操作性研究會議[20]。危險與可操作性會議是基于小組的方法,此小組由主席、秘書和經過選擇的熟諳安全管理過程的人員組成。通過集體研討和不斷地有組織的討論,用指示性的詞語(例如“缺少”、“略過”、“不合時宜”)和恰當的詞語(如“人”、“行動”、“程序/規范”)考察安全管理過程,會議的結果是找出安全管理的一系列漏洞[19]。
關于子文化系統模型,Reason指出,安全文化包括各種亞文化系統,亞文化系統包括一些子部門中的人們及其文化的各個方面。Reason把安全文化等同于非正式文化,安全文化依賴于由“公正的文化”支撐的“報告的文化”,同時,需要靈活的文化,如果一個組織根據某種危險對組織進行調整,將需要一個“學習型文化”。為了建立安全文化,安全文化被分解為一系列子目標,例如建立報告的文化、正義的文化、靈活的文化、學習型文化。上述每一點都依賴于獲得一系列次級目標來實現[22]。Choudhry等學者以建筑安全文化為例,提出了安全文化的綜合框架模型。該模型認為[17]:不安全的狀況可以通過安全執行來追溯和矯正,員工的行為可以通過基于行為安全的百分比來測量,安全管理系統可以通過工程和工地安全監督來測量,員工的認識可以通過安全氛圍來測量。Choudhry把安全文化與人員以及工作小組的行為、態度、想法聯系在一起,同時通過組織的安全管理系統把安全績效聯系在一起;把安全與承諾、管理風格、對安全的行動和反映的能力聯系在一起。綜上所述,已有的安全文化模型類型多樣,各有所長,但是,它們之間很少體現出相應的因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這些研究僅僅指明了一些廣闊的研究范圍和它們之間探索性的關系,未來研究中有待發展出共同認可的,能夠有效促進安全文化實踐的安全文化模型[17]。
(四)積極的安全文化及其建構
發展和維持積極的安全文化是提高組織安全的有效工具。在積極的安全文化中,員工不僅感受到對自身安全的責任,同時感受到對同事安全的負責。積極的安全文化是組織成員共有的、與安全相關的一套價值觀、認識、態度和行為模式的集合,也是與減少員工職業風險,在組織每個層次中被執行的,反映出減免事故和疾病發生的高度責任的一系列政策、實踐和程序[34]。Pidgeon認為,好的安全文化具有三個特性:處理危害的規范和規則,面向安全的態度,安全實踐的靈活性[35]。Choudhry等認為[17],積極的安全文化包括五個要素:其一,管理層對安全的承諾和職責;其二,管理層對員工的重視;其三,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可靠性;其四,對員工的授權;其五,持續的監督,校正措施,系統評估,不斷地改進以反映工作場所中的安全。Hale指出了好的(積極的)安全文化的要素:[21]安全的重要性;所有層面上的員工參與;安全人員的角色;關注信任;所有部門和主體警惕和幫助處理不可避免的疏忽和錯誤;開放的交流;改善安全的信心;把安全融入到組織中。
當一個組織具備下列條件時,可以認為其擁有安全文化[34]:其一,確定了反映組織在該領域的原則和價值安全政策;其二,建立了促進工人融入安全活動的獎勵機制;其三,為員工提供不斷的訓練,使他們以盡可能安全的方式工作;其四,為工人提供工作場所中關于風險的動態信息和正確面對風險的方法;其五,對行動進行計劃,以避免事故發生(組織性的計劃),同時在緊急情況下能夠及時做出反應(緊急計劃);其六,通過對組織中的工作狀況和事故的分析,通過對比其他組織,對組織的行動進行適當的控制或反饋。同時,管理者對安全具有強烈的責任,對員工的工作環境和狀況具有持續的興趣,并親自參與到安全活動中。最后,工人意識到安全的重要性,遵守規則和工作程序,積極參加安全會議,為提高工作場所的安全提出建議。安全文化的上述方面并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聯系。
發展和維持積極的安全文化是提高組織安全績效的有效工具。發展和促進積極的安全文化可以考慮下列方面:改變態度和行為;管理者的職責;員工參與;獎勵性的策略;訓練和研討班;特別活動[17]。一個組織要建立有效的安全文化,應該擁有收集、分析、傳播信息的安全信息系統,從事故和接近的事故中,在系統前攝的常規檢查中促進安全文化的建立。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報告的文化,人們可以報告他們的錯誤、失誤、違反;需要信任的文化,鼓勵甚至獎勵人們提供與安全相關的重要信息,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行為之間界限清晰;需要靈活的安全文化,當面對動態迫切的任務時,靈活地調整組織的結構,具有從安全系統中得出結論的意愿和能力,在必要的時候愿意而且能夠實施改革[36]。
三、安全文化研究評述
總體而言,研究者承認安全文化對安全績效有重要影響,因此,對安全文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的爭論較少。研究者更多地在安全文化的定義(包括哪些要素)、性質(是安全文化還是組織文化?安全文化是組織的組成部分還是組織表現出的特征?)、測量(安全文化與安全氛圍)、模型、積極的安全文化(及其特征)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討。基本可以達成共識的是:安全文化是對安全的前攝的積極立場,對安全管理和安全績效有重要影響。已有研究把安全文化看作多維的概念,更多關注了員工的價值觀、信念、態度、認識,用安全氛圍測量來替代安全文化測量目前仍然是主要的做法。從地域上看,挪威、英國、荷蘭等國家的安全文化研究居多,美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也有一些相關研究。從產業和組織方面看,已有的安全文化研究主要關注高危產業以及高可靠性組織。
安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尚無共同認可的定義和清晰的結構,安全文化的理論基礎仍然缺乏。已有研究對安全文化具體維度的共識和對安全文化可操作的經驗性研究較少;與情境性的約束相關的問題和與人們的真實行為相關的問題往往被忽視。這很可能因為安全文化的多數定義過于寬泛,使它很難具有一致的操作性。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二者之間的關系尚不清晰,缺乏令人滿意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模型。安全文化的內容、安全文化在組織中如何被反映等問題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研究,也尚未達成一致。從安全文化研究對安全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實際好處和價值而言,安全文化研究中諸多不成熟的觀點使得安全文化的實際有效運用尚處在初步的階段。
綜上可見,安全文化研究未來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至少應該包括下列方面:安全文化的定義、性質、要素、特征;積極的安全文化及其建構,安全文化的有效的標識和測量,安全文化影響安全績效的機制,安全文化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安全文化在特定產業、區域、文化中的個案研究,安全文化與其他文化(及其要素)相互影響的機制;安全文化模型及其運用等。
[1]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Summary report on the Post-Accident Review Meeting on the Chernobyl Accident[R].Vienn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1986.
[2]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Basic safety principles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M].Vienn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1988.
[3] Cox S,Flin R.Safety culture:Philosopher’s stone o r man of straw?[J].Work&Stress,1998(3):189-201.
[4] Mathis T L,Spitzer D D R.Developing A Safety Culture:Successfully Involving the Entire Organization[M].Keller&Associates,1996.
[5] Morris S,Willcocks G.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Illness at Work:How to Create a Health and Safety Culture[M].Trans-Atlantic Publications,1996.
[6] Cooper D.Imp roving Safety Culture:A Practical G-uide[M].John Wiley&Sons,1997.
[7] Sorensen J N.Safety culture:a survey of the state of-the-art[J].Reliability engineering&system safety,2002(2):189-204.
[8]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Developing safety culture in nuclear activities: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assist progress[M].Vienn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1998.
[9] National Safety Council.Safety culture and effective safety management[M].National Safety Council,1999:450.
[10] 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Safety culture survey report:Australian minerals industry[M].Canberra: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1999.
[11] Great Britain.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Safety culture:a clear guide to the HSE publications you are most likely to need.[M].Sudbury:HSE Books,1999.
[12] Occupational Safety Health Council.A Survey of safety culture in 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M].Hong Kong:Occupational Safety&Health Council,2001.
[13] Hoholm T.Safety culture in the Norwegian petroleum industry[M].Centre for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Oslo,2003:41.
[14] Yiannas F.Food Safety Culture:Creating a Behavio r-Based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M].Sp ringer,2008.
[15] Antonsen S.Safety Culture:Theory,Method and Imp rovement[M].Ashgate,2009.
[16] Choudhry R M,Fang D,Mohamed S.The nature of safety culture:A survey of the state-of-the-art[J].Safety Science,2007(10):993-1012.
[17] Glendon A I,Stanton N A.Perspectives on safety culture[J].Safety Science,2000(1-3):193-214.
[18] Cox S,Cox T.The structure of employee attitudes to safety:A European example[J].Work &Stress,1991(2):93.
[19] Guldenmund F W.The nature of safety culture: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J].Safety Science,2000(1-3):215-257.
[20] Kennedy R,Kirwan B.Development of a Hazard and Operability-based method for identifying safety management vulnerabilities in high risk system s[J].Safety Science,1998(3):249-274.
[21] Hale A R.Culture’s confusions[J].Safety Science,2000(1-3):1-14.
[22] Cooper M D.Towards a model of safety culture[J].Safety Science,2006(2):111-136.
[23] Mohamed S.Scorecard App roach to Benchmarking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in Construction[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03(1):80-88.
[24] Richter A,Koch C.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 and ambiguity in safety cultures[J].Safety Science,2004(8):703-722.
[25] Fang D,Chen Y,Wong L.Safety Climate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06(6):573-584.
[26] Cox S,Jones B,Collinson D.Trust Relations in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J].2006(5):1123-1138.
[27] Burns C,Mearns K,Mcgeorge P.Exp licit and Implicit Trust Within Safety Culture[J].Risk Analysis,2006(5):1139-1150.
[28] Clarke S.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fety culture[J].Journal of O 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9(2):185-198.
[29] Jeffcott S,Pidgeon N,Weyman A,et al.Risk,Trust,and Safety Culture in U.K.Train Operating Companies[J].Risk Analysis,2006(5):1105-1121.
[30] Conchie SM,Donald IJ.Th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safety-specific trust and distrust[J].Safety Science,2008(1):92-103.
[31] Roughton J,Asse JM.Developing an Effective Safety Culture:A Leadership Approach[M].Butter worth-Heinemann,2002.
[32] Hafey R.Lean Safety:Transforming your Safety Cutlure with Lean Management[M].Productivity Press,2009.
[33] Vecchio-Sadus A M,Griffiths S.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safety culture[J].Safety Science,2004(7):601-619.
[34] Ferna’ndez-Mun-iz,B.,Montes-Peo’n,J.M.,&Va’zquez-O rda’s,C.J.Safety culture:Analysis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ts key dimensions[J].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2007(6):627-641.
[35] Pidgeon N,O’Leary M.Man-made disasters:w hy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s(sometimes)fail[J].Safety Science,2000(1-3):15-30.
[36] Reason J T.Managing the Risks of Organizational Accidents[M].A shgate Publishing,1997.
Review of Western Countries’Safety Culture Study in 20 Years
GUO F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Zhejiang,China)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ubjects,the study on safety culture in the latest 2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y 1998 year:the first phase,from introducing the term of safety culture into safety studies to the special issues on safety culture published in 1998,is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e sorientated study.The second phase,from 1998 to the p resent,transform s into academic-oriented study gradually.Safety culture in the latest 20 years has been stu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definition of safety culture,nature of safety culture,content of safety culture,measurement of safety culture,safety culture models,how to build a positive and good culture and etc.On the whole,the above aspects of safety culture merely have partial agreements,and safety culture studies are in the initial period to imp rove organizational safety performance in industry.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safety culture are important to study in the future:unanimously theoretical premises,valid measurement,persuasive models,constructing a positive and good safety culture.
safety culture;western countries;progress on study
F270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1.012
2010-09-20
郭 飛(1980-),男,安徽省渦陽縣人,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主要從事工程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研究。
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項目(留金出20083019)
(責任編輯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