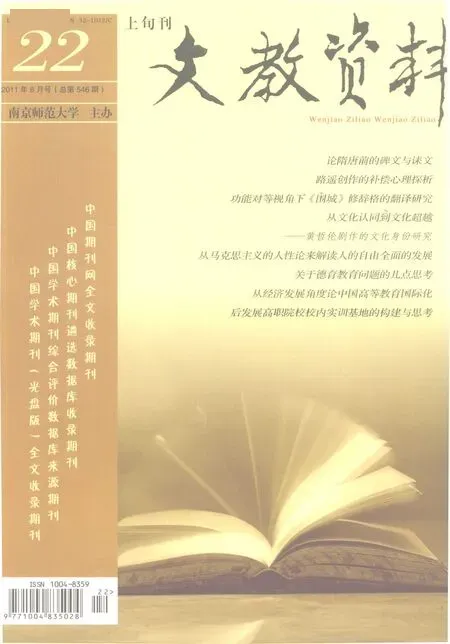論隋唐前的碑文與誄文
趙 征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有《誄碑》一篇,碑、誄兩種文體的并稱并不是始見于劉勰,早在陸機的《文賦》中就有并稱趨勢的雛形,漢以后馬融、蔡邕等人的人物傳記中,均有碑誄并舉的例子。“寫實追虛,碑誄以立”(《文心雕龍·誄碑》),考察碑與誄兩種文體的特征后,不難發現,碑、誄同源,雖然分屬兩種實用文體,但在內容形式風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碑與誄同源,吸納《詩經》的文學表現手法,文辭化用五經,體現深刻的儒家思想內蘊。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碑志類者,其體本于詩。”《文心雕龍·誄碑》:“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詩是碑、誄產生的源頭,并對其發展影響深遠。
首先,碑、誄同時吸收《詩經》中頌的文體功能,繼承頌德的寫作范式。頌詩以四言為主,韻律整齊,隔句押韻,節奏感強。碑文與誄文也傳承這一特色。我們翻閱漢魏六朝的碑、誄作品,行文結構由“序文”和“銘文”組成,序的部分可韻可散,銘的部分(即正文)都是四字一句,工整對仗,一詠三嘆。
其次,碑與誄借鑒頌詩的文學表現手法,在序文開頭追述先祖世系、歌頌先祖功美。《詩經·周頌·武》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后。”這是歌頌周武王的詩,卻在其首追述其父文王的功績。“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周頌·閔予小子》)這是周成王哀悼武王的詩,也提到祖父文王的事跡。“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魯頌·閟宮》)這是歌頌魯僖公的,同時也述及周始祖姜嫄和后稷。碑文和誄文中對先祖的記述,既表現了儒家孝道中“敬”的一面,又有祈求祖先庇佑后代之意。如東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開頭即曰:“其先蓋周之胄緒,虞部建國,享土受胙。”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于天地。”曹子建《王仲宣誄》,其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傅毅《明帝誄》:“武伏蚩尤,文勝孔墨,下制九州,上系皇極。”這些在碑誄中歌頌先祖功美的手法均源于頌的寫作手法。
再次,翻閱碑文與誄文,隨處可見行文中對儒家經典的化用。“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文心雕龍·誄碑》)蔡邕《郭有道碑文》是化用《論語》“循循然,善誘人”之語。王仲寶 《褚淵碑文》則是化用孔子對孟子的評價:“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哀公誄孔子化用《小雅·十日之交》中的語句,曹植的《王仲宣誄》化用《論語》:“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碑與誄對儒家經典的繼承,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倫理本位觀的宣揚。儒家“以祖為宗,以孝為本”的觀念深入并根植于各個文化階層中,反饋出“見賢思齊,內自省”的個人人格修養。
最后,在哀悼所碑所誄之人的同時,深刻體認先祖功美,增強自我滿足感和家庭成就感,收到“垂示后裔、作范后昆”的效果,最終回歸儒家的政治教化功能。“石墨鐫華,頹影豈戢?”(《文心雕龍·誄碑》)死者的形象無法消失,已經作為一種衡量后人德行的教化標準,后代紛紛敬仰與效仿的,至此,封建宗法制度下宗族的凝聚力加深。
二、碑與誄吸納銘文與頌文“述德”的文體職能,且溢美之詞頗多。
《文心雕龍·碑誄》篇曰:“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誄。是以勒石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可見,碑、誄、銘、頌在文體特征方面相互通融,聯系緊密,有各自的區域,又有交錯的地方。
李充在 《起居誡》中說:“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文心雕龍·誄碑》云:“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與誄在內容上均有稱述功美之辭,其實,在翻檢隋唐的文獻資料后,便可看到一個顯著的特征:碑誄銘頌四種文體有一個相互溝通的橋梁,是“述德紀功”,且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隱性的繼承。下面討論碑與誄對銘文、頌文的各種吸納。
1.碑與誄同時吸收銘文的方面
《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彥和在《文心雕龍》中也指出,銘文有兩種功能,其一是勸誡,其二是紀功。由帝王“刻輿以弼違”。到夏商周“天子令德,諸侯計功”,銘文“歌功頌德”的文體職能充分被碑與誄所吸收,產生了周穆王“紀跡于弇山之石,創古碑之意”和 “周朝之誄,稱天以誄之”(《文心雕龍·誄碑》)的結果。后世以來,碑、誄逐漸與銘合流,“碑銘”、“誄銘”并稱的情況也很普遍:《后漢書·翟酺傳》:“學者為酺立碑銘于學云。”《晉書·天文志上》:“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曹丕《典論·論文》中“銘誄尚實”《三國志·凌統傳》:“權聞之……使張承為作銘誄”之句。可見,碑、誄在稱頌祖先功美和所碑所誄之人行跡上與銘文“述德詠功“兼容。
2.碑與誄吸納頌文的方面
首先,《文心雕龍·頌贊》篇云:“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上文我們已知碑、誄起源于詩,又受頌的影響,彥和在《文心雕龍》中指出:“頌有兩種功能,其一為諷刺,其二為贊頌。”“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就是頌“述德”的最早代表。而碑、誄則充分吸收頌的贊頌功能。
其次,頌文的創作風格和寫作方法上要求“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文心雕龍·頌贊》),還要跟著情意的變化。這些都與碑、誄的行文風格相類似。碑文要求“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文心雕龍·誄碑》),這是碑之制也。碑文的“清華之風”與頌文的“清鑠之風”相近,碑文以形容為主,“俊偉洪深”之風與頌文運用藻飾,鋪采摛文,汪洋恣肆的風格相近。而誄文“傳體而頌文”的特色有頌文之風范,用“嗚呼哀哉”四字,表達愈積愈濃的情感,又與頌文“與情而變”的情感敘述方式暗合。碑文與誄文均有自覺吸收頌文“述德”內容,只是在藝術風范和抒情表達上各有偏重而已。
碑、誄共同對銘與頌的吸納兼容,使得碑、誄的文體特征趨同但不雷同,它們在繼承銘、頌的基礎上,形成了獨具風格的寫作格局。但應該看到,由于“述德”功能的無限膨脹,帶來大量的溢美之詞,也是文學發展的弊端所在。
三、碑與誄的適用人群由帝王向平民普及,內容由簡到繁,向既述德又述哀發展,風格清麗與弘深并舉。
《文心雕龍·誄碑》:“樹碑樹亡者,同誄之區。”樹立石碑,表述死者的,就同誄一個區域了。其實,碑最早不是一種文體,《禮記·祭義》中有記載,碑用來系牲畜、識日影、懸棺木。孫何亦云:“碑非文章之名,后人假以載其銘耳。”后來,人們在懸棺木的碑上刻立文字,形成了碑文,才與誄文同區域。而碑也逐漸成了碑文的代名詞,發展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文體。追溯到上古時期,碑與誄的使用有嚴格的等級制度的規定,不是所有人都有立碑誄的權利。“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到秦王刻石以記功勛,再到“后漢以來,碑碣云起”。駱鴻凱在《文選學》中指出:“碑文之作,乃子孫為其父祖,弟子為其師尊,親故為其親故。”可見碑文的適用范圍的擴大化。誄亦如此,“夏商以前,其詞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文心雕龍·誄碑》)直至春秋戰國,打破格局,有哀公誄孔子,柳下惠之妻誄惠子之文,誄逐漸也由官誄向私誄轉化。
碑與誄使用階級的廣泛性帶來寫作形式的自由性和內容由簡到繁的變革。上古帝王將相的碑、誄,形式嚴謹,內容嚴肅,氛圍凝重,雖有溢美之詞,但字數有限;發展到漢朝,尤蔡邕碑誄為例,“其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文心雕龍·誄碑》)孔融有摹伯喈,“其文辨給足采。”誄文的字數也由十幾字向幾千字過渡,并且,碑與誄均是由前序文和后銘文組成,在文體發展過程中,序文越來越長,銘文更加駢儷化。
碑與誄的體制功用由最開始的碑述德、誄述哀向碑與誄既述德又述哀轉變。趨向兩種文體內容與風格的合流。前文我們已知碑、誄同時繼承與兼容銘、頌“銘德纂行、紀德彰功”德性的一面,也有顯示哀情的一面:《杜氏文譜》云:“碑以志悲貴哀慕。 ”《初學記》亦云:“碑,有悲意,悲往事也。”“誄,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凄焉如可傷。”(《文心雕龍·誄碑》)故而傅毅之誄北海,其文敘述哀情;曹植的誄卞太后,也尚及哀情。因此,述德述哀的表情方式,是對先祖及已故之人的歌頌和緬懷,通過“巧于序悲”的藝術加工,在盛德中彰顯哀情,與王國維“借景抒情”從“有我之境到無我之境”的升華,至此“自成高格”的手法異曲同工。使聽者讀者“觀風似面,聽辭如泣。”
陸機《文賦》云:“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我們翻檢漢魏六朝的碑文,渾樸高古,遒勁凝重,誄文亦在纏綿中隱寓歷史的厚重,文情并茂,文質相半。《文心雕龍·定勢》曰“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碑與誄的總體風格是清麗與弘深并舉,它們或多或少滲透兩種風格,但兩種文體根據文體特征又各有偏重,誄文偏重清麗,碑文偏重弘深。所謂的“碑宜雄渾典雅”(陳繹曾,《文說》)。但是碑與誄都要求避免玄渺浮艷,正如陳懋仁在 《文章緣起注》中指出:“宏邈淫艷,非碑誄之施。”
四、結語
由上述可知,碑與誄在起源、內容、表現手法、藝術風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這勢必在文體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合流的趨勢。根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文學發展規律,碑以“變”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在唐以后的碑文創作實踐中,作者吸收史家筆法,與“志傳”結合,內容飽滿,表現手法多樣。“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新變后的碑文彰顯了競爭的優勢,使得狹窄的誄文最終吿敗,退出了歷史舞臺。唐以后,碑文取代了誄文的文體職能,并且向更寬廣的文學道路上邁進。
[1][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
[2][晉]陸機.文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梁]蕭統.文選.中華書局,1977.
[4][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清]李兆洛選輯.駢體文鈔.上海書店,1988.
[6][清]姚鼐.古文辭類纂.中國書店,1963.
[7][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程俊英.詩經注析.中華書局,1991.
[9]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2009.
[10]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12]于景祥,李貴銀編著.中國歷代碑志文話.遼海出版社,2009.
[13]程章燦.文選.選錄碑文及其相關的文體問題.
[14]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15]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6]周振甫著.文章例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17]錢基博.中國古代文學史.東方出版中心,2008.
[18]袁行沛.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