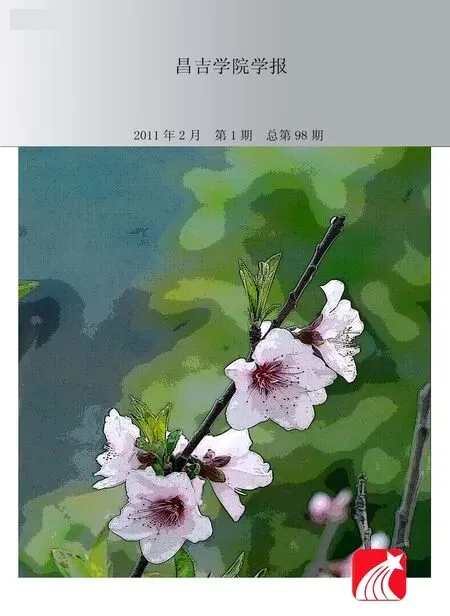對塔里木盆地佛教初傳的思考
王 勝
(昌吉學院社會科學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古代新疆又被稱作西域,西域這一詞最早出現于漢代文獻里,如《史記·司馬相如傳》中在司馬相如告巴蜀民檄中說“康居、西域重譯納貢,嵇首來京”,此檄作于漢武帝元光末年(前134-前129年左右);《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公元前121年,漢武帝表彰霍去病收撫匈奴渾邪王之功時稱:“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強萬有余人”;《漢書·西域傳》記述“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以上這些文獻中都曾出現過“西域”這一詞,但“西域”一詞究竟為何意呢?《說文解字·戈部》認為“或,邦也。域,或又從土。”加之古人所說的“或”、“域”、“國”三字古聲意并同。因此西域的本意應當就是指西部地區。
古代新疆地區(西域)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東北、北面、西面和西南面分別與鄰國接壤,東面有幾十里寬的谷地通向甘肅河西走廊,與我國內地連通。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在這里形成發展起來的。塔里木盆地以東、盆地的南北兩側均由一條絲綢之路連起來。通過 “絲綢之路”,中原地區與西域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友好往來頻繁發展起來了,而印度的佛教也隨著這兩條聯系著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而傳入中國的西域地區。北道龜茲,北倚天山,南對昆侖,西通疏勒,巴楚圖木舒克為龜茲西境;東接焉耆,庫爾勒為其分界線。塔里木河流貫其南,隔一大沙漠,而與于闐為鄰。水草豐盈,城市林立,在西域36國中,龜茲為一大國,包括今之輪臺、庫車、沙雅、拜城、阿克蘇、新和六縣,而以庫車為中心。南道于闐,地處塔里木盆地南沿,東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盛時領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豐等縣市,都西城(今和田約特干遺址)。這兩地作為西域佛教初傳的入口,究竟哪一地區為佛教傳入的第一站,曾引起許多學術界學者的爭議。本文試圖從從大量的典籍中另辟蹊徑地推論出一些新的看法以釋疑,望能從中探出一些端倪來。
一
佛教在公元前6世紀左右產生于印度,它的廣泛傳播是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大概是公元前324年,旃陀羅笈多建立了孔雀王朝(約公元前324-前185年),第三代國王阿育王征服羯陵伽后,對自己以往造成的禍害頗為悔恨,遂將佛教定為國教,勸導人們要服從父母,尊敬師長,對朋友、同伴、親戚、苦行者等要慷慨和友好,甚至對所有的生物也要克制殘暴的行為。為了促使佛教的發展,阿育王大力宣揚佛理并建造了許多佛塔,但后來他又發現佛教教義異說紛起,僧團內混進許多異教徒,不尊從佛法,為了統一信仰和教規,也為清除冒充比丘的外道,他于華氏城的阿育王寺舉行了千人結集(第三次結集),之后,他又派出許多使團和大批宣教師赴四方弘揚佛法,據巴列文斯里蘭卡歷史書《大王統史》第12章和《摩崖法敕》第13節的記載,佛教那時已跨越恒河流域,傳布到印度各地和毗鄰印度的中亞、南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基至佛教傳教士的足跡遠至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臘。后來又經過迦濕彌羅(克什米爾)的大月氏貴霜王朝國王迦膩色迦“第四次結集”,使得佛教在蔥嶺以西廣大地區開始盛行,這客觀上為印度佛教向蔥嶺以東的西域廣大地區的傳入奠定了必要的條件。[1]
佛教是何時傳入西域的?目前仍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現列舉一些前輩學者的觀點:
佛教于何時傳入中國?諸說紛紜,學術最貴重者為所謂《魏·略》的記載,據此記錄知在前漢末期,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是則西域之佛教的傳播;必前二公元前二,蓋其地為中國與西方各國交通必須之地,且富于宗教信仰的“伊蘭”系人種聚居,佛教至此當先為樹立,而后方始傳播東方,波及中國,自可置值。(羽田享《西域文明史概論》)
佛教傳入龜茲之時期必與佛教傳入中國之時,即漢明帝時或同時或在前。紀元前第一世紀中頃,迦濕彌羅國之羅漢毗盧折那來此國(于闐)傳布佛法之事,當為可靠。……故謂公元前佛教已傳入于闐,固不足怪。(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
佛教之傳入西域,時間要比內地早,但早到什么程度,現在還不能確立。……不過最遲也不會晚于一世紀,固為佛學傳入中國是在二世紀中葉,傳入內地之前,還應當有一個時期在西域流通。(呂微《中國佛教源流略講》)[2]
佛教傳入于闐大概在公元前二世紀以后,而至遲在公元前一世紀大月氏向中國內地傳入佛教之前。于闐國曾長期流行迦濕彌羅的小乘佛教。(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
自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從迦濕彌勒國(克什米爾)傳入西域以后,至魏晉南北朝,佛教在西域發展的鼎盛時期。(閻萬均《于闐與龜茲佛教之興衰》)
以上是諸位學者的觀點,僅從這些看法我們不難看出佛教在西域的傳入至晚當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
這些關于佛教傳入西域的說法不一,但筆者以為這其中必然存在著一些合理的因素。因為說法都是基于現實生活的,是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勞動和斗爭的產物,并非出于人們頭腦里的空想。
塔里木盆地作為西域佛教傳入的主要地區,具有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意義。下面就佛教初傳塔里木盆地的原因談一些筆者的看法。
(一)佛教在印度廣泛流傳時,當在公元前5至公元前2世紀左右,塔里木盆地兩側出現了由新疆最早的居民塞種人建立的大大小小幾十種之多的小國,史稱城郭諸國;并且當時塔里木盆地諸國特別是于闐和龜茲國已出現了農業和牧業的大分工,進入了農業社會[3]。而這兩個小國社會發展形態比西域諸國要先進些。此外,當時這里只有一些原始宗教觀念以及“薩滿教”,西域文化不突出,文化根基淺薄,對外來的文化沒有較強的排斥和抵制力,外來文化在這里很容易扎根。
(二)塔里木盆地曾出現過像于闐這樣的大國。于闐自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吞并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國,迫使莎車等國臣服,成為西域強國后,到十一世紀,政局一直比較穩定,并且長期致力于生產的發展,經濟比較繁榮。王室曾派侍子去中原學習先進科學文化和治國之術,而且幾代與中原王室聯姻,[4]從而加快了經濟的發展,奠立了有利于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
(三)佛教本身有兼收并蓄的特色,它能容納和吸收各種優秀文化來充實豐富自己。佛教內部的派系之爭,大多帶有明顯的學術爭論的特點,不存在毀滅對方教派的激烈行動,有利于取長補短,相互提高完善。
(四)于闐、龜茲等國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正處在絲綢之路的要沖,是多種文化交匯的樞紐,離世界古老文化發祥地并不遙遠。在當時西有波斯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埃及文化;南有印度文化;東有中原文化。當時海上交通尚不發達,更因北部的草原絲路也因自然條件惡劣而蕭條,這樣處于綠洲絲道上的于闐、龜茲,各種文化在此交匯、沖撞、融合,為這里的佛教文化發展增添了豐富的內容。
二
龜茲地區與佛教接觸時間相當早,很可能比于闐地區早[5],但由于資料缺乏,無法得出明確的時間界限,因此看法也有許多不同。李進新說: “佛教傳入龜茲的時間因缺乏史籍可考,故無定論。但至少在東漢初年,龜茲已有佛教傳布……東漢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長史班超破月氏,降服龜茲王尤利多,而立白霸為王。……這時龜茲王室已皈依佛門。”[6]湯用彤先生說: “龜茲之有佛教,不知始于何時”。[7]羽田享認為: “至于佛教何時起源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無確證。”[8]羽溪了諦對這個問題曾做了比較詳盡的論證。[9]他首先談到《阿育王息壞日因緣經》,經中談到阿育王讓與其子法益一部分領土,龜茲國名亦在其內。如這個說法可靠,則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葉,“龜茲與印度必已漸啟其佛教的關系也”。但是后來羽溪又否定了這個事實,說“殆未必然”。談到西域譯經僧中有姓(白)者,實為龜茲之姓。最終只說:“更自他方面觀察,佛傳入龜茲,當較中國為早。”始終也沒有說出一個具體時間來。余太山主編的《西域通史》第六編第四章說得很明確: “龜茲佛教傳入的年代和于闐差不多,總在公元前二世紀中,可能是通過它的西鄰疏勒傳的”,[10]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似乎晚了些。
總之,佛教傳入龜茲的時間問題是一個異常棘手的的問題,到目前尚無一確信的答案。通過上述前輩、學者的研究以及一些古代典籍,我們可以知道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到公元二世紀之間佛教在龜茲地區已開始傳入并有所發展了。
至于佛教傳入龜茲的道路,我們可以借助于前面提到的印度佛教東進的背景想像到一些龜茲佛教始傳方面的狀況。龜茲處于塔里木盆地北道的中心,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諸國與中國內地之間的往來,皆取北道,必通過龜茲。據魏書《西戎傳》所載,大月氏與中國內地在公元前發生了佛教交往。大月氏高僧東進中國內地,必途經龜茲,佛教的思想應在該地有所傳入。公元前迦濕彌羅之佛教輸入到于闐、疏勒,而于闐、疏勒與龜茲自漢朝以來,文化交往極為頻繁。《后漢書·班超傳》記載: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龜茲王攻破疏勒而殺其王,立龜茲人兜題為王,可知龜茲與疏勒的關系之密切。而佛教在此立王事件之前,由疏勒方面傳入龜茲的可能性比較大。佛教進入龜茲后早期一直流傳小乘說一切有部。
佛教傳入于闐的最初時間也是史學界十分重視而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日本著名絲路學家羽溪了諦在《西域之佛教》一書(41—43頁)中記敘:阿育王時代已有僧侶到迦濕彌羅傳教。到了公元一世紀于闐即有佛教。迦濕彌羅就是今天的克什米爾,距于闐不遠,在于闐赴南亞、中亞的必經道上,是綠洲絲路南路的必經之國,在公元前三世紀中期,佛教傳入迦濕彌羅后,經過一兩百年的發展,必然要向近鄰國家傳播,必逐漸傳入于闐是可信的。《大唐西域記》記載了一則佛教最初傳入于闐的故事,雖帶有神話色彩,但說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藍,點明了首次來于闐傳播佛教的是毗盧折那,來自迦濕彌羅。比玄奘早200多年到過于闐的宋云、惠生在他們的《行記》中,也記載了上面所說的伽藍,只是將毗盧折那譯成毗盧旃這里應是一人。又據《西藏傳》稱:毗盧折那來于闐傳教之時,在于闐建國后165年,即于闐王尉遲散婆跋治世之第5年。據羽溪了諦考證:于闐建國在公元前242年。按此推算,毗盧折那來于闐傳播佛教在公元前74年。這與羽溪了諦所言公元前一世紀于闐即有佛教之說相符。
據記載東漢永平十六年(73)班超首次來于闐時,于闐王廣德對他很冷淡,而且有個巫師從中離間,無理地要求要用班超的坐騎來祭神。班超用計殺了這個巫師,提著巫師的頭去見廣德王,廣德王見狀,便殺了早于班超來到于闐的匈奴使者,表示愿意臣服漢室。[11]證明在這段時間里,佛教在于闐尚無影響,也沒有改變于闐的國俗。直到永建二年(127)班勇率軍擊焉耆,于闐十七國皆降服。《西域傳贊論》中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這段記載說明了兩個問題:1、班勇在西域活動時期,源于身毒的佛教已在西域流傳,連班勇也知道了奉浮圖之事;2、班勇畢竟深受儒學薰陶,他回西域建功立業時,秉承其父遺志,執行兩漢一貫的西域政策,而對佛教的精微之處,則不可能深知明察。加之當時的大月氏的貴霜王朝進入全盛時期,就是迦賦色迦(78—120)當政時代,其政治勢力遠到于闐一帶,佛法也遠播至于闐。期間又發生了第四次結集。因此在這時期的于闐,佛教已有了很深的影響。并隨大月氏的軍事征服傳播進來,大致是越蔥嶺至疏勒、莎車和于闐。佛教傳播可能就是通過這條路線的。
楊富學在所著《回鶻之佛教》中,先說 “在古代印度佛教東傳過程中,西域起著至關重要作用,于闐是佛教傳入我國的第一站,傳入時間大約在公元前80年左右。”但后來又說:“龜茲與佛教的接觸相當早,甚至還有可能早于于闐。”[12]才吾加甫也說過 “西域最早佛教傳入地區是于闐。假如我們對這一論證產生疑點,將佛教傳入于闐的時間定在公元1至2世紀,等于將地乳王(于闐王)置于2世紀。則其前的于闐史將全部落空。”后來又承認 “據考證,龜茲地區與佛教接觸時間相當早,甚至有可能比于闐地區早”[13]。看以上的觀點似乎有點矛盾,究其原因,不難看到許多學者已推出一種結論:佛教較早傳入于闐,有據可循;而種種跡象又表明佛教更早傳入龜茲,但又苦于無據可循。一種觀點的提出都是要依據事實的,所以出于科學的認真負責的態度,目前學術界把于闐暫定為佛教傳入的第一站。但筆者認為,從當時對西域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龜茲佛教遠比于闐佛教大的多,早在南北朝時期,龜茲的宗教音樂和歌舞就已經傳入到了當時的長安,史書上曾記載當時西域出現的和唐朝“玄奘”齊名的佛教翻譯家鳩摩羅什[14]的父親鳩摩炎就是來自遙遠的天竺(印度),西域每逢進行大型佛教法事都在龜茲地區舉行,現有的大多數佛教建筑文化出現于庫車(龜茲)地區,從南北朝時期龜茲成為佛國到它于東察合臺汗國禿黑魯·帖木兒汗上臺后最終消亡時,大約經歷了有上千年的歷史,其影響力之大遠遠超過于闐。據此,筆者認為佛教傳入龜茲地區比于闐地區較早則更為可能。
三
與龜茲相仿,焉耆也是西域小乘佛教中心地區之一,據高僧大德法顯和玄奘記,其有“烏夷國(即焉耆)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學”,“伽藍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15]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以及至今現存的千佛洞也說明佛教在焉耆也曾有過一個特別興盛時期。龜茲、于闐作為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的入口,佛教順利傳入西域并很快取代了當地的原始宗教成為西域的主要宗教,并且出現了龜茲、于闐、疏勒、焉耆等幾個較為著名的佛教中心,在當時的西域形成了佛教蔚為大觀的景象,據《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等典籍記載,跋祿迦(阿克蘇)、疏勒(喀什)、竭磐陀(塔什庫爾干)、烏鎩(莎車)、子合(葉城)、鄯善(若羌)等地區也均流行小乘佛教的“說一切有部”。后來又傳進了大乘佛教,小乘和大乘佛教都曾在塔里木盆地流行并且以大乘佛教占據優勢。
參考文獻:
[1]季羨林·再談“浮屠”與“佛”[J].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9:93-105
[2]吳焯.從考古遺存看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J].敦煌學輯刊,1985,(2):47
[3][4]馬登杰.新疆歷史民族宗教源流述略[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01-104.
[5]季羨林.佛教傳入龜茲和焉耆的道路和時間[J].社會科學戰線,2001,(2).
[6]李進新.新疆宗教演變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113.
[7]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32.
[8]羽田享.西域文化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57.
[9]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80-183.
[10]余太山.西域通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2-15.
[11]范曄著.后漢書·班梁列傳[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04.
[12]楊富學.回鶻之佛教[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0-13.
[13]才吾加甫.漢代佛教傳入西域諸地考[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9):43
[14]楊發仁等著.新疆歷史與民族宗教理論政策教程[M].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2007:17
[15]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卷一)·阿耆尼國[M].長沙:岳麓出版社,20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