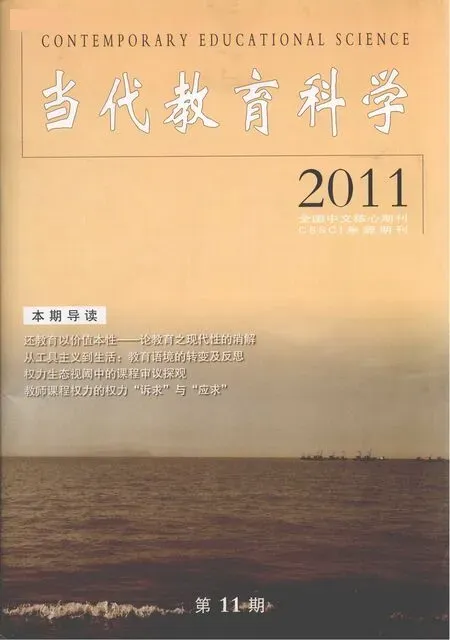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訴求”與“應求”
● 侯鐵平 封向陽
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訴求”與“應求”
● 侯鐵平 封向陽
目前有關教師課程權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參與課程權力運作中的權利保障或專業能力等領域,卻忽視了最終真正影響教師課程權力執行效能的并不是教師在課程權力運作中被制度性賦予的權利或教師執行權力的能力,而是教師在權力運作過程中所爭取到的包含行政權力與專業權力在內的綜合性權力。因此,對教師課程權力執行效能低下的歸因,不應將矛頭指向“權利”訴求亦或是“能力”訴求,而應轉向對“權力”的訴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教師課程權力的運作效能。
教師課程權力;權力訴求;權力應求
隨著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以及課程教學優化進程的加快,課程權力作為一種權力形式開始慢慢的下放于教師的教育教學過程中來。為保證教師課程權力的有效執行,一方面,國家、地方制定規章制度為教師課程權力的運作提供合法的權利保障;另一方面則對教師進行培訓,為教師課程權力的運作提供專業的能力保障。但是,教師對課程權力的表達欲求依舊不溫不火,甚至拒斥課程權力,最終造成了教師課程權力的運作失當、低效參與或主動放棄等不盡人意的執行狀況。反思教師課程權力運作的現狀,我們不難發現,最終真正影響教師課程權力執行效能的并不是教師在課程權力運作中被制度性賦予的權利或教師執行權力的能力,而是教師作為課程權力結構的最底層,由于長期受制于我國完全的國家教育決策體制的約束,教師所擁有的權力比較有限,致使教師無權可用;教師課程權力運作的場域受制于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如學校管理體制、課程評價方式、教師評價制度等,致使教師課程權力虛化,從而未能實現真正的權力自主。因此,教師課程權力的有效執行不應將矛頭指向“權利”訴求亦或是“能力”訴求,而應轉向對“權力”的訴求——爭取到包含行政權力與專業權力在內的綜合性權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教師課程權力的運作效能。
一、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訴求”
(一)課程行政權力的控制與操縱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小學的課程決策機制開始由國家決策機制走向國家、地方和學校三級相結合的模式,一時間,“權力下放”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教師課程賦權問題也開始走進研究者的視野。然而,“權力下放”的結果并沒有給教師課程賦權帶來多少驚喜,因為課程權力分配并沒有跳出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學校分權的框架,它不是建立在政府職能轉變的基礎上,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行政權力的運行機制,行政權力在教育體系內仍然高于一切,依舊凸顯其指令性權威而不是服務性職能。在當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恢復教育的公益性的過程中,政府掌控著越來越多的教育資源,承擔更多的公共教育責任的同時,行政權力隨之膨脹;控制取向、效率取向和科層取向的學校管理制度將教師排除于課程決策體制之外,這種現狀限制了教師課程權力的行使。
(二)權力控制下教師權能感的淡化
教師作為課程權力結構的最底端,受到各種權力的控制、影響與約束,這些權力力量直接作用于教師的決策行為,使之不斷被操縱、塑造、規訓,不斷服從、調整和配合,變得流暢、靈巧且熟練。[1]在權力“馴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教師失卻了對自我專業的把控力與專業自信,專業權力讓位于行政權力,專業發展服從于行政權威,造成了對專業權能感的淡漠;另一方面,長期受制于“權力控制”中的教師,形成了特定權力場域中的專業信念、價值觀、教學效能感等教師主觀的專業認知框架,這種框架幫助教師搭建起了特定教育教學行為的“心理舒適區域”,因此,當外在的課程權力下放時,由于對權力下放后的不確定感,他們則對原有的“心理舒適區域”產生了依戀感,致使教師對“行政權力”的淡漠。兩種不同方式的“淡漠”導致了課程權力下放的無力感。
二、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應求”
在上述對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訴求”的陳述緣由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教師的課程權力問題并不是由教師本身素質或國家權利保障不利所造成的,而是課程權力的下放不當、權力共享機制不健全以及對教師權力運作引導不利而導致。因此,作為對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訴求”的回應,教育行政部門應在課程權力如何真正下放到教師手中,如何實現權力共享以及引導教師實現權力有效運作等方面作出有效探索。
(一)以校本管理模式實現課程權力的重新配置與下放
“生活就是對權的尋求”。[2]只有當一種職業的從業者是自我管理的,并擁有對自己的職責的最終控制權的時候,這種職業在總體上才是自主發展的。因此,我們不能將教師的課程權力僅僅作為一種 “權利”來加以保障,而是要真正的實現“權力”擁有,不僅僅強調教師“可以做”、“應該做”,更要落實到教師“能夠做”、“必須做”的問題上來。因此,對于教育行政部門來說,首當其沖的問題便是要將整個教育體系內權力進行重新分配,國家、地方把預算、人事、課程等權力下放到各個學校,實行“校本管理”,在權力下放到各個學校后,校長則繼續放權,讓教師成為課程權力的主要執行者。
(二)通過課程權力的共享實現責任的分擔
通過權力共享,不僅能夠集思廣益,實現了權力的有效運作,而且還能夠分擔責任,共同化解矛盾。因此,削弱控制性管理職能,加大協調服務性管理職能應是政府機構及其管理體制發展的取向。轉至于課程管理領域,亦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管理層要轉變職能,改行政命令為服務體制,國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責是創設教師課程權力運作的政策制度和社會環境,幫助教師參與學校管理,參與學校事務決策,從而實現國家、地方、學校、教師四位一體的權力共享與責任分擔體系。
(三)引導教師形成權力共同體以促進權力效能的最大化
由于教師長期處于課程決策的低端,缺少必要的行政自信(相對于教育行政人員)與專業自信(相對于課程專家),因此,當下放權力于教師個體時,有可能會出現權力懸置的狀況,局限于一個人的世界,權力對其而言無任何意義。而一旦將課程權力下放于教師群體之中,首先會表現出群體對課程權力的認同,然后將實現對課程權力的參與與運作。課程權力執行過程中的爭執與討論,競爭與合作,對于教師課程權力的獲得、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專業的持續成長以及增強自我效能感,都是極為重要和行之有效的。但是需要清醒的意識到,教師權力共同體的培養方向必須既是自覺的群體,也是相互關懷的群體,還是勇于嘗試的群體,更是學習化的群體,[3]而不是為權力而進行權力角逐的群體,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教師課程權力效能的最大化。
三、權力“應求”過程中的關鍵詞
在對教師課程權力的權力“應求”過程中,由于牽扯到課程權力的方方面面,雜亂而無序,這就需要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抓住權力“應求”過程中的關鍵詞,為教師課程權力的賦權獲得正確的取向與方向提供保障。
(一)多元:建立課程權力下放的多元機制系統
目前,我國提倡分權的課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考試評價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卻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狀況就很容易引起課程權力的回流與重新集中,教師也會因為評價問題而產生危機感,進而放棄課程權力而情愿留足于先前無權的 “舒適地帶”,進而使得課程權力下放失敗。因此,在賦予教師權力時,制度保障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學校文件規定,而是全方位的保障教師課程權力實施的多元機制系統,包括權力的分配機制、監督機制、支持機制與評價機制等。特別是課程實施領域與評價領域的權力下放如果不協調的話,很容易導致教師的課程權力流于形式。
(二)漸進:防止權力不適感與權力的低效運作
課程權力的下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由原來的“無權”到“少許權力”的獲得,然后到“合適權力”的擁有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漸進,一方面可以減少教師對于下放權力的不適感,從而消除其躲避或者逃離課程權力的狀況;另一方面,可以保證課程權力下放的連續性和有效性,使課程權力能夠更好的實現正常運作。
(三)理性:把握權力權項與教師課程權力的關聯性
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我們不應將課程權力共享或共有的籠統表述直接拋給教師,而是要對課程權力進行細分,界定各權力權項的強度、性質、內容以及這些權項與教師課程權力運作的關聯程度。例如,有些課程權力必須由政府行使,那就必須按照國家權力的運行機制——即強制的規則運行,有些權力必須由學校行使,那就要按照學校權力的運行法則——即自我管理的規則運行,而有些權力則必須由教師行使,則就需要遵循個人自主的法則運行。不是歸屬于教師課程權力范圍內的,應加以剔除,而隸屬于教師課程權力范圍內的,教育行政則要讓位,從而實現二者權力的“互補”與“促進”。
(四)法治:增強權力的行動性與操作性
權力具有行政性的屬性,無授權就無法行使權力,因此,教師課程權力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授權方能有效的運行。為此,一方面在教育行政方面,應不斷完善《教育法》和《教師法》及其相應的行政法規與政策等,盡快在制度上確立教師的自主權力和專業地位,為教師的課程賦權營造適宜的政策與社會環境,提供行政與輿論支持。另一方面在學校管理方面,應建立健全教師行使自主權力和落實專業地位的運行機制和內部環境,將校本課程的開發與課堂教學的權力還給教師,為教師提供運行課程權力的實踐基地。
[1]何巧艷等.教師課程決策本性的文化分析[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5).
[2]錢滿素等.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86.
[3]曾文婕等.美國教師“賦權增能”的動因、涵義、策略及啟示[J].課程·教材·教法,2006,(12).
侯鐵平/河北北方學院文學院講師 封向陽/渤海石油職業學院人文系講師
(責任編輯:孫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