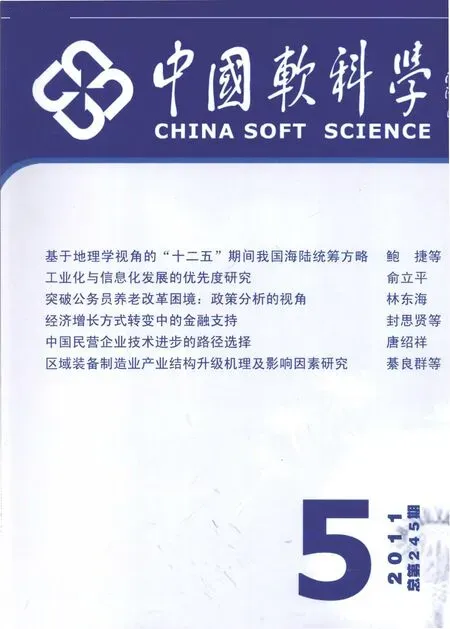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金融支持——來自長三角的實證分析
封思賢,李政軍,謝靜遠
(1.南京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2.中國進出口銀行 南京分行,江蘇 南京 210029)
一、引言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存在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Mckinnon(1973)[1]、Shaw(1973)[2]、Beck 等(2000)[3]、Rioja和Valev(2004)[4]等大量文獻也早就從多方面論證了這種增長效應。在本輪金融危機發生初期,各國政府便根據這種增長效應迅速出臺了一系列拯救經濟的金融措施,并期望以此來避免金融危機向經濟危機蔓延。然而,后危機時期經濟艱難復蘇且前景仍不明朗的現實背景,必然要求我們對金融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新的深刻思考。在當前及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轉變增長方式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翻開長三角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最新“十二五”發展規劃,不難發現,江蘇、浙江、上海均把發展金融業作為轉變本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措施之一。長三角的許多措施更是經常被國內許多其他省市借鑒和應用,然而,后危機時期,經濟演變的復雜性需要我們對“金融在多大程度上并通過哪些渠道來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做出科學判斷。基于此,本文將以長三角為例,分析金融支持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的相互關系。
從已有相關文獻來看,專門討論金融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系的文獻還十分稀少,絕大多學者重點研究的是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如Goldsmith(1969)[5]曾指出:“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不是最重要問題,也是重要問題之一。”但正如Goldsmith所說:“但是,我們無法弄清這種聯系究竟意味著什么;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增長呢,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一種反映?”King和 Levine(1993)[6]等延續了 Goldsmith 的工作,分析了金融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早期的相關研究大多以銀行業代替金融業,但在現代金融體系下,討論金融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時,僅僅考慮銀行是不夠的。為了更準確地衡量金融支持,需要引入股票、債券等金融子市場。在此 基 礎 上,Arestis、Demetriades和 Luintel(2001)[7]發現,雖然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解釋了后來的增長,但是銀行的影響遠比股票市場大。Rioja和 Valev(2004)[4]卻認為,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不同的,只有發達地區或基于市場的金融體制才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國內方面,談儒勇(1999)[8]最早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王定祥等(2009)[9]認為,金融資本適度形成是經濟實現最優增長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國金融資本和真實資本之間的轉換制度缺乏充分的彈性,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和金融之間并未體現出有利的相互促進關系。趙勇、雷達(2010)[10]認為,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存在較大差異;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降低增長方式轉變的門檻值來推進經濟發展向集約型轉變。在分析視角上,上述文獻給本文的啟示至少有三點:金融與增長方式轉變的關系分析不能只是單方向的;不能只考慮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金融,必須綜合考慮資本市場;不同的區域或經濟體制應區別分析。
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結構安排是:在第二部分,本文將基于索羅經濟增長模型(Solow,1957)[11],給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的衡量指標和計算方法,并根據結果探討長三角增長方式的特征;第三部分是給出具體的金融指標,并建立金融與增長方式轉變效率的計量模型;第四部分將利用第三部分的模型與長三角的數據,實證分析金融支持與增長方式轉變的相互關系;第五部分為全文的結論和相應的政策性建議。
二、長三角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的衡量
(一)衡量指標的選擇
經濟增長的核心內容是效率,生產率自然為人們所關注。生產率是指生產過程中投入品轉化為產出品的效率,分為單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來自于兩個方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TFP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其計算方法是:

在現實經濟中,由要素投入增加對經濟增長起主導作用的增長方式稱為粗放型,由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起主導作用的增長方式稱為集約型。全要素生產率是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反之則意味向粗放型轉變。根據Solow(1957)等提出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從長期來看,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如果僅通過要素投入的增加來驅動經濟增長,則經濟增長很難持續,因此,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在于積極轉變增長方式。
基于上述判斷,本文用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效率。
(二)全要素生產率(TFP)年增長率的計算
1.計算公式
遺憾的是,由于統計等因素,TFP無法直接從公式(1)中計算出來。本文將在Solow(1957)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結合經濟計量方法給出全要素生產率的間接估計方法。
在Solow(1957)經濟增長模型中,總的產出函數是:

下標 t表示時間,Y、A、K、L、α 分別表示總產出、技術進步、資本、勞動和資本產出彈性。在假設L不變時,對人均化的產出函數取自然對數并對t求導,得到增長方程式:

其中,gAt是 TFP的增長率①此模型中,Solow把TFP的增長視為技術進步的反映,把技術進步視為轉變增長方式最核心的因素。,gyt是 GDP增長率,gkt是資本存量增長率。由于gyt和gkt可以根據統計年鑒上的相關數據計算出來,因此,只要能夠估計出資本的產出彈性α,就可以從式(3)中計算出TFP的年增長率gAt。
2.數據處理
要估計長三角的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需要1978-2009年的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存量的數據。本文所稱的長三角是廣義上的概念,包括江蘇省、浙江省和上海市。GDP數據來源于《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和《中國統計年鑒》。本文利用江蘇、浙江、上海各省市的GDP指數和當年價格GDP計算出隱含的GDP價格指數,對當年價格的GDP數據進行平減,得到以1978年為基期的GDP時間序列。
關于資本存量Kt的測算方法,本文采用Goldsmith于1951年開創、現在被OECD國家廣泛采用的永續盤存法(PIM),它的基本公式是:

其中,It是當年凈投資,δ是資本折舊率。計算資本存量Kt需要解決四個指標:當年投資量It的選取、固定資本投資價格指數的確定、固定資產折舊率δ和基年(1978年)資本存量的確定。
由于現有投資有一部分是用于研究開發而并非全部服務于生產,因而,結合內生技術進步理論,在選擇It數據時,本文采用的是扣除對技術投入補償后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根據統計年鑒顯示的數據規律,扣除比例為5%。本文利用固定資本形成額和統計資料中已計算的各省固定資本形成指數,計算出長三角的固定資本價格指數。結合王小魯和樊綱(2000)[12]、龔六堂和謝丹陽(2004)[13]等人的研究,本文取δ=13%。根據張軍(2003)[14]對全國固定資產800億元(1952年價格)的估計以及長三角GDP占全國比例,我們估計1952年長三角的資本存量為88.7億元(1978年價格)。據此,由式(4)得到1978年的長三角資本存量為529億元(1978年價格)。
有了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存量的數據,便可以估計資本產出彈性α了。在Solow(1957)的分析框架中,產出是資本的指數函數,取對數后得到估計α的線性計量模型:

其中,c是截距項,εt是隨機擾動項。但是,只有當lnyt和lnkt兩個序列全是平穩時,才可直接利用式(5)得到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1。因此,必須首先檢驗兩個序列的平穩性。
本文采用的平穩性檢驗方法是ADF(單位根)檢驗法。由于我國的宏觀經濟體制在1994年末實施了“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改革,因而,根據我們從文獻綜述獲得的啟示,我們將檢驗分兩個時間段:1978-1994年和1995-2009年。
檢驗發現:1978-1994年,lnyt和lnkt兩個序列全平穩。式(5)的計量結果是:R2=0.71,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1=0.61(對應的t值統計量為4.75,結果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1995-2009年的lnyt和lnkt兩個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進一步對兩序列的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檢驗,得到lnyt和lnkt兩序列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于是,得到計量模型:

式(6)的計量結果是:R2=0.62,1995-2009年的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2為0.4(對應的t值統計量為4.42,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3.計算結果
將得到的兩階段資本產出彈性系數分別代入式(3),并將結果合并在一張圖上,我們得到了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圖1)。圖1顯示,長三角兩個階段的TFP增長呈現較明顯的短期波動性特征。1979-1994年,TFP增長速度緩慢,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16%;1995-2009年,TFP增長加快,年均增長率達到4.5%。這表明:在計劃經濟階段,長三角的經濟增長方式并未得到有效的積極轉變。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1995-2009年,長三角的經濟增長方式處于快速積極轉變之中。這也可以從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的計算結果中得到驗證。α的含義是資本存量Kt每增加1%,產出增加α%。在GDP增長率既定條件下,資本產出彈性估計值α越大,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就越高,TFP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就越低。1979-1994年的α1為0.61,明顯大于1995-2009年的α2(α2=0.4),這表明長三角1979-1994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比較傾向于粗放的投資拉動型,而1995-2009年比較傾向于集約型。

圖1 長三角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1979-2009)
三、變量選擇、數據描述與研究方法
金融支持是指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推動、調度和潤滑作用。根據本文第一部分歸納的幾點啟示,本文將可能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金融支持因素分為三個主要方面:銀行發展、證券市場發展和金融開放。
(一)變量選擇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用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來衡量,我們用g(即gAt)表示。
銀行業發展的主要體現是其規模和效率,本文分別用TFIR和BVAR表示。借鑒包群、陽佳余(2008)[15]等成果,TFIR用當年“全部金融機構新增的存貸款金額之和占名義GDP的比率”來計算,這一指標也被各種文獻稱之為“金融相關比率(Total 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TFIR)”。“貸款利息 -存款利息+中間服務收入”是銀行類金融機構最主要的增加值(bank value added),反映的是銀行經營績效,因而,本文用本地當年銀行類金融機構“(貸款利息 -存款利息+中間服務收入)占當年銀行類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比例”來計算BVAR。
證券市場包括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對應地,我們分別用SMR和SVR表示。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主要體現為A股市場。因而,SMR用“當年長三角上市公司A股市場融資總額占名義GDP的比率”來計算,反映本地區獲得的股票市場融資支持力度。SVR用“當年本地區年末上市公司的A股市值占名義GDP的比率”來計算,反映二級市場。
根據WTO協議,我國金融業的全面對外開放直到2006年底才開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幾年,因而,我們難以直接用外資金融數據來衡量金融市場開放程度①自2001年6月開放以來,B股市場的參與資金主要來自境內;長三角H股上市公司數量不多且外商直接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是通過金融市場等原因。因此,本文曾有的“用B股、或H股、或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來衡量金融開放程度”等想法最終沒被采用。。金融開放不僅體現為對境外開放,也包含對內開放。長期以來,國有金融機構壟斷著我國的金融市場,因此,對我國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個地區非國有金融機構的市場占有比例可以被用來反映該地區對內開放程度。本文用“非國有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占全部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之比”來替代長三角的金融開放程度(FOR),計算方法是“FOR=(全部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 -國有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全部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
這樣,我們選擇了g(增長方式轉變效率)、TFIR(銀行業發展規模)、BVAR(銀行經營效率)、SMR(證券一級市場發展)、SVR(證券二級市場發展)和FOR(金融開放)共6個變量來尋找長三角金融支持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相互關系。
(二)數據描述
g的數據來自圖1。其他5個指標的計算方法已在“(一)變量選擇”中給出。
計算TFIR和BVAR的原始數據是1978-2009年的年度數據,主要來自《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的“各地經濟金融篇”、《上海市統計年鑒》、《江蘇省統計年鑒》、《浙江省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各地統計信息網和近年來各地的《金融運行報告》。
由于我國的兩個證券交易所直到1991年才全部成立,因而,計算 SMR和 SVR的數據時間是1991-2009年,原始數據源自天相數據庫。
計算FOR時,銀行類金融機構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含農村信用社)、財務公司、郵政儲蓄和外資銀行。國有銀行類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開放后,真正意義上的非國有銀行起始于1987年4月正式對外營業的、第一家由企業投資創辦的招商銀行。因而,計算FOR時,本文選取的時間為1987-2009年,原始數據來源同TFIR和BVAR。
(三)研究方法
由于各變量的時間無法統一,因而,本文對金融支持的分析將分別從銀行發展、證券市場發展和金融開放等三方面展開。
首先,我們將檢驗g分別與金融5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然后,對存在相關關系的g和金融各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并借助協整理論從整體上判斷g與相關金融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②協整理論認為,盡管多個變量的時間序列自身是非平穩的,但如果這些時間序列均是同階單整、且這些變量之間存在某個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這些變量之間被認為存在協整(cointegrated)關系。,判斷金融各變量是否是決定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將檢驗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來討論金融各變量與增長方式轉變之間“誰是因,誰是果”,即判斷是金融支持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轉變,還是增長方式轉變促進了金融發展。
為防止偽回歸,本文將首先對各時間序列變量作單位根(ADF)檢驗。檢驗過程依序采用“帶趨勢和截距項模型、帶截距項模型、不帶趨勢和截距項模型”,何時檢驗出平穩,何時停止檢驗。否則,就要繼續檢驗,直到檢驗完最后一個模型為止。其中最優滯后期(p)的確定是基于赤池(Akaike)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Schwartz)準則(SC)給出,即在增加p值的過程中使AIC值或SC值達到最小。
協整檢驗的一般方法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兩步法。然而,當對兩個以上的變量作協整分析時,這種方法存在一個較大的缺陷:把不同的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時,可能檢驗得到不同的協整向量。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跡統計量協整檢驗方法。如果存在著協整關系,則意味著二者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對于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研究,一般采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法。但是,Granger因果檢驗只能檢驗變量間的長期因果關系,而無法度量變量間的即時因果關系,而且對于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的兩變量,Granger檢驗無法估計并比較雙向因果關系(又稱反饋)的相對大小。為此,本文采用Geweke(1982)[16]的分解檢驗法(Geweke decomposition test)。Geweke(1982)把變量X和Y的因果關系(記為FX,Y)分解為:X對Y的因果關系(記為FX→Y)、Y對X的因果關系(記為 FY→X)以及 X 和Y的即時因果關系(記為FX·Y)。各因果關系之間的聯系如下:

對于時間序列X和Y,Geweke(1982)提出如下規范表達式來檢驗兩者間的因果關系:

其中,最佳滯后長度p和q可以運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加以確定,FX→Y、FY→X、FX·Y和 FX,Y為零的原假設的最大似然檢驗值①Geweke(1982)證明這些統計量服從χ2分布,且對于FX·Y的度量,In分別為:

其中,n為觀測值的個數,d為兩配對模型自由度的差。對比式(11)與式(13)、式(8)與式(10)可知,自由度d=q。
四、實證結果
本文采用的計量軟件是EVIEWS6.0。
(一)相關性分析結果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金融支持的5個變量分別與增長方式轉變效率g之間的相關性呈現不同特點。衡量銀行業發展的TFIR與 g之間、BVAR與g之間,衡量證券一級市場的SMR與g之間、衡量金融開放的FOR與g之間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7643、0.9481、0.5045和0.766),而衡量證券二級市場的SVR與g之間的相關性未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二)協整檢驗結果
相關性分析結果并不表明兩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判斷長期均衡關系需要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的變量檢驗協整關系。由于金融支持的各變量時間不統一,因而檢驗將依序從BVAR、TFIR與 g之間,SMR與 g之間,FOR與 g之間展開。
得到的平穩性檢驗結果是:各變量的時間序列均是非平穩的,而各變量一階差分的時間序列均是平穩的,即各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在此基礎上,通過計算跡統計量,我們得到協整結果(表1)。

表1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g)與金融支持各變量之間的協整檢驗結果
通過比較表1中的跡統計量與臨界值,我們發現: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r=0的假設被拒絕,r≤1的假設通過檢驗。這說明:在長三角,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與銀行業發展之間、增長方式轉變效率與本地上市公司融資規模之間、增長方式轉變效率與其金融開放程度之間,均分別存在唯一的長期均衡關系。
(三)Geweke因果關系分解檢驗結果
協整關系只能說明變量間存在長期相關關系,而不能說明增長方式轉變效率與金融支持之間有因果關系。基于赤池信息準則(AIC),在式(8)-(13)中,g、TFIR和BVAR的最佳滯后期為1,而SMR和FOR的最佳滯后期為2。根據前述Geweke分解原理,得到結果(表2)。

表2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效率與金融支持之間的因果關系分解檢驗結果(Y=g)
表2顯示:
(1)關于銀行發展與增長方式轉變效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從FX,Y列的結果來看,轉變效率與銀行業發展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從TFIR欄來看,銀行信貸規模(TFIR)與g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但從反饋份額來看,更多地表現為g對TFIR的因果關系(55.90%);從即時因果關系(FX·Y)來看,長三角的銀行存貸款不僅長期影響轉變效率,短期也顯著影響。再從BVAR欄來看,BVAR與g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這種因果關系不是雙向的,而是轉變效率g的變化引起了銀行業內部效率的變化(檢驗BVAR對g因果關系的相伴概率為0.1209,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
(2)關于證券市場與轉變效率之間的因果關系。SMR欄顯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的證券市場融資規模(SMR)與轉變效率(g)之間均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從反饋份額來看,SMR與g的即時關系(FX·Y)所占比重卻很小(14.02%),而SMR對g產生因果影響的反饋份額(40.86%)和g對SMR產生因果影響的反饋份額(45.12%)則大體相當。這說明,兩者的雙向因果關系中,短期影響較少,而長期內兩者相互產生因果關系的程度相當。
(3)關于金融開放與轉變效率之間的因果關系。FOR欄顯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金融開放與轉變效率之間均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從反饋份額來看,這種反饋關系更多地反映為金融開放對增長方式轉變效率的影響(46.79%)。這說明,長三角的金融開放對本地增長方式轉變的滲透力、影響力和推動力已越來越強。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長三角地區的銀行信貸規模、銀行經營效率、證券一級市場、證券二級市場、金融開放等金融支持的五個方面,探討了其與本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的相互關系。現小結如下:
(1)信貸規模與增長方式轉變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這種雙向關系更多地體現為轉變效率的提高促進了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張。這表明,長三角地區銀行的信貸投放結構總體上不盡合理,本地銀行應從改善內部經營管理等方面提高應對宏觀經濟困境的能力。
(2)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轉變促進了長三角銀行內部效率的提高,但銀行內部效率的提高并未明顯促進長三角地區增長方式的積極轉變。這表明,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還未成為長三角的核心產業。同時也提醒,國內經濟發展相對欠發達的地區不宜模仿長三角而把金融業作為“十二五”重點發展的行業之一。
(3)長三角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轉變促進了本地區企業的證券市場融資,證券市場的融資便利也顯著促進了本地增長方式的積極轉變。但是,證券二級市場并未明顯體現出其與本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相關關系。這說明:具有一級市場特征的股權融資在促進增長方式轉變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國的證券二級市場急需規范。
(4)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長三角地區的金融開放與其增長方式轉變之間均存在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兩者相互促進。這表明,即使在目前的后危機背景下,對長三角地區而言,無論是發展金融業、還是促進增長方式轉變,有序、加快推進金融開放都是應堅持的改革方向。
為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國實施了以信貸規模擴張為主的金融政策。然而,本文的研究結果提醒我們,無論是應對危機還是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優化金融支持結構更應成為未來政策制定時考慮的重點,即應根據銀行、證券、金融開放以及各自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的不同效應,區別對待。在利用銀行信貸支持來促進增長方式轉變時,既要優化信貸結構,有針對性地對環保、能源等重點領域和民生等重點環節進行支持,又要完善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銀行的經營效率。在利用證券市場措施時,應盡快發展公司債券市場,并重點發展具有股權融資特征、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私募股權市場等;在促進金融開放方面,“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是必須堅持的改革方向,既要爭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政府間貸款及國際銀行組織的專項貸款,進入國際證券市場融資,又要發展民營金融企業、引入外資金融機構并鼓勵有序競爭。
[1]Mc Kinnon.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2]Shaw.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Beck, Thorsten & Levine, Ross & LoayzaNorman.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1-2):261-300.
[4]Rioja F.,Valev N.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at Various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Economic Inquiry,2004,42(1):127-140.
[5]Goldsmith,Raymond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6]King,Robert G & Levine Ross.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717-737.
[7] Arestis, P., Demetriades, P.O., & Luintel,K.B.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Stock Market[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1,33(1):16-41.
[8]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 經濟研究,1999,(10):53-61.
[9]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金融資本形成于經濟增長[J]. 經濟研究,2009,(9):39-51.
[10]趙勇,雷達.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生差率促進抑或資本形成[J]. 世界經濟,2010,(2):37-50.
[11]Solow 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12]王小魯,樊綱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13]龔六堂,謝丹陽.我國省份之間的要素移動和邊際生產率的差異分析[J].經濟研究,2004,(1):45-53.
[14]張軍,章元.對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J].經濟研究,2003,(7):35-43.
[15]包群,陽佳余.金融發展影響了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較優勢嗎[J]. 世界經濟,2008,(3):21-33.
[16]Geweke J.Measurement of Linear Dependence and Feedback between Multiple Time Series[J].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2,(77):30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