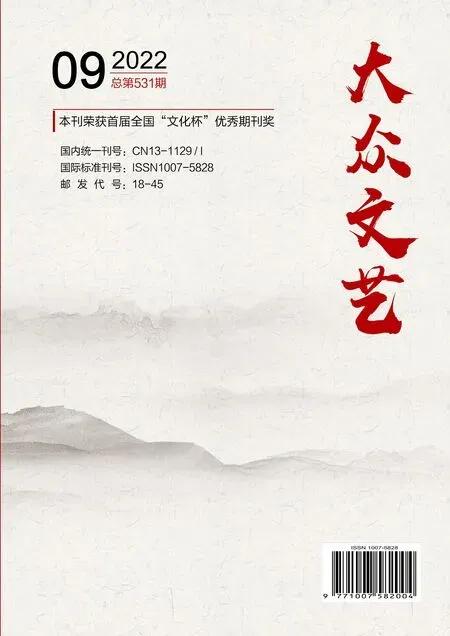兩漢西南地區(qū)石碑形制及其特點(diǎn)
楊子墨 (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 山東濟(jì)南 250000)
兩漢西南地區(qū)石碑形制及其特點(diǎn)
楊子墨 (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 山東濟(jì)南 250000)
中國(guó)古代銘刻文字常鑿于巖壁,刊之石碣。東漢,一種外形規(guī)整、制作講究的石刻形式——石碑,驟然完善并遍及全國(guó),正如劉勰《文心雕龍?誄碑》所言:“自后漢以來(lái),碑碣云起”。漢代石碑主要集中于黃河中、下游及長(zhǎng)江上游的廣大地區(qū),涉及山東、河南、四川、山西、陜西等二十幾個(gè)省市。其中地處西南邊陲的四川、重慶、云南等地,石碑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此地石碑以四川成都為中心,東起渠縣,北抵成縣,西達(dá)蘆山,南止昆明,為漢代漢中郡、武都郡、巴郡、蜀郡、越嶲郡、鍵為郡、益州郡轄區(qū)。
全境地處西南邊陲,崇山峻嶺,河流縱橫,交通不便,素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之語(yǔ)。先民為了方便與其他地區(qū)的交流,打破地域封閉隔絕的狀態(tài),開(kāi)山建路,發(fā)展交通。各種地界碑和有關(guān)鑿山修路的紀(jì)事碑常見(jiàn)于此,如《延光石刻碑》《長(zhǎng)王君石路碑》《修道碑》《李翕天井道碑》《趙孟麟羊竇道碑》《安長(zhǎng)陳君閣道碑》《蜀國(guó)造橋碑》《長(zhǎng)王君平鄉(xiāng)道碑》等。
兩漢中央政權(quán)為開(kāi)發(fā)西南地區(qū)經(jīng)濟(jì),對(duì)其采取“以其故俗而治”〔1〕的靈活政策,大力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部分紀(jì)事碑、功德碑記錄了當(dāng)時(shí)廣開(kāi)渠道、興修水利的盛況,《沈子琚都江堰碑》《郭擇、趙汜碑》就屬這一類(lèi)。
本地少數(shù)民族眾多,族人皆信奉巫術(shù),區(qū)內(nèi)事物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先秦,人們崇拜神靈、信奉巫術(shù)、薩滿巫術(shù)籠罩全區(qū),表現(xiàn)出古老原始的宗教氛圍。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guó)后,令大量楚民遷至川東,以至“江州以東,濱江山險(xiǎn),其人半楚”〔2〕,荊楚文化與道教思想隨之而入。《漢書(shū)?地理志》記載,楚人“信鬼神,重淫祀”,這與本區(qū)悠久的巫術(shù)崇拜相契合,使其神仙巫術(shù)繼續(xù)發(fā)展,成仙得道的思想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先秦荊楚之地以龍鳳為崇拜對(duì)象,如《離騷》曰:“吾令鳳鳥(niǎo)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駕八龍之蜿蜿兮,載云旗之委蛇”,《春秋握成圖》又錄劉邦之父“劉媼夢(mèng)赤鳥(niǎo)如龍,戲已,生執(zhí)嘉”;而巴蜀之地則崇拜白虎,樊綽《蠻書(shū)》言:“巴氏祭其祖,擊鼓為祭,白虎之后也。”漢代,本區(qū)將荊楚文化的龍鳳和巴蜀文化的白虎圖紋結(jié)合,使龍鳳、白虎圖像大量裝飾于建筑、服飾及雕塑等各種物件內(nèi)。在此影響下西南地區(qū)碑面多施畫(huà)像,題材涉及神話傳說(shuō)、升天成仙、四神靈獸等內(nèi)容,與北方古樸簡(jiǎn)純石碑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王孝淵碑》碑陽(yáng)淺浮雕朱雀、夫婦、仕女像,碑陰有伏羲、女?huà)z、蟾蜍、朱雀、牛首、鹿、圭、璧、璜,碑側(cè)浮雕青龍、白虎,是現(xiàn)存最早碑側(cè)裝飾龍虎圖案的實(shí)物。《朐忍令景云碑》碑面雕琢日、月、青龍、白虎、朱雀、婦女啟門(mén)及兔首人身像,其中婦女高盤(pán)發(fā)髻、半倚門(mén)廊、翹首眺望、面含思緒,真實(shí)生動(dòng)地表達(dá)了妻子守家盼夫的渴望之情。此類(lèi)表現(xiàn)墓主人夫婦現(xiàn)實(shí)生活及情感的畫(huà)像為古代西南地域所特有。四川郫縣《王孝淵碑》碑陽(yáng)的夫婦仕女圖,滎經(jīng)《東漢石棺》的秘戲圖,以及蘆山《王暉石棺》《東漢石刻樓房》的婦女啟門(mén)圖等,它們?cè)⒁庵怪鞣驄D之間真摯的愛(ài)情,寄托了遺孀對(duì)亡君的思念之情,充分流露了古代四川民眾的浪漫主義情懷。
儒家學(xué)說(shuō)及其思想在該區(qū)傳播較晚。景帝末年,文翁“見(jiàn)蜀地僻陋有蠻夷風(fēng)”〔3〕于是“立文學(xué)精舍講堂”,〔4〕派蜀中學(xué)子至京師太學(xué)深造,使儒學(xué)文化在此傳播。由于本區(qū)長(zhǎng)期對(duì)神仙巫術(shù)的青睞,巴蜀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于今文經(jīng)學(xué)的災(zāi)異學(xué)說(shuō)及讖緯之說(shuō)。但無(wú)論吸取那種學(xué)說(shuō),此區(qū)對(duì)于儒學(xué)文化的認(rèn)可,為其接受漢代儒家倡導(dǎo)的厚葬禮儀給予了有利的思想保證,致使?jié)h末巴蜀地區(qū)厚葬之風(fēng)尤勝,正如《華陽(yáng)國(guó)志?蜀志》記錄:“工商致結(jié)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聚嫁設(shè)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從車(chē),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贈(zèng)襚兼加,赗賻過(guò)禮”。繁縟的喪葬禮儀,使墓碑大量出現(xiàn)。部分墓碑還搭配石獸、石闕立于墓冢前,與中原冗繁考究的墓上石刻組件形式一致,現(xiàn)今四川雅安高頤墓、樊敏墓仍保留完整的墓上建筑。高頤墓址,墳冢、神道、石闕、石獸、墓碑皆保存完好。雖石闕與石獸位置略作調(diào)換,石碑多有移位,但整體位置及形式仍保留原貌。墓上石獸體態(tài)矮小,造型別致,獸首張口吐舌,多作昂首跨步、挺胸彎腰之姿態(tài),威猛強(qiáng)健盡現(xiàn)其中。
東漢獻(xiàn)帝時(shí)期,北方政局混亂,社會(huì)動(dòng)蕩,石碑發(fā)展停滯不前。地處邊陲的西南地區(qū)為防止北方戰(zhàn)亂侵蝕,將其“牦牛道一度閉塞,郵驛廢止”,切斷與中原的聯(lián)系。使本區(qū)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的政局形式,為石碑制作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蟠螭圓首碑在此成熟發(fā)展。此類(lèi)石碑造型沿襲暈紋圓首碑形制,獸身沿碑暈弧線紋走勢(shì)布置,獸頭下垂位居碑首左右兩端,這種獸即是螭。《說(shuō)文》釋“螭”曰:“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從蟲(chóng),離聲,或無(wú)角為螭。”《漢書(shū)?司馬相如傳》謂“蛟龍赤螭”。孔穎達(dá)疏:“龍子為螭……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它是古人想象出的一種神獸,凡是龍形有角無(wú)鱗者稱(chēng)虬,無(wú)角無(wú)鱗者為螭。虬、螭為同類(lèi)異體,故古人皆以虬螭并用,或以螭代虬。現(xiàn)存完整的蟠螭圓首碑為四川雅安《樊敏碑》和《高頤碑》。
此類(lèi)石碑上窄下寬,這種“收分”的建筑處理,既增加了石碑穩(wěn)定性,又曾添了“崇高”的視覺(jué)美感。《樊敏碑》和《高頤碑》高寬比例2∶1,寬度皆在100厘米以上,最寬達(dá)133厘米,寬廣的碑面給人以開(kāi)闊博大的審美效果。碑首構(gòu)圖飽滿充實(shí),獸體肥碩寬大。螭足盤(pán)纏鑲嵌軀體,左側(cè)兩螭首尾并行交匯,右側(cè)僅飾一螭首。碑座形式多樣,龜趺、長(zhǎng)方形均有涉及。《樊敏碑》龜趺造型巨大,形象逼真,龜首偏向一方,十分生動(dòng)。《高頤碑》長(zhǎng)方形碑座寬廣扁平,浮雕虬螭二獸,左右相對(duì),口銜綬帶,共合玉璧,十分別致,是長(zhǎng)方形碑座中的精品。
除此之外,暈紋圓首碑、方首碑等形制都與北方地區(qū)形成鮮明的差異。東漢時(shí)期,北方暈紋粗壯清晰,它采用減地陽(yáng)刻的手法,即在磨平的半圓形碑首上,鐫鑿三道凹槽,使暈紋呈平面凸顯出來(lái)。暈紋寬度約計(jì)10厘米,醒目突出,諸如《孔彪碑》、《韓仁銘》《仙人唐公房》等。南方暈紋纖細(xì)流暢,以浮雕技法,逐層排疊拱面,由高到低,形成三條暈紋弧線,《楊君銘碑》《朐忍令景云碑》等均為此類(lèi)。方首類(lèi)碑首頂端置有榫頭,并配置屋檐狀碑帽,碑面四周留有矩框以作裝飾,如《王孝淵碑》《李君碑》《裴君碑》。2010年11月5日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府廣場(chǎng)的《李君碑》和《裴君碑》石碑,二者皆有碑帽,狀若中國(guó)古代建筑木結(jié)構(gòu)之屋檐狀,其整體形制猶如漢代石闕,以起到對(duì)石碑的保護(hù)與裝飾的雙重作用,造型別致為漢代四川地區(qū)所獨(dú)有。
本區(qū)碑文書(shū)法采用隸書(shū),結(jié)體方正,筆畫(huà)渾厚,書(shū)風(fēng)稚拙。這與西南地區(qū)裸露著廣闊的泥灰質(zhì)巖石有密切關(guān)系,此類(lèi)石質(zhì)內(nèi)各化學(xué)成分在溶蝕、風(fēng)化的作用下,易發(fā)生物理力學(xué)變化,再加上石質(zhì)多呈顆粒狀碎屑結(jié)構(gòu),直接影響了碑面紋飾及書(shū)法細(xì)部刻劃,使碑文書(shū)法略顯樸拙。
同時(shí),漢代四川地區(qū)石碑碑文多記錄工匠姓名,張伯嚴(yán)、劉盛二人常刊于碑文之后。可見(jiàn),當(dāng)?shù)厥淌止I(yè)的發(fā)達(dá)及石碑制作的商品化。
綜上所述,西南地區(qū)石碑傳承久遠(yuǎn)、形制講究、裝飾華麗、石刻配置齊全,特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使其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各類(lèi)石碑內(nèi)容及形制的的形成與發(fā)展,既表現(xiàn)出它對(duì)北方中原和南方荊楚地域文化的吸收、融合及互動(dòng),也表現(xiàn)出石碑地處自然間隔地帶,獨(dú)立完善成熟的特殊性。
注釋?zhuān)?/p>
〔1〕(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
〔2〕(東晉)常璩《華陽(yáng)國(guó)志?巴志》.
〔3〕(東漢)班固《漢書(shū)?循吏傳?文翁傳》.
〔4〕(東晉)常璩《華陽(yáng)國(guó)志?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