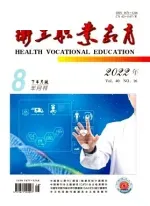醫學教育模式的演變及其動因
醫學教育模式的演變及其動因
趙同領,曹云飛,柳 亮,陳金梅,李 頎
(廣西醫科大學,廣西 南寧 530021)
通過認真分析和考察醫學教育模式的發展和演化過程,探索醫學教育模式演變的動因,以便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醫學教育模式的理論基礎及其演變。
醫學教育模式;演變;動因
醫學教育模式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特別是在新舊醫學教育模式轉變階段,它們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滲透是難免的,即使新的醫學教育模式取得了支配地位,舊的醫學教育模式也不會立即消失。鑒于此,將醫學教育置于歷史的顯微鏡下,探索是什么力量推動醫學教育發生變化,而且還將繼續發生變化,對于理解醫學教育模式的變遷和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1 醫學教育模式的演變
1.1 以師帶徒形式的醫學教育
在歐洲中世紀之前,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不足,無法區別自我與環境,認為人類和自然界的萬物一樣,受到一種神秘力量的支配,人類的生命與健康是上帝所賜予,疾病和災禍是天譴神罰[1]。雖然當時已經出現了醫師(巫師、通靈師),但是人們患病之后主要的應對手段是求神問卜、符咒祈禱,很少求醫。由于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低下,人類對自我認識是膚淺的、粗糙的,醫學知識貧乏,純書本知識就更少了。醫生如同其他工匠一樣,其醫療知識主要來自經驗。醫學知識的傳授者把醫學作為一種手藝,主要以口頭形式傳授給自己的徒弟。在醫學教育出現固定場所之前,醫學教育主要是以師帶徒形式展開。
1.2 中世紀醫學教育
中世紀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時代。按醫學知識傳授的場所不同,可以把這個時期的醫學教育分為修道院醫學教育和大學醫學教育。
1.2.1 修道院醫學教育 10世紀以前,在宗教文化的影響下,僧侶醫學盛行,修道院既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傳習醫學知識的學校。醫學著作主要是問答式的醫學著作;教學法主要是問答式的教學方法;理論學習的目的在于解釋和論證圣經的真實性,而不是對人類自身的認識;學生必須死記希波克拉底、蓋倫、阿維森納等權威著作的教條;書本對醫學的實踐方面僅僅是加以描述,而學習醫學的人并不完全付諸實施。由于受“經院哲學”的影響,理論與實踐分離,認識對象錯位,修道院培養出了具有濃厚神學色彩的只會坐而論道的修道士醫生(牧師醫生),這與社會需要的醫生大相徑庭,同時這也極大地制約了醫學的發展。直到11世紀以后,隨著大學的興起,修道院醫學教育逐漸為大學醫學教育所取代。醫學進入大學,開始分享神學和法學的特殊榮耀[2]。
1.2.2 大學醫學教育——阿的西拉模式 阿的西拉模式是中世紀大學醫學教育的基本模式,其方法是按照經典著作進行全面引證[3]。大學醫科學生的基本課程是希波克拉底、蓋倫、阿維森納等權威著作,其組織形式已無從考證;大學課程的內容須同教義和宗教法規對醫學的解釋相吻合;大學教學形式是經院哲學和教條式的灌注形式。大學培養的只是一批動腦不動手,只表明他們的學術水平而不掌握實踐技能的內科醫生。阿的西拉模式嚴重制約了實踐醫學的發展。然而中世紀發生的多次鼠疫和其他傳染病改變了人們對理論醫學和實踐醫學的看法。從事實踐醫學的醫務人員更受到民眾的歡迎,實踐醫學得到了一定發展。
實踐醫學的發展,并不意味著中世紀大學的醫學課程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那種通過評論和辯論式的教學方法沒有根本的改變,即使到文藝復興時期,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教學制度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這就是中世紀醫學教育的基本特點。但是與修道院醫學教育相比,大學醫學教育受經院哲學的影響相對較小,為中世紀的醫學發展與醫學教育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世紀的歐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統治。由于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發展停滯;歐洲文化完全被宗教文化主導;經濟主要是封建制的莊園式自然經濟,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由于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人類對自我的認識還不夠客觀,醫學知識還不夠豐富,醫學教育模式是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水平等的產物。
1.3 機械唯物論醫學教育模式
14—16 世紀,西方出現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三大近代化運動[4],極大地打擊了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宗教的清規戒律,使人們擺脫了教會思想的束縛,以及以神學和經院哲學為基礎的傳統教條。這個時期涌現出了大批科學家,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哈維、培根等。在培根“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觀點影響下,機械學與物理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在17世紀機械唯物論的影響下,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魏爾嘯提出了細胞病理學說。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和醫學知識的豐富勢必影響當時的醫學教育。
馬爾比基(1628—1694)提出了基于實驗哲學的新醫學體系。他竭力主張建立以“基礎研究”為基礎的推理醫學理論體系。在原子論和機械論的影響下,他運用顯微鏡來研究人體的結構和功能,用機械原理來解釋人體疾病的發生和臨床表現的過程,并認為體內化學成分的改變在疾病發生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他通過顯微鏡解剖來研究疾病的部位和原因,并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用化學方法治療人體疾病。到1769年,這種實驗精神終于在斯巴蘭薩尼的努力下,成為推動帕維亞大學醫學教育改革的巨大力量。為培養醫學生的實驗精神,他主張采用一種分階段進行的結構式教學。用這種方法,年輕人就容易認識到觀察精神就是理解事物的能力,找出事物內在的聯系,并把這些事物之間及同其他事物之間相互聯系起來,以便發現某種真理或作出有意義的推論。
機械唯物論醫學教育模式是醫學教育擺脫教會思想的束縛向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的過渡形式。它把醫學教育模式同學生的能力培養結合起來,把醫學教育過程同學生的認知特點結合起來考察,是該模式的進步。把實驗精神注入醫學教育,極大地推動了基礎醫學和醫學教育的發展,然而把生命活動解釋為機械運動,把治療疾病看作“維護機器”是機械唯物論醫學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它忽略了人類機體的生物復雜性,產生了對人體認識的片面性和機械性。
1.4 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
在談到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之前,不能不說用機械原理來解釋機體過程的布爾哈夫(1668—1738)對醫學教育作出的貢獻。他把醫學課程分成3個階段,即基礎科學學習、正常解剖生理學習和病理學與治療學學習,這一醫學教育模式為18世紀以后形成的現代醫學課程模式描繪了藍圖。18世紀和19世紀的兩次科技革命極大推動了包括生物科學在內的科學的發展[5]。生物科學的進步,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理學、細菌學、生物化學、病理學及遺傳學等生物學體系的形成,使人們從生物學的觀點來認識健康與疾病的關系,以生物學為帶頭學科的生物醫學模式逐漸在醫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直接影響醫學領域的各個方面。隨著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深入,醫學知識量的擴增,醫學課程的增加,必須重新設計課程體系才能適應生物醫學模式的要求,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逐漸登上教育舞臺。
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是以學科為單元進行教學安排[4],遵循“先一般后醫學,先基礎后臨床”的循序漸進原則,將整個教學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的醫學教育模式。第一階段為醫前期,設置公共基礎課和普通基礎課,學生基本上不接觸醫學;第二階段為臨床前期,開設醫學基礎課,醫學生開始學習醫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和技能,但不接觸病人;第三階段為臨床期,開設醫學臨床課并進行教學實習,課程結束后,安排一年左右的生產實習[6]。這一教育模式培養了大量從事醫療的專科醫生和從事科研的專家,為19世紀以前嚴重危害人類生命的烈性傳染病的控制、降低嬰兒死亡率、平均期望壽命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
1.5 現代醫學課程綜合化趨勢
由于通識教育登上教壇,人文科技時代到來,科學技術迅速發展,醫學課程門數不斷增加與學制時間有限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當前以學科為基礎的三段式醫學教育模式,各學科界限分明,內容多有重復,基礎課與臨床課截然分開,不利于醫學生早期接觸臨床、早期接觸科研、早期接觸社會。20世紀,特別是50年代以來,由于生物醫學模式的成就,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衛生革命的任務,控制了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性疾病,人類疾病譜和死亡譜發生了很大改變,人們對生命與健康認識發生了變化,現代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出現。
20世紀下半葉,人們開始對醫學教育的全過程進行全面反思。在以器官系統為中心、以問題為中心、以臨床表現為中心的綜合化運動推動下,醫學課程發展呈現綜合化趨勢,但與之相適應的醫學教育模式尚未成熟。
2 醫學教育模式演變的動因分析
通過對醫學教育模式演變過程進行梳理分析,發現兩種因素在醫學教育模式變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是認識的突破,二是社會的需求。
2.1 認識的突破
認識的突破是醫學教育模式轉變的思想源泉。引起認識突破的原因有兩種:一是對人類疾病與健康認識的突破,二是對醫學生認知特點認識的突破。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從認為疾病是天譴神罰到疾病如同機器出現故障和失靈,再到從生物醫學角度認識疾病,從生物學一維角度到生物、心理、社會三維角度考察疾病和健康,人類對疾病與健康的認識由粗淺到精深,由單一到多元,不但引起醫學知識的不斷豐富和發展,而且為醫學教育模式的轉變提供了思想基礎。從經驗教學、分階段教學到綜合化的醫學課程教學演變過程來看,醫學課程體系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再到科學的演變,體現了對醫學生認知特點認識的突破。認識的突破為醫學模式的轉變提供了可能性。
2.2 社會的需求
醫學教育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通過培養的人才、創新的知識、服務社會與社會發生相互作用,它的產生、變化和發展都要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人口等社會因素的制約,社會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潛在的醫學教育模式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對教育模式有選擇和淘汰作用。但醫學教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有其自身的能動作用,對社會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醫學教育必須滿足社會的需求,包括兩層含義:適應社會的發展和促進社會的發展;一定的醫學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滿足社會需求的產物。
醫學教育模式是在醫學教育實踐活動和醫學教育理論發展中形成的,并對醫學教育實踐和醫學教育研究具有指導意義,它實質上是一種醫學教育觀,是人們對客觀存在的事實的主觀反映。沒有認識的突破,不轉變教育觀念,醫學教育就很難發展。當前醫學教育正處于新舊醫學模式轉變、人文素質教育興起、醫學課程發展呈綜合化的關鍵時期,但尚未有一種成熟的醫學教育模式容納當前醫學教育的變化,醫學教育改革的步伐落后于醫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醫學教育改革應轉變醫學教育觀念,解決當前的問題、滿足社會的需求、符合未來的發展,即醫學教育改革應立足當前、面向社會、展望未來。未來醫學教育模式是什么圖景,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有理由相信:未來醫學教育模式會更加滿足社會的需求,更加適應醫學生的認知特點,課程體系更加科學,更能體現人文素質教育的要求。
[1]張拓紅.社會醫學[M].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
[2]朱潮.中外醫學教育史[M].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88.
[3]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M].張大慶,譯.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劉鵬,趙建華,范偉力.醫學綜合發展課程模式的歷史回顧與特征分析[J].西北醫學教育,2006,14(2):158~159.
[5]王渝生.科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N].光明日報,2007-08-02(2).
[6]薛天祥.高等教育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G40
A
1671-1246(2011)21-0005-03
注:本文系廣西醫科大學教育教學改革“十一五”第二批立項項目(2007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