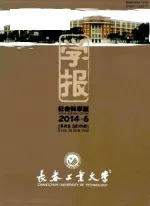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鏡像理論”關照下影像維度的他者認同與自我重構
曾景婷
(江蘇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鎮江212003)
“鏡像理論”關照下影像維度的他者認同與自我重構
曾景婷
(江蘇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鎮江212003)
“鏡像理論”是拉康理論的邏輯起點和歸宿,主要描述“自我”如何在與另外一個完整對象的不斷認同中實現構建。銀幕是嬰兒“鏡子階段”的延伸,觀影時,銀幕內外的“自我”與“他者”不斷沖突造成了主體的異化,最終使觀眾潛藏在深層心理中的無意識得到宣泄與升華。“鏡子階段”是個體完成第一次自我認同和構建的過程,而電影影像的鏡子功能則使個體實現第二次他者認同和自我重構。
鏡像理論;電影;自我;重構
古希臘神話中美少年Narcissus迷戀上了水中自己的倒影,然而倒影的不可碰觸卻又讓他備受折磨,最終抑郁而死,幻化為一株水仙,斜生在岸邊,永遠映照在湖水中。這是早期人類關于鏡像的寫照,表達了人類一種自我審視和自我迷戀的情結。這個神話說明主體能通過對鏡像的觀看來實現對自我的認證,即是一個主體—影像—自我認證的過程。[1](P71)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斷然宣稱電影已成為左右人類文化方向,影響社會現代化進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自電影藝術誕生以來,人類自我確認的方式就和影像結下了不解之緣,電影幾乎和精神分析同時成長,電影文本,鏡頭語言,觀眾潛意識等諸多范疇無疑影響著每一個體的深層心理。銀幕,以鏡子的隱喻身份,潛移默化地操縱著觀眾的心理暗箱;影院里,觀眾觀影時大多都無意識地遵循著形形色色的他者邏輯,或喜、或悲、或哀、或樂,品味另類人生。
一、影像傳媒與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從弗洛伊德到拉康,走過了一條近百年的漫長之路。弗洛伊德認為,夢是人的一種替代性的滿足,夢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它是一種愿望的達成,可以算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而無意識的沖動乃是夢的真正創造者,被壓抑的愿望經過改頭換面后在夢中得到滿足。[2](P90)而拉康則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角度對弗洛伊德進行重新闡述,使我們有可能探討無意識與人類社會的關系。
在經典精神分析家看來,藝術應遵循夢的法則,電影亦是如此,觀眾的觀影就是被壓抑的欲望經過加工改造后得以表達的過程。如果說文學作品營造的白日夢境我們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只能憑借各人所具備的審美能力去體驗,那么電影則使這種夢的具象化成為可能,虛構的電影創作也是欲望的滿足。這符合人的某些本能的需要,譬如生欲和死欲伴隨人的一生,是人生命進程的原始動力。在弗洛伊德看來,生存的本能代表建設性,它根據快樂原則支配人的行為;死亡的本能正好相反,它代表破壞的、毀滅的和進攻的力量。觀眾的安全感和破壞欲只有在觀看驚險動作片時才能同時得到滿足,人生命原動力中這兩種本能欲望隨著轟然倒塌的大廈或是槍林彈雨的戰場而全然釋放。觀眾安坐影院,卻能體驗到日常生活難以給予的巨大心靈震撼,獲得異常或超常的愉悅和快感,最終壓抑的心理能量得到宣泄和升華。
精神分析的引入給電影藝術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路。早期的電影藝術研究總是一味地把眼光投向電影的構成組件如畫面、語言、鏡頭的切換等,而忽視了對觀影主體心理的研究,因此無法解釋電影這門新興的藝術讓無數人如癡如狂的深層原因。隨著電影研究逐步從客體轉向主體,我們有義務把目光投向觀眾的心理層面,自覺地把精神分析法融入到觀影主體審美心理的研究中去。
二、影像維度中的鏡像理論
(一)銀幕前的“鏡像理論”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到過“巖洞映像”。他認為束縛于表象世界之下的人類個體如同置身于黑暗的巖洞之下的囚犯,無法對自己的真實處境有真切全面的了解,只能通過映照在巖洞石壁上的模糊的影像才能得出關于自己的認識。柏拉圖認為,這個洞穴就是我們的世界。[3](P222)雅克·拉康運用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就人的主體問題實現了對傳統精神分析學的一次語言革命。他在1936年提出了“鏡像理論”,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對弗洛伊德主義進行了改造和再闡釋,重新審視了人類認識世界和自我的途徑。
弗洛伊德認為嬰兒在早期還沒有主體與客體、自身與外部世界的界限。這種缺乏任何確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狀態拉康稱之為“想象態”。[1](P73)當嬰兒進入到6到18個月時,已經能夠坐起來,這標記著嬰兒已從完全依賴于別人向自己獨立行動轉化。他雖然還不會說話不會行走,但和外界事物之間的聯系性質已與以前大不相同。這個時期的某一瞬間,嬰兒與別人一起站在鏡子面前時常會發生一種現象:嬰兒偶然從鏡子中辨認出自己的映像,因而變得興奮起來,他會以種種行為表達自己的心情,特別是向自己身旁的大人作出各種姿勢。因為這是兒童首次看到了自己完整的映像,而此前他對于自我與他人的認識只是片段的、零碎的,也是幻想性的,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認同。[4](P90-91)
這就是拉康提出著名的“鏡像階段”,也是拉康理論的邏輯起點和歸宿。鏡像階段是一種前語言階段,嬰兒不能通過象征系統(語言)來理解,但可以通過想象(幻象)的方式來認同。因此,嬰兒與其映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想象的關系,嬰兒的自我是在與另外一個完成對象的認同過程中構建的。一方面,嬰兒通過區分鏡像與自己的身體從鏡子中認出自己,他雖然還不會說話,卻能以不同尋常的面部表情和興奮狀態來表現他對這一發現的喜悅。這一神秘瞬間即為一種自我認證、自我確立的標記。也就是說,“鏡像階段”實際是指自我的結構化,是自己第一次將自身稱為“我”的階段。正如拉康所言“鏡像階段是一出戲文,其內在動力經歷了從不足到期待的劇變,而期待既然耿耿于空間的認同,便為主體制造了那一系列幻影,把支離破碎的身體—形象轉變為他的一個完整的形式”。[5](P4)另一方面,鏡像并非現實,當嬰兒企圖觸摸鏡像時發現它并不存在,因此發生了自我與鏡中之我的對立,鏡中之我既是又不是嬰兒自己,是與“自我”矛盾統一的“他者”。對此,拉康的發現是“欲望確立于與他者欲望的遭遇。它以其主人能指再次指向匱乏,并澄清要求”。[6](P167)主體經過鏡像階段,體驗到只能將自己還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這種對他者的疏離。它將我們導入這樣一種自己與他者不可思議的關系中,即“我”在成為自己本身之際所認同的對手其實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為了成為真正的自己必須舍棄自己本身,而穿上他者的衣裳。因此,主體在自己內部刻上自己和他者這一互相矛盾的本源性裂痕,欲望著他者的欲望。在這一過程完成后,幼兒就從“想象態”轉入拉康所說的“象征性”秩序,即預先確定的社會與性的作用以及構成家庭與社會關系的結構。[1](P73)
(二)他者身份的認同
鏡像階段預示了主體存在的辨證關系,這貫穿了拉康關于主體與他者的相互關系的論述。鏡像不過是嬰兒在接觸社會和進入語言之前的一個虛構自我。“語言與映象本質上并沒有差別,都是思維所借助實現的媒介。通過這一媒介,人所具有的認識形式(logos等)顯現出來,并且空間化了。[7](P65)鏡像階段就像是一幕戲劇,其內部資料應到自身的準備反應尚不完善的不適應性中去開掘,同時也是在對這一完整對象的認同過程中構建,而這個對象是一種想象的投射:人通過發現世界中某一可以認同的客體,來支撐一個虛構的統一的自我感,這種認識將一直影響著主體以后的全部心理發展。事實上,在電影院中什么也不曾發生,只有放映機所制造出的光學幻影,使得觀影者黑暗里或是潸然淚下,或是欣喜若狂。
主體就誕生在鏡子和各種鏡子隱喻中,作為主體基礎的“自我意識”必然是相對于“他者”而存在,而“他者”則是“主體”的投射。也就是說,“主體”在“他者”中看到自身,此為鏡像理論的哲學基礎。電影成為現代生活的認知基地,是人理解世界、發現自我的一面鏡子。形式上,鏡子與銀幕十分相似,它們都有邊框,而且都是在二維平面中體現三維空間,鏡前的嬰兒與銀幕前的觀眾均處于靜止的狀態,凝視著鏡子或銀幕。所不同的是,嬰兒是對鏡中自身鏡像的認同,而觀眾則是對銀幕上自己想象中化身的認同,電影院黑暗的環境更是營造了虛幻的感官世界,恍惚間觀眾如同回到童年鏡前的主體。當觀眾在某種“信仰”的支持下,相信了聲、光、點、影所呈現出的“真實感”,在想象和幻象層面達到了視覺的滿足,那么他們也就正如鏡像階段的嬰兒一樣,完成了“誤認”過程,即把“幻象”當成了真實。將精神分析學引入電影研究的麥茨認為,對電影的理解依賴于認同的過程。當電影觀眾根據影片及其含義來進行自我定位時,鏡像階段的自我反省就變成了電影觀眾的自我意識。因此,電影觀眾的認同實質上是一種他者認同:“每一次我都是在電影中成為自己目光的受撫對象。”[8](P153)
因此,電影產生并迅速被人普遍接受是因為它從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人在童年時期就存在的本質需求。它的運行機制幫助人類找到了擺脫現實的束縛,通過他者回到“主體”的想象空間。不過對于個體而言,由于知識結構、文化傳統、性別以及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已知的世界也有所不同,因而對世界的認知也不同,這也是為什么“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原因。歸根結底人們根據“自我”選擇性地理解電影。
(三)“自我”迷戀與重構
作為視像媒介的電影藝術對觀眾而言具有特殊吸引力,觀影使潛藏在觀眾深層心理中的自戀欲得到宣泄與升華。從根本上講,觀眾對電影的迷戀已不再是簡單地針對某類影片、某個人物,而是對不斷滿足自己欲望的觀影過程的迷戀。這種迷戀有著十分復雜的心理根源,人對視像的喜愛源于人格形成的早期階段嬰兒第一次見到鏡子時拼命靠近的舉動,嬰兒有渴求清楚地看到鏡中自己影像的欲望,而動物則采取逃避。這種自戀情結存在于人類的深層心理空間,他們不滿足在普通鏡子前的“自我”欣賞,可現實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又約束了這種情結的釋放,這樣一來觀影活動就在當下現實的安全時空中彌補了這種缺憾。我們之前分析了鏡前嬰兒所面對的情境與電影觀眾所處的情境有驚人的相似。正是這種相似驅動了把人帶回童年早期回憶的可能,從而滿足人類某些被壓抑的情感。
但是,鏡像畢竟不是現實,拉康所說的鏡像關系依然是一種想象關系,鏡中之我既是又不是嬰兒自己,當嬰兒企圖觸摸鏡像時發現他并不存在,因此發生了自我與鏡中之我的對立,拉康稱之為“自我的異化”。我們觀察一下就能發現觀眾眼前所見之景也有著和夢一樣的特質——虛幻、迷離。銀幕上上演的悲歡離合、人性的苦苦掙扎、善良與邪惡的沖突都隱喻著人內心深處潛藏的種種秘密。較之其它的藝術形式,電影提供了人與現實分隔而直接與夢幻相聯系的特殊環境,使觀眾真正成為白日夢的實踐者或者說使觀眾能夠欣賞自己的白日夢。因此,做夢和觀影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本我”在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后,沖破了“自我”和“超我”的桎梏而得到滿足。這種滿足不必冒犯罪、亂倫等譴責,它在社會文化、習俗、法律、倫理認可的前提下得以實現,能真真切切地充分觸及現實生活中不可能也不能觸及的東西,在作者創作的這面“鏡子”中讀者看到了“我”的人的本質和“我”的社會本質。[9](P6)做夢和觀影雖為兩種不同行為,但在心理層面上卻同為人的無意識在不同空間的安全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拉康最初將鏡像階段視為幼兒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但后來拉康認為不僅如此,它還表現了永恒的主體性結構,也就是說,鏡像階段展示了主體形成的過程:“自我”和“他者”的沖突造成了主體的異化,鏡像階段的主體是通過想象的認同完成的。當下傳播語境中的影院就是拉康“最初鏡子”的延伸,觀影者借助“觀看——認同”模式,通過銀幕完成了自身完滿性的幻覺:或是道德的完美,或是各種能力的完善。各種“影院暗箱”的要求催生了電影業的蓬勃發展,而觀眾的“自我”構建正是在這種與影像中理想形象的認同中產生。正如弗洛伊德的“自戀的自我”一樣,“自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主體與自身之鏡像認同的“自戀的激情”的產物。電影觀眾的位置是被當作一種“空虛的空間”而制造出來的,正如拉康認為,嬰兒在經歷過“鏡像階段”之后,一個真實的自我從此便不再存在,人類本身其實只是一個被“他者”侵占和控制的傀儡。[10]不過影像并不是簡單的他者,它形成了自我,觀影是又一次觀鏡行為,是又一次幻象活動,是在一個“不可能存在之真”的世界里對自我身份進行再次認定和重構。
三、結語
總之,電影不僅通過生動的影像滿足主體的本能欲望,而且更直接、更深入地進入人類深藏的無意識深淵。作為觀影的“主體”是在對另一個完整對象的認同過程中構建的,而這一對象是一種想象的投射,人通過發現世界某一可認同之客體來支撐一個虛構的“自我”。因此,影像認同中“自我”得以形成的“主體”屬一種誤認,也就是說,主體是在把自己視為某種實際上并非自己的東西。那么,由“誤認”產生的“自我”就是主體的異化幻象。這正是“影院暗箱”對人類自我之虛幻性質的揭示。電影作為一種普遍接受的媒介影像通過“鏡子”功能,把一個五彩斑斕的幻象世界展示給觀眾,而觀眾則籍此重溫“鏡子階段”,完成社會個體的第二次自我認同和重構。
[1]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奧〕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賴其萬,符傳孝,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6.
[3]〔古希〕柏拉圖.理想國[M].段至誠,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
[4]〔法〕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
[5]Lacan.J.Ecrits:A Selection[M].New York:Tavistock,1977.
[6]〔法〕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上卷[M].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7]方漢文.后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2000.
[8]〔法〕克里斯蒂安·麥茨,吉爾·德勒茲.凝視的快感——電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吳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9]金元浦.影視藝術鑒[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10]崔露什,從拉康的鏡像理論看電影及其他媒介影像的鏡子功能[J].社會科學論壇,2009,(2).
曾景婷(1979-),女,碩士,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學、文藝理論、英語教學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