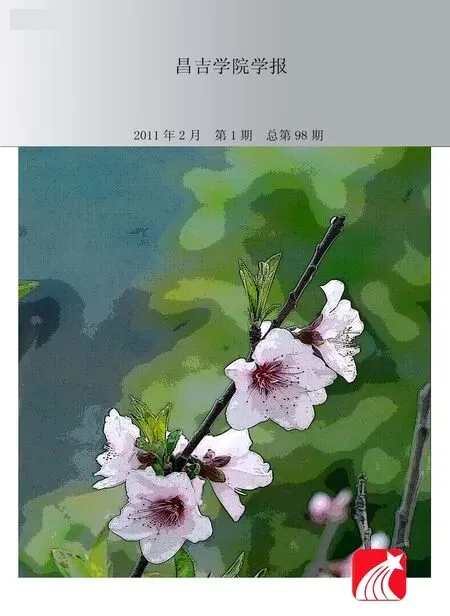交際范式構念下英語“新語法觀”的理論接口及實踐探索
毛懷周
(昌吉學院外語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1 引言
英語語法教學來源于古典法,之后語法翻譯法在英語教學中方興未艾,(普拉托爾和 Celce -穆爾西亞,1979:3)[1]直到海姆斯 (1972) 提出“交際能力”學說后,語言教師逐漸從重視語言形式的誤區中走出來,關注語言形式和能力相結合的教學模式。[2]斯凱恩 (1998) 和弗里曼(2002:148) 分別提出了語言能力的“三要素”和“新語法觀”的動態模式-語法教學技能 (Grammaring)。[3]有的學者認為 (哈默,1983; 利特爾伍德, 1990), 重要的是在傳統和現代教學模式之間構建一座橋梁, 提高和改善英語語言教師和學習者在課堂上交際能力和交際教學法觀念上的認識,[4]因為“語法能力”是學習者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使語法知識學習為交際服務成為一項新的課題。
本文的論述重點在于如何有效地實施交際范式構念下的英語“新語法觀”教學模式,如何在英語語法技能教學中增強積極主動的投入感,幫助語言教師提高學習者的英語應用能力,從而逐步改善傳統英語語法翻譯法教學的觀念,構建交際范式構念下的英語“新語法觀”教學模式,提高大學英語語法技能教學水平和質量,對大學英語語法技能教學的教學大綱設置具有指導作用。
2 語法技能教學研究
長期以來,英語教學的焦點是如何正確地講授語法知識,而很少關注語言(語法)知識的使用程度。傳統的語法翻譯法只強調語言知識規則的使用形式。自海姆斯 (1979) 提出了交際能力以來,語言教學的核心大為改觀,轉向關注語言的使用和交際能力。卡納爾和斯維恩 (1980)[5]對海姆斯的交際能力進行了系統的完善,但沒有把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斯凱恩認為 (1997),只有達到語言的準確性、流利性和復雜性才能反映能力的增長,也說明了有效使用語言的能力。不過要使兩者統合,在語言教學中卻有一定的難度。弗里曼 (2002: 48) 基于對懷特里德語言“惰性知識” 的“完型” (Gestalt) 提出了“新語法觀”(Grammaring)。[6]認為只有在語言形式和意義之間形成一個動態的模式,才能實現“語法技能教學”模式,才能實現語言的語用使用,進而形成語言教學從形式走向意義,從意義走向語言使用的動態循環三階段。但英語教師認為,語法技能和交際教學屬于兩個不同的緯度,因為語法技能教學是機械記憶訓練的結果。而交際語言教學是四種技能有意義的動態的理解,是為實現一種目的而建立的交互的伙伴關系。由此,語法技能教學和交際范式語言教學始終沒能建立起溝通兩者之間的橋梁。
我國的語法技能教學由來已久,在基礎教育階段長期占有主導地位。20世紀70年,交際語言教學和交際范式教學才被引進,但由于中國教學狀況和師資的問題,面對如此之多的班級規模,出現了對交際語言教學的顧慮和偏誤。有人認為交際語言教學就是不教語法,只教口語,還有人認為是對子練習和角色表演……(湯普森,1996: 9-15)[7]于是出現了英語教學“穿新鞋走老路”典型的漢語式英語課堂教學。另外,吳旭東 (2002 /12: 143-162) 在中國以漢語為主的英語教師的案例研究中表明,盡管受試都同意理查德和羅杰斯 (1986) 的“交際語言教學‘范式’”原則,但在課堂練習上用時較多,受試反映表明對學習者的交際需要忽視較為廣泛。[8]
3 交際教學研究
國外“新語法觀”技能教學主要經歷了直接法、口語情景法、聽說法、交際教學模式的歷史發展過程。直接法 (理查德和羅杰斯, 2000: 9-10) 是基于戈恩“系列法” 的基本命題,認為在交際范式語言教學中須大量的口頭交互和即時地使用目的語教學。這種方法排斥在L1和L2之間的語法教學翻譯及對語法規則的解釋和分析。雖然“直接法”在理解言語和聽力中使用了口頭交際技能和語法知識,但沒有排除語法教學,因為語法技能教學在“直接法”教學中關注的是語言的背景意義。帕爾馬 和Horby(引自束定芳,莊智象,2004)的“口語情景教學法”是基于S-R理論形成的一種口語領先,讀寫跟后的語言教學模式。是語言詞匯和語法項目的學習/習得,是經情景達到語言的口頭交際的非交互意義過程。[9]聽說法是弗萊斯和拉多 (1945) 在二戰期間建立的為培養軍隊所需的“語言島”而創立的,認為語言形式比語言意義更為重要。語言學家的任務是描述復雜語言的有限因素和歸納語言的有限句型結構。[10]正如普拉托爾和 Celce-穆爾西亞 (1979) 指出,“聽說法” 就是以對話的形式呈現新的語言材料,重復地傳授語言結構句型……作者認為直接法、口語法和聽說法似乎忽略了學習者的認知能力,從而使學習者對語言的創生受到了影響。這些方法把語言教學看作一種機械的重復和記憶,缺乏應有的自然語言交際的環境。要具備語言交際的自然環境,必須探究學習者的交際能力,并能使其在交際范式教學中得到應用。
海姆斯 (1979) 基于喬姆斯基 (1965) 的語法知識能力, 認為交際能力理應成為語言能力的一部分,因為交際能力不僅包括為形成語法性正確的句子能力,也包括語言的可行性、適合性、表達性和現實性。卡納爾和斯維溫 (1980) 的交際能力包括語法能力、社會語用能力、篇章能力和策略能力。交際能力強調話語發生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語言教師應反思如何在不同的情景中講授同樣的語言知識,而這種語言知識又能表達所要陳述的同樣的語言功能。交際能力對語言教師的影響是,在意義背景中的句型練習是有效和可行的,但不利于學習者交際能力的培養。許多語言學家和教師試圖找到把語言知識和交際能力結合起來的方法,因為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這樣,使交際范式下語法技能教學在理論上成為可能。
要理解交際能力在教學中的應用,須考慮在語言教學中如何處理英語語言教學中“用語言學習”的“強模式”和“學會用語言”的“弱模式”, (威爾金斯, 1976)[11]而后者更適合中國語言的英語教學, 但都應遵循語言教學的序列性。為此,利特爾伍德(1981) 對交際語言教學中的交際性序列做出如下兩個緯度的區分:前交際活動(Structural and Quasi-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 和交際活動 (Function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它們應遵循相互關聯的兩個策略 (1)語言教師把具體的語言成份分離后構成交際活動內容并提供給學習者練習的機會;(2)學習者需激活這些知識并與這些知識進行有意義交際。但哈默(1983)在語言課堂交際活動中認為,交際教學應形成一種循環的連續體-從非交際性過渡到交際性活動過程。這兩個連續體還需包括五種交際語言教學中的基本特征。(如愿望和目的等);利特爾伍德和哈默的交際過程和序列法有共同之處,可劃分為交際語言教學范式的三階段,即呈現、練習和生成, 使語言教師保證交際語言課堂活動的執行。可以看出,在交際范式英語語言教學的歷史中,其理論研究并未排斥語法教學,而是對英語語法技能教學的重釋和意義的擴展。
具體來說,國外主要采用CPDC模式即以“交際-語言呈現-句型操練-交際”(哈默, 1983) 為主,是對“呈現-練習-背景練習”(Brumfit,1978)的修正;[12]IPP模式由信息差-交際目的感-開放性活動三成分和PR模式-“表達-排練-報告”。(引自黃遠振, 2003: 112-114)[13]
國內“新語法觀”技能教學主要經歷了由“呈現-師生討論-演繹總結-鞏固-理解性應用”、 “呈現、討論、分析、實際應用-觀察、假設、驗證-口頭、理解性練習”到“呈現-練習-遷移”的三個演變過程。黃遠振 (2003) 指出,交際范式下的語法技能教學應以四階段為主,即“呈現-師生討論-演繹總結-鞏固和理解性應用”。趙梅娟 (1999)認為三階段較符合中國教學實際-“呈現-討論和分析-實際應用”。[14]張振東 (2001) 提倡交際范式下的語法技能教學以“呈現-練習-遷移”三階段為主,認為新課程英語語法技能編排以分散而非集中為主,這樣第一階段應以語言材料如課文和對話為主;第二階段以獲取語法項目和規則為主;第三階段以語言的遷移如用說和寫作的活動來表達學習者的思想情感,以達到把學到的語言知識遷移到真實的交際背景之中,最后實現英語語言知識的可教性和可學性的理想的語言學習結果。
4 交際范式構念下語法技能教學新理念
基于對 “新語法觀” 語法教學技能、交際教學研究的抽象化,特別是利特爾伍德(1981) 的交際教學序列性和哈默 (1983) 的交際教學循環連續體原則,本文作者提出以下交際范式構念下英語語法技能教學模式,如圖-1:

從宏觀看SCNQA模式需經歷創設交際環境到交際策略培訓橋接,在此建構下,學習者關注語言的基本形式、基本意義和意義背景。非交際活動隸屬于語言的基本形式,準交際活動隸屬語言的基本意義,而真實交際活動隸屬語言的背景意義,由此構成三維交際范式下的英語語法技能教學的基本框架,而交際環境和交際策略培訓必須貫穿整個語言學習的始終,它是構建交際范式,貫徹英語語法技能教學的核心。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語言形式轉化為語言意義,以動態而非靜止的過程模式,使交際范式構念下“新語法觀”的語法技能教學模式成為一種最佳途徑。
5 啟示
縱觀語法和交際教學的今昔,各學派關注的焦點是:語法教學的重點是形式還是意義,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如何把一對矛盾體結合起來,雖然像海姆斯等人對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都有論述,但均未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交際范式下的語法技能教學模式。以交際范式下的“新語法教學觀”為理念,使大學英語語法技能教學策略模式交際化并運用到英語教學勢在必行。
重要的是在傳統教學方法(英語語法教學)和現代教學方法(交際范式語法技能教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提高英語語言工作者對交際能力和交際范式下語法技能教學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學習者在一定語境下習得(學習)一門語法知識和語言的應變能力,并為如何在英語教學中整合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能力提供相關的數據,從而對大學英語課程大綱的設置和英語語法教學施加一定的影響,實現交際范式下英語語法技能教學模式的理論和實踐結合。
參考文獻:
[1]Brumfit, C.Review of Wilkins' Notional Syllabus” [J]. ELT Journal. 1978, (34):79-82.
[2]Canale & Swain.“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nd teaching”[J].Applied Linguistics.1980,(1):1-47.
[3]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Boston: MIT Press.1965.
[4]Harmer.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London:Longman. 1983.
[5]Hymes.“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In Pride,K.B & Holmes,J.(eds). Sociolinguistics.London:Penguin.1979:5-26.
[6]Freeman, D.L.Teaching Language: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148.
[7]Littlewood.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M].Beijing:People’s Education Pres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8,15,85.
[8]Richards,J.C & Platt & Platt.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9]Skehan,P & P. Foster.“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post-task activities on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in task-based Learning”[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997,(1):3.
[10]Thompson, Geoff.“Some misconceptions about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J].ELT Journal. 1996,(50):9-24.
[11]Wilkins,D.A.Notional Syllabuse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3.
[12]束定芳, 莊智象.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112.
[13]黃遠振.新課程英語教與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112-114.
[14]張振東.教學理論與流派[M].北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