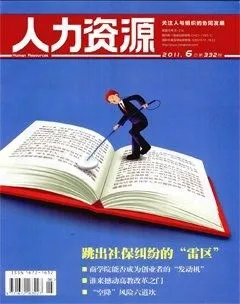“行業最低工資”不能止步于好看
“十二五”期間如何實現國民收入翻番的預期目標?來自有關部門的聲音是主要通過市場調節,隨之從武漢方面傳出餐飲業工資集體協商成功的消息,使人們很受鼓舞,有人認為這是實現國民收入翻番的重要途徑或者基本途徑。然而,如果我們僅僅聚焦于其中行業最低工資的博弈,使得工資集體協商陷入最低工資協商的誤區,按照其博弈結果推演至“十二五”結束,低收入者將很難走出“被增長”的尷尬。如此增幅難以實現“五年翻番”計劃
工資集體協商并非武漢餐飲業首創,2000年《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以勞動部第9號令發布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歷史。也并非武漢餐飲業的工資集體協商最成功,如沈陽市工會通過組織探索工資集體協商形式,使工資集體合同反映地區行業經濟特色,總結出“街道式”、“社區式”、行業性、“工業園區式”、“樓宇式”、“商業一條街式”、“大市場式”和“工地式”集體合同等8種協商形式,在沈陽市非公企業中推行,維護了企業職工的權益。2008年7月,全國總工會調研組還對沈陽市總工會推行餐飲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給予了肯定。武漢市餐飲行業勞資雙方的代表在今年4月23日就簽訂了合同,之所以“五一”節過后才被關注,顯然有媒體的助推。然而,在其最低工資標準上調30%好看的背后,工資增幅不低于9%的效果堪憂。
按照國民收入翻番的政策設計,“十二五”期間需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的目標:而在武漢餐飲業的集體協商結果中,2011年餐飲業職工的工資增幅只能承諾實現9%。按照《武漢市“十二五”規劃綱要(框架)》的要求,未來五年,居民收入增幅也要保持在每年10名以上。上述9%的承諾顯然低于政策設計的指標。而且在當前收入分配差距超過基尼系數的情況下,為了縮小差距,應當加大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增長力度才能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訴求。而武漢餐飲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在所有行業中是最低的,按照最低工資標準上調30%后,還不到2009年武漢市人均工資2400元的一半。即使按照上述9%的承諾增加工資,到“十二五”期末,社會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的增長不僅得不到控制,反而會進一步加大。
即便如此,武漢餐飲業的集體協商結果能不能產生應有的約束力,仍然是個未知數。這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規模較大的企業基本起不到指導作用。所謂按照最低工資標準上調30%,是一個均值,規模較大企業的工資水平大多數超過了這個標準,所屬員工從這個協商結果中看不到對自己收入的提高有什么樣的促進作用。另一種是對規模較小、效益難有保障的企業來說,基本看不到全面落實的前景。不少餐館業主表示,執行合同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太難,今年再漲9%有難度。也就是說,上浮后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也只是在975元到1170元之間,最低工資上調有可能遭遇“天花板”。有些飯店服務員得知集體協商合同的內容后,雖然心里對工資標準有了底,但是對今年再加薪不抱希望。因為他們對自己能夠工作多久,心里一直沒有底。
由此可以看出,公眾對工資集體協商寄予的厚望與它目前所實際起到的作用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當然,對此抱樂觀態度的人可以解釋說,作為一種談判,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通過新一輪的談判逐步逼近比較理想的狀態。但是武漢餐飲業的集體協商的過程告訴我們,達到目前的協商結果已非常不容易。此輪協商從3年前就開始醞釀,中途屢屢被擱置。雖然從第一次正式協商到集體合同文本簽訂,時間不到50天,三輪談判大大小小的協調會也開了上百次。為了這50天,有關助推者準備了整整兩年。按照這個速率啟動新一輪的協商,“十二五”規劃的執行期限至少將過半。可見,如果按照目前武漢餐飲業的集體協商的狀態,難以完成它理應擔負起的歷史使命。
最低工資的博弈沒有贏家
在收入倍增計劃有可能被“看空”的情況下,武漢餐飲行業的協商成果無疑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但是,即使對此叫好的人也認為,經武漢餐飲行業勞資雙方妥協后的工薪標準不高。那么,人為地將工薪標準定得很高是不是就好呢?恐怕未必。寫在紙面上的東西固然可以有贏家,但是在實踐中同樣會產生負面作用。香港最低工資法例從5月1日生效只有一個多星期,就有議員因負面作用凸顯呼吁“叫停”。
香港立法會5月11日就暫緩執行《最低工資條例》的議案進行辯論,其動因就是鑒于多個行業勞資雙方均對《最低工資條例》有異議。香港政府所公布的一般性指引,及專為多個最受該條例影響的行業制訂的特別指引,仍未能消除大眾疑慮。而贊成《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議員近日也被質疑沒有仔細審議有關條例草案,以及低估條例將產生的負面影響。所謂負面影響,就是因為該法案所定最低工資28元的時薪標準過高,隨時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導致面對租金急升及通脹的壓力而資金捉襟見肘的中小企業不堪重負。即使企業條件較好的雇主,也會傾向聘請相對年輕及經驗豐富的員工,一些年老工人和缺乏工作經驗的應屆畢業生可能被擠出勞工市場。盡管這項動議被否,也引起了政府在監管方面的高度重視。
其實,在武漢餐飲行業的協商過程中已經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而雇主之所以能夠接受行業協會的建議,主要是迫于“用工荒”,旺季時缺工達15%:再加上上浮30%的最低工資的標準本身也不高,而且效力主要在當前,至于到年底能不能兌現增加工資的承諾,主動權還是完全在雇主這一邊。這就足以看出,為什么一提到集體協商就圍繞著最低工資進行博弈,那實在有避實就虛之嫌。以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為基礎的協商,由于起點低,比較容易達成形式上的妥協,看上去好看。但是,正如武漢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席朱毅所說,協商不易,落實更難。如果當地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餐飲行業的協商結果要么沒有實際意義,要么需要進行新的一輪協商。
一般說來,工資集體協商從薄弱環節獲得突破沒有錯。但是在“十二五”期間,既要實現國民收入翻番,又要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正。有雙重指標的約束,圍繞著最低工資的博弈,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低收入群體的弱勢地位。從“調薪主要靠市場”,到工資集體協商,再到最低工資的博弈,這顯然不是完成“十二五”計劃的攻堅路徑。從理論上講,在市場化訴求與勞動價值規律相背離的情況下,按照“調薪主要靠市場”的導向亦有失偏頗。如果說在“十二五”期間不可能每個人工資都翻一番,那么主要應當控制高收入群體的工資增長,而不應當成為低收入群體工資增長滯后的理由,不能僅僅糾纏于最低工資妥協的低層次博弈。就武漢餐飲行業集體協商個案而言,不能在已經達成的協議前止步。超越行業最低工資博弈的對策
應當承認,按照“調薪主要靠市場”的導向,弱勢群體的收入增長往往找不到抓手。工資集體協商作為一種國際慣例被各方關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工資集體協商必須防止蛻化為行業最低工資的妥協:不斷超越現有的談判水平,采取如下的一些對策是必要的:
首先,上級工會組織在工資集體協商中應當更加務實,敢于碰硬。這里所說的務實,除了在工資集體協商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還可以適當介入勞動力使用的過程,比如將政府部門人力資源或人才資源管理的職能部分轉移給工會:工會可以擔負勞務派遣的職能,以防止部分用人單位規避法律風險,導致員工“被派遣”的弊端蔓延。所謂敢于碰硬,是要敢于和處于強勢的雇主直接談判。在武漢餐飲行業的協商中,工會組織選擇的是一個較弱的談判對手——行業協會,盡管形成了相對優勢,卻為協商結果的落實增加了變數。至少那些沒有加入行業協會的餐飲企業,行業協會管不著i即使是行業協會的成員,也可以退出行業協會。
其次,可以考慮像選派大學生駐村干部那樣,向企業派送大學生工會干部。這是因為,企業里雖然必須依法成立工會,但是工會負責人拿的是所在企業的工資,為職工說話就受到牽制。而向企業派送大學生工會干部,就有助于割斷這種利益羈絆。大學生工會干部可以由所屬地區或者系統工會派出,參照“大學生村官”的待遇執行,以便在進行包括工資集體協商在內的工會工作時保持公正和可信度。大學生工會干部在推動或者代表勞動者與雇主進行工資集體協商時,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比如形成“同級工會主動要約一上級工會提出整改建議一勞動部門依法追究”的工作鏈。
再次,在上述基礎上,致力于將行業性的談判延伸到具體企業的實際當中。可以根據具體企業的贏利模式進行成本核算,核定合理的勞動力價值。比如上海市普陀區紡織工會從2009年開始,就在企業層面探索“一品一測一協商”的制度。即企業每生產一個紡織品種(每個訂單號),企業工會就進行一次現場測試,同時開展一次工資集體協商,以此確定企業生產加工品種的勞動定額和工時工價標準。通過對6家大中型紡織企業總計10個生產加工品種的工時工價勞動定額標準進行現場測試和協商,提高了174道工序的工價定額標準,有效幫助職工實現了收入的合理增長。
另外,有必要進行落實國民收入翻番計劃與縮小收入差距的頂層設計,努力把好事做得更好。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比較糾結的主要涉及低技能、低付出、低產出的人群與業主,政府可以從擴大就業的角度給予必要的扶持,對低技能、低付出、低產出的人群進行培訓,為充分就業創造條件。還需要對工資集體協商在不同層次上達成的協議給予必要的法律支撐,比如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實施最低工資的11天中,就進行了千余次勞工督察巡查,發現15宗個案涉及薪金低于最低工資,收到1宗投訴后,就實時跟進,及時消除了更多的混亂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