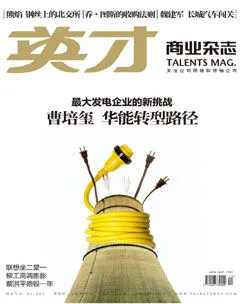中信建設海外造城
2011-12-31 00:00:00嚴睿和陽
英才 2011年12期

自非洲某國時局動蕩以來,十幾家大型中國基建企業的多個承包項目命運多舛,或是重型設備被搶,或是成了前線的掩體。2011年10月初,這些合同總值據估超過100億美元的中國企業的項目工地上,仍散落著彈藥。
突如奇來的政局變化或許沒人能猜到,不過位列中國第七大國際承包商的中信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信建設)卻未出現在基建企業的名單當中。中信建設近年95%以上的營業額來自海外,絕大部分員工及資產也位于海外,為何在中國企業扎堆該國,偏偏中信建設沒有染指任何項目?
一位業內人士向《英才》記者透露:中信建設前期調查時發現該國有惡意拖欠工程款項的不良記錄,遂未進入。
除了規避海外市場各種風險外,怎么掙錢,是讓中國基建企業集體頭疼的另一個關鍵性問題。在近10年內,中國基建企業的國際市場營業額從約54億美元增至約506億美元,但凈利潤率卻依然在2%左右徘徊(數據來自魯班咨詢),甚至部分企業還遭遇數十億元的巨虧。
中信建設也畫出了一段類似的海外市場營收增長曲線,但結果不同。接受《英才》記者專訪時,中信集團董事、中信建設董事長洪波表示,2003年時中信建設的海外業務幾乎為零,此后公司接連拿下4.28億美元、9.42億歐元、62.5億美元等多筆打破同類海外項目合同金額的訂單。
與此同時,“我們能保證每年較高的凈利率”,中信建設總經理袁紹斌告訴《英才》記者,中信建設是“有利可圖且不唯利是圖”。
這家在基建同行中并不具備規模體量優勢的公司,把自己的主要競爭市場擺在了海外,卻能持續的開疆拓土,并展現出令同業側目的創利效率和風控能力,中信建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造城”模式
“創造市場”,中信建設不但用這四個字撬開了海外市場,所拿下的合同金額也越來越大。
2011年安哥拉凱蘭巴·凱亞西(Kilamba Kiaxi下稱K.K.),不時有周邊國家領導人來到中信建設位于此地的住房工程K.K.項目參觀。安哥拉處于戰亂后的重建期,遍地都是住房工程,他們來K.K.看什么?一位政府要員有過“回答”:該項目是安哥拉其他房建項目的樣板。
所謂的樣板工程,在安哥拉百姓看來,等于房屋+自來水管道、電廠等生活設施,盡管如此,“來看房買房的人山人海將每個出入口都堵死了”目睹了第一現場的袁紹斌告訴《英才》記者,安哥拉是一個工業基礎薄弱到需要進口螺絲釘的國家,這導致基建企業在安哥拉市場上承建的不少工程缺少配套設施。
為單一項目策劃、籌建配套設施,無中生有的獲取訂單、創造訂單。這實際上是董事長洪波針對非洲國家的市場需求,制訂了一套“創造市場”的經營戰略。
洪波四年前曾告訴安哥拉重建委主席,中信建設將向安哥拉額外提供水泥磨粉廠、磚廠等十余項目,而且運轉一定時間后它們將轉贈給安哥拉。安哥拉有關方面隨即給予中信建設“不僅僅是在做項目,還擁有社會責任感”的評價。
同一年,在安哥拉耕耘超過25年的巴西最大建筑企業Odebrecht失手K.K.一期項目。中信建設卻以高出Odebrecht 5億多美元的最高報價(35.35億美元)拿下了目前中國海外合同額最大的這一住房項目。
為住宅區提供配套設施,在洪波看來,還不是“創造市場”的全部內涵。2011年5月,中信建設設計聯合體與安哥拉羅安達省政府簽訂了《安哥拉羅安達省K.K.市與BELAS市城際規劃服務合同》,“中信建設與安哥拉國家的合作實現了又一跨越。”
現在這份市際規劃合同則意味著中信建設的施展空間正式升格至城市級別——把K.K.項目變成K.K.市。據袁紹斌透露,僅K.K.項目三期合同總額就有約150億美元。
袁紹斌說“我們為業主國提供國家級配套服務”顯然正是中信建設屢屢拿下大單的殺手锏。
資源調配者
“如果還在國內,再大本事我也做不出較高的凈利率。因為,競爭太激烈了。”中信建設的海外營收占比逐年增加,目前已到95%以上的高位,洪波認為,出海是中信建設擁有高凈利的一大原因。
但拿下海外市場的高價大單,只是中信建設能盈利的基礎。如果有數萬、數十萬員工加以稀釋,中信建設很難獲得兩位數的凈利率,尤其是在國際勞務輸出市場上中國工人的月薪已經漲至1000-1500美元的當下,很多中國基建企業喪失了過去倚重的勞動力成本優勢。
這似乎并未帶給中信建設太大的沖擊。K.K工地上的1萬余名中國工人并非中信建設的員工,他們是中信承建聯合體即中國鐵建、中國中鐵等公司的員工。所以袁紹斌感慨埃及勞工的月薪之便宜時(200美元)說,“我們爭取還是讓合作伙伴一塊兒走出去,不過中國企業逐步使用其他勞動力資源,這樣可能會有好處。”
不光只有承建聯合體。歷次海外項目中,以中信建設為核心,洪波聯合了國內諸合作伙伴形成了中信農業聯合體、中信設計聯合體等公司,組成了“獨特的聯合艦隊集群”。
中信建設企業文化總監李才元向《英才》記者著重強調了艦隊里的共贏關系,“這并非簡單的總包與分包關系,我們是兄弟連,參與我們的項目時他們也獲取了比同類項目高得多的利潤”。
雖然中信建設未就此向《英才》記者提供具體數據,但從產業鏈角度來看中信建設,與傳統基建企業相比,中信建設本身并不以勞動力為競爭優勢、以施工承包為主要業務,而在項目管理、設計、采購、運維、融資等高附加值環節進行突破。“國內沒人能為業主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一條龍服務,那就讓我們來。”
中信建設試圖以資源調配者的身份進階為EPC(Engineer,Procure,Construct)廠商。洪波對《英才》記者回憶,此前制約中信建設走傳統重資產化發展道路的人力稀少,這反而成為中信建設的主要優勢之一。
“其實建筑企業都知道怎么轉型,怎么發展,但從底部蹦到最高,下面的幾十萬員工怎么安排?”洪波說。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中信建設的在編員工數也不到800人。
現在,洪波希望在核心產業環節的薄弱之處通過并購來補強中信建設。比如針對設計短板,“適當的時候,我們會收購中國一些比較有實力的設計院,再通過中信建設的國際大項目持續完善EPC的綜合能力。”
為確保資源的聚焦,袁紹斌說中信建設現在只承接合同額超過5億美元的項目,“我們人數太少,分散在太多項目上會降低工程質量。一兩億美元的項目如果還散在好幾個國家里頭,我們沒有興趣。”
如何挑選海外市場?基于種種因素,眼下中資基建企業幾乎沒有進入歐美日等國市場的可能,只剩下了不確定性風險較大的亞非拉國家。
洪波最常去的國家是安哥拉、委內瑞拉,實際上,中信建設目前約60%的業務是來自這兩個國家。洪波認為,應首看業主國與中國的戰略互動級別。
追逐國家戰略并非意味著依靠中國政府,“很多中國公司都競爭有些國家援助性質的中國貸款工程,我們不是。我們會幫助客戶融資,但是市場化的。”袁紹斌對《英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