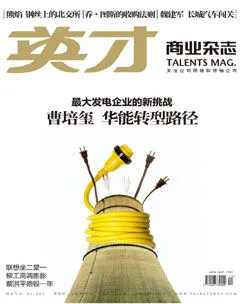當革命成為符號
2011-12-31 00:00:00王雨佳
英才 2011年12期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作為最接近“2012年世界末日”的年份,從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到歐洲的希臘、西班牙、冰島,甚至全球經濟中心美國,“革命”好像成了2011年的主流。
先是在美國,憲法日后開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持續到第19天,“活著就為了改變世界”的蘋果公司C E O史蒂夫·喬布斯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因他的死引發的對創新、革命的思考瞬時間席卷了全球。
15天后,縱橫多年的非洲“梟雄”卡扎菲死在了“革命”的槍口之下。
在中國,情況迥然不同。對100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的紀念,正散發出一種相反的氣息——“告別革命”。
“文人、知識分子只會唱矯揉做作的小調,中國的民國史熱,就是小調的大合唱”,作家余世存如是說。
的確,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遠離革命,卻又如此貼近革命。在“革命”二字漸成符號的年代,革命卻又在方方面面真實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當代中國人還需要革命精神嗎?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在這個安逸的年代,中國人似乎正在告別革命。
革命與改良
主持人:革命和改良,分別意味著什么?
吳曉波:革命是對舊有秩序的顛覆。而改良是漸進式的演變。過程中,舊有秩序的基因是沒有變化。
何剛:革命是短促而激烈的,是短時間內的一種質變。而改良是漫長的,是修修補補,是需要更長時間的一種量變。
其實,對于革命的概念,中西方是不同的。中國歷史上最初的革命是湯武滅夏桀。那時候強調的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將改朝換代歸結為天命所歸,民意所向。所以,革命在中國有特定的含義,叫做順天而為。即順乎潮流最重要,是否激烈,是否暴力,都不重要。
改良有狹義、廣義之分。從中國歷史改變的艱難程度來看,改革本身就是某種程度的革命,只不過我們通常把改革和改良看作一個朝代內的變化。比如商鞅,他的變法就是改良。改良不主張以短時間內劇烈變化的方式來推動社會的變化。
高翔:在英文中,革命和改良是兩個很近的詞。革命是revaluation,改良是evaluation。就差一個“R”,但意思完全不一樣。比如說,科技進步每一秒都在發生,但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顛覆性的就那么幾個。
兩者最顯著的區別是:首先,革命一定要影響很多人,比如蒸汽機的發明、電的發明。第二,革命性的東西,改變的是人們的觀念和意識。很多時候,引導革命的人,不是去迎合潮流,而是超越潮流,甚至敢于和潮流叫板。其三,革命對人們的影響是長時間的,是有深度的。其四,革命要對歷史有正面的推動。像毒品的出現,不是革命,而是禍害。
主持人:革命和改良,哪個更有效?
何剛: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從來不拒絕革命,甚至某種程度上對革命有一種狂熱,但現實常態反而是改良更多。
其實,從商鞅遭受“車裂”到戊戌六君子為變法犧牲,改良的斗爭激烈程度上大于革命。要知道,革命有明確的陣營,兩派刀兵相見,死傷的多是一線參與者,也就是所謂的公眾、軍隊,全是些自愿付出者和無辜者。但指揮者一般不會受傷害,甚至可以全身而退。
從結果看,革命的結果是零和。什么是零和?比如有一塊餅,原來兩派是五五分,革命之后變為四六分,這種沖突是沒有真正價值的。我的所得等于你的損失,這就叫零和。更有甚者,革命會把盤子打碎,導致整個餅都沒法吃了。
此外,革命的代價比較慘重。通常,革命是一種暴力推翻另一種暴力,一種獨裁推翻另一種獨裁,很少有革命是用一種民主來取代另一種民主。
而改良的好處在于:首先,任何改良都不會讓對方徹底被消滅。也就是說,沒有你死我活,只是得大利或得小利。第二,改良通常會長期增值,會創造增量,把餅做大。即使是戊戌變法失敗了,它仍然創造了增量,比如京師大學堂。這些新生事物通常以不完全廢除舊秩序為前提,納新不吐故。因為,不是所有的改良對立派都會失去自己原來的利益。在改良中,他們往往也是既得利益者。
革命是瞬間完成的,但建設和完善是需要不斷改良的。如果后續的改良沒有跟上,革命的成果則無法保留。革命是標志和旗幟,不是結束,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而后續的改良,對于各階層的耐性則要求更高。革命容易形成共識,而改良是最難形成共識的。比如打敗蔣介石,你不愿意,那你就是敵人。但面對國企改革,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有理由。也許,改革的復雜性就在這里。
余世存:我支持革命。因為革命是代價最小、成本最低的社會演進方式。
革命有很多種。很多人往往把革命等同于暴力和流血,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其實,革命可以是不流血的。
而改良,取決于精英階層的一小撮人的意愿。他們會不會攫取改良的果實,成為新的特權階層?對大多數人而言,改良是個不太靠譜的事情。
從生物學上來講,精英階層也要經歷不斷衰敗的過程,到最后他們只能聽懂槍炮的語言。精英階層只能被槍炮所取代,別的形式的聲音對他們毫無幫助,無法把他們變得更高尚。
中國人與革命
主持人:革命和改良,中國社會多半選擇哪個?
余世存:有觀點說: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早就立憲了。這肯定是胡扯,是小文人情懷。依靠清政府怎么可能改良呢?更何況,民眾不該把自己的一切輕易讓他人代表。
吳曉波:在某些時刻,歷史是非常吊詭的。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十幾年里,改良和革命兩條路是并進的。最終,歷史選擇了革命,是一種偶然。馬克思說過:歷史如果沒有偶然,就會很無趣。如果將慈禧去世、皇族內閣產生,取消科舉制度、將大量精英排擠到體制外等等事件翻盤,清政府不著急取消科舉,或者慈禧晚死一兩年,又或者光緒沒有同時去世……說不定“立憲”有可能實現。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所謂“精英上升與衰亡”的結論只是一個邏輯推理而已,分析“革命”成因,還要從歷史背景和經濟基礎入手。
比如,1911—1921年這十年,由于俄國十月革命、一戰,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低潮,社會主義成了主流,整個世界陷入革命風潮,孫中山晚年也決意聯俄。因此,中國接下來的走向就變得可以預知。
1911年的中國實際上是個農民社會。那時候,城市化率為6%,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農村,城市中產階級人口少。由于面臨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爆發革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是50%,大量人口聚集在縣級以上的城市,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且革命思潮早已不是世界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也已經不復存在。而宗教方面,東方和西方不存在對立。
主持人:中國人是否缺乏改革、或者說是缺乏創新精神?
余世存:現在,中國有13億人,歐美國家人口才多少,怎么能有那么多發明創造?每個中國人都應該不斷自省,追求進步。而不是傻乎乎的生活,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精英階層。文明不是技術治國或精英治國。
中國是比較缺乏革新精神的民族,真正的進步,很難做到。中國人總是妄斷革命,總是將之等同為造反、恐怖、暴力。因此,中國有很多李逵、宋江。他們做的是造反,不是革命。這兩者差別很大。
中國人不明白,革命是讓人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創新。現代文明就是讓每個人都有獨立人格、思考的精神,能夠自己主宰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然后影響周圍的人。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想一想,如果沒有革命,人類怎么能進入文明時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一切生活資料,都是來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物理學革命,和五六十年代的科技革命。文明在技術領域的革命,肯定是先從思想領域發起的。吳曉波:中國人在經濟、思想方面的確缺乏足夠的創新。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三種秩序在起作用。第一種是政治秩序、第二是思想秩序、第三是經濟秩序。在中國,一直以來政治秩序凌駕于另兩個秩序之上。很多中國文人希圖從思想、文化的邏輯分析問題,其實那是很難分析清楚的。因為,政治家的要求永遠大于思想家和企業家。政治家解決問題永遠只是兩個:經濟發展、政權穩定。在中國歷史上,政權一直都在發展、穩定兩條路上搖擺。比如,1978年以后的30年,發展是硬道理;而現在,穩定才是硬道理。
高翔:中國企業,模仿多,改良多,革命少。這不是因為中國人不聰明,而是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升官發財,光宗耀祖,因此,我們投機取巧、浮躁,想掙錢……沒有人想過“我來到世上,就是為了在宇宙間留下不朽的印跡”。很多中國人崇拜喬布斯,想成為喬布斯,但是做不到,因為中國人不具備喬布斯那樣的世界觀。
的確,中國民營企業生存很難,因此很多民營企業靠著一點創新賺了第一桶金之后,就開始搞房地產、搞金融……但是,誰都有困難,喬布斯沒有困難嗎?困難不是借口。為什么喬布斯沒有去搞多元化?還是因為中國人沒有理念、沒有夢想。他們創業的最初動力就不是一個偉大的夢想。所以,什么掙錢做什么。
當然,這種情況應該會改變。我覺得,永遠不能依照過去計劃未來。也許,1000年以后,會有歷史學家評價現在的中國,和上一個一千年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