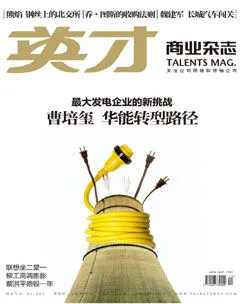搖晃的新富豪搖籃
2011年中國股市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在大盤一路唱跌、頻繁震蕩的大勢下,國內生物醫藥板塊耀出了僅有的幾點光芒。在孕育了李鋰、吳以嶺等億“國內生物醫藥行業正在快速發展過程之中。‘十一五’期間,國家投入了大量科研經費,萬富豪之后,生物醫藥板塊名副其實地成為了“新富豪搖籃”。
這正符合曾經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預言:以后,世界首富必將在生物技術領域誕生。而作為生物技術產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生物醫藥被賦予了太多夢想,成為被淘的“金礦”。
一時間,高成長、高回報似乎成了生物醫藥的代名詞,一些成立時間短短幾年的醫藥公司也紛紛打著生物醫藥的旗號,排隊上市。
然而,繁華的背后,似乎暗藏隱憂。這些年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定基礎,特別在研發領域,始終緊跟國際發展潮流。”不過,楊曉明坦言,中國生物醫藥市場雖然龐大,但中小企業‘十二五’規劃中又把生物醫藥行業作為戰略新興產業提出。此外,中國生物技術集團總經理楊曉明對《英才》記者表示。藥品市場的銷售額達到8500億美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生物醫藥行業今年前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300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1.04%;實現凈利潤25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4%。但這樣的增幅與去年同期的26.49%和28.03%相比,有所回落。更甚至,個別公司前三季度營業收入和利潤甚至出現近40%的下滑。
究竟,中國生物醫藥產業是足以撐起未來的經濟支柱,還是僅靠概念放大泡沫、曇花一現?面對行業估值仍偏高,且國內上市的生物醫藥公較多,規模偏小,行業集中度偏低,自主研發創新雖然活躍,但整體比較薄弱。同時,資金投入、技術成果轉換的機制等方面都需要不斷完善。
郭凡禮則把發展瓶頸聚焦到了更小的范圍。他指出,雖有政策綠燈,并有一定的稅收減免,但國內生物醫藥企業落后國際企業的關鍵所在,其實仍是對技術的研發美元,占比為16.5%。在中國,目比,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有一定的司普遍產品單一,受政策影響明顯的質疑,中投顧問醫藥行業分析師郭凡禮的觀點相當樂觀。他認為,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目前正處于起步階段。這一階段中,利潤下降不可避免,出現問題也屬正常,而接下來的新醫改以及“十二五”規劃,將對整個行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前景看好。資金掣肘以及研發資金投入的老問題。數字顯示,“十二五”期間,中央財政動員的“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資金約為400億元。而2010年全球十大研發領先藥企對研發的資金投入共計602.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近4000億元,是我國未來五年重大新藥創制資金的近10倍。“生物醫藥行業有長周期、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外資有先天優勢。”郭凡禮表示,“而我國連具備將收入的1%投入到研發的生物醫藥企業都很少。”
業內人士指出,其實,很多國內的大藥企并不是沒有錢。他們完全有實力拿出資金做研發,但由于擔心辛苦建立起來的品牌受影響,吳以嶺因此很多企業不愿意輕易嘗試。而中小企業雖然最希望憑借新藥在市場中立足,但他們又往往缺乏資金和研發實力。結果,看到眼前利益后,不少企業急功近利,畢竟做仿制藥收入快,門檻也較低。這正是我國生物醫藥領域90%以上的產品都是仿制藥的主要原因之一。
楊曉明也認為,我國生物醫藥行業發展的重點和難點表象是原創能力弱,其本質還是研發資金的短缺。而通過市場化或資本化的手段,提升包括科研創新、管理、市場等方面的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效果,尚需時日。
多個缺失
首次創新、標準認證、投融資、成果轉化……無論是在生物醫藥領域,還是在化學藥、中藥領域,甚至是醫療器械領域,其實,中國企業在這條產業鏈上的多個環節都有所缺失。而這些方面恰恰是外資的強項。
近年,拜耳、默克、默沙東、輝瑞等跨國藥企紛紛在華設立研發中心,有的甚至成立專項投資基金,投資或收購國內優秀的生物醫藥企業和項目。2010年7月,賽諾菲·安萬特以4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購買上海生命科學院研發的抗癌藥物的獨家許可;今年3月,諾華制藥以1.25億美元成功收購浙江天元生物藥業有限公司85%的股權,叼走了中國疫苗市場一塊“肥肉”。
針對這些現象,主流觀點認為,當前外資企業正利用成熟的經驗和完善的體系,在中國市場并購創新型企業,大肆收購研究成果。藉此,外資企業未來的市場占有率將會有進一步的提升,在競爭態勢中已占盡先機。
與這種近乎“折戟沉沙”的論斷相反,楊曉明眼中的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并非沒有機會。“創新能力強、科研成果轉化快、在管理上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以市場為導向運作的企業,最終可以勝出。”
楊曉明認為,市場化、國際化是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突破的關鍵點。為了在這兩點上有所收獲,中生集團進行了徹底的股份制改制。“自今年3月新版藥典正式實施以來,中生集團對研發條件、生產設施、質量標準進行了全面的提升,也加大了投資力度。在業務上,除了繼續保持疫苗和血液制品的主營業務外,我們還拓展了一些新的生物醫藥領域。”同時,加強國際合作,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也被列入中生集團下一步的發展重點。
資金的來源渠道越來越寬。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處長姚珺表示,從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資金、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資金、研發投資加計扣除等稅收政策,以及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創業板、中小板市場等四大財政金融方面出手,國家正加大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支持力度。中國醫藥工業科研開發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也表示,越來越多的醫藥企業正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資金,為技術創新、市場開拓、兼并重組和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條件。
不過,即使技術、資金問題解決了,在創新和醫學成果轉化之間通常還會橫亙一條“死亡峽谷”——標準。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在定制國際標準、取得歐美認證以及專利保護方面,話語權太弱。
“其實可以借國外企業和科研院所、高校的平臺,采用或共同研發,或一同承擔研發風險的發展模式。”郭凡禮表示,“雖然國內生物醫藥企業也會和科研院所、高校合作,但基本都是淺層次的。而國外科研院所市場化程度較高,高校的研發課題與企業需求也相當密切。”
“生物醫藥是靠時間和財力慢慢拼出來的,現在我們才剛剛起步,要達到相對成熟的發展階段,起碼還需要一二十年。”郭凡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