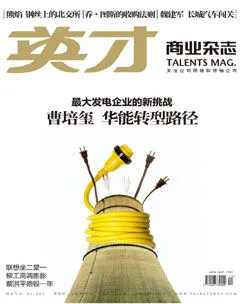曼氏金融 豪賭歐債的下場
2011-12-31 00:00:00何春梅
英才 2011年12期

同為高盛集團前主席、同為華爾街政商兩界通吃的大佬,剛剛辭去曼氏金融CEO職位的科爾辛和對沖基金經理保爾森,這兩位曾經的競爭對手,如今不約而同地陷入了他們職業生涯的低潮期。
先來看科爾辛。10月31日,科爾辛所供職的期貨經紀商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下稱曼氏金融)因投資歐洲主權債務損失慘重而申請破產。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該公司持有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和愛爾蘭主權債共計63億美元。
隨后的11月4日,曼氏金融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科爾辛辭去在全球曼氏金融的所有職位。
再來看當年的勝出者保爾森,如今的處境可能也和科爾辛一樣尷尬。
曾經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押注房貸抵押證券而一炮走紅的保爾森,其旗下的基金在今年大多數時間內都蒙受了虧損,旗下的旗艦基金Advantage Plus fund在9月下跌19.35%,今年以來的跌幅達到46.73%,幾近腰斬。
9月大規模拋售黃金使保爾森基金的虧損雪上加霜。雖然包括Lee Ainslie、Leon Cooperman在內的許多基金經理人也遭受虧損,但保爾森卻成為今年業內的大輸家。
“科爾辛和保爾森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賭。科爾辛賭政府會救歐債,結果賭輸了;保爾森過分押注某一領域,想讓利潤無限擴大,結果證明也賭輸了。豪賭和貪婪,是投機者的典型特征。”中信銀行國際金融市場專家劉維明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表示,除了科爾辛和保爾森在賭,歐債本身也是一種賭博,“只要這種賭徒心理繼續存在和蔓延,金融危機還將發生,不管是局部的還是全球性的。”
曼氏金融緣何“豪賭”歐債?真的是因為賭錯了以致陷入當前申請破產的境地嗎?保爾森的大起大落也是源于豪賭嗎?為何金融機構包括政府都喜歡“賭”?中國的民間借貸是否也是一種賭博?如何才能規避下一次可能的金融危機?
豪賭的大佬
科爾辛的“下臺”雖沒有言明是“引咎辭職”,但在業界看來,曼氏金融當前面臨的危機,和科爾辛有著很大的關系。
科爾辛的履歷相當出彩:前高盛集團主席,曾經在1999年帶領高盛集團進行了獲利頗豐的首次公開募股,不過最終他還是因敗給競爭對手保爾森而丟掉了高盛集團主席的頭銜。2000—2005年,科爾辛出任美國新澤西州參議員,在該州州長競選中勝出。
不同尋常的政經背景,讓科爾辛在加入全球曼氏金融時曾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事實上,在科爾辛就任曼氏金融之前,很多評級機構就已經看到了公司可能的財務危機。然而,科爾辛一上任,就提出了打造全方位服務的投資銀行“小高盛”的戰略。不再安于做一些傳統的經紀業務,也不是縮減已經規模太大的歐債自營交易,科爾辛利用公司的自有資金進行了更多的自營交易。
豪賭的結果業界都看到了,科爾辛將曼氏金融送上了破產法庭。“科爾辛賭的是政府會救歐債,只要政府出手,歐債就沒事了,而且危機會很快過去;加上歐債已經跌得很低了,一旦好起來將會大賺一筆。”劉維明分析說。
和科爾辛系出高盛同門的保爾森,因為押注了美國住房市場的泡沫將破裂,并大舉做空金融股,保爾森的對沖基金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賺了至少上百億美元。不過,今年以來,他卻屢屢成為負面新聞的主角。
“保爾森在危機期間大賺了一筆,但不意味著他就是一個穩健的風險管理者。過分地押注某一類資產絕不會是一個穩健的投資管理者應該做的事情,即便是對沖基金,這種策略也是不可行的。”劉維明分析說。
國際金融專家趙慶明向《英才》記者表示,科爾辛和保爾森所操作的產品是有共性的,比如說都是高杠桿率的衍生產品,都是在O T C市場做的,標的都是一些匯率、國債、期貨等等,客戶都是非常少的。“這些產品市場流動性很差,參與者少,往往是一對一甚至量身定做的交易,市場平靜時沒有問題,一旦市場發生大的變動,賺了就是狂賺,虧了就是巨虧,想平倉都難。”
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如果都是非常謹慎地做風險管理和防控,及時平倉,將風險敞口控制在自己能夠承受的范圍內,不會出現類似科爾辛,包括前段時間類似瑞銀的魔鬼交易員事件。而一旦陷入了賭博,一切就會變得無法預期、不可控起來。
而在劉維明看來,除了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們喜歡賭博,包括歐債危機,甚至包括我國的地方債、民間借貸,同樣也是在走鋼絲。
最后一棒的賭徒
“歐債那么大的財政赤字,傻子都知道不可持續,但卻都在拖,不斷發新債還舊債。政府都在賭,賭在自己任期內不會出事,賭危機很快就會過去。”劉維明如此評論歐債危機。
長期的財政赤字,加上償債能力有限,或者沒有償債能力,到了市場不認可時自然會發生逆轉。而對歐債的購買者來說,前期可能有一撥人是賺了錢的,但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則可能是巨虧的。
緣何政府明知可能出現危機仍然大規模舉債?為什么不去深究背后可能的結果,而只是去看短期的繁榮,短期利益群體的利益最大化?
劉維明認為這是投機心理在作祟,包括金融機構,包括政府,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貪婪、好賭。“這些也是人性的弱點,是沒有辦法消滅的,只能靠機制和制度讓這些特性少點發作。”
另一個必然的原因是金融發展過快,勢必以投機和賭博來支撐,因此,“在金融監管和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的發展方向一定不能以投機為導向,要落實到金融的發展速度不能超過實體經濟的平均水平。”
而目前的整個金融體系,其實是鼓勵投機的。無論從經濟體對于金融系統的依賴,還是大力發展、扶持、救助金融機構,都可以看出這種鼓勵的氣氛。而這些金融機構在被救助之后依然不規范,依然還要走老路,加上還有如此寬松的貨幣政策等等。
在劉維明看來,只要鼓勵投機的問題不解決,金融危機就不可能規避。這一切也同樣給中國的民間債務敲響了警鐘。
“中國的民間債務其實也是這種賭徒心理的表現。動輒百分之幾十的利潤,吸引著放貸者和借貸者參與豪賭。放貸的人賭借貸的人不會出事,很快就能度過過渡期;借貸的人賭自己不會出事,結果卻最終只能以跳樓和逃跑來應對。”劉維明說。中國民間債務危機最典型的地方是溫州。
今年以來,溫州錢荒加劇、違約增加,民間借貸機構只得提高“利率”對沖風險。而“炒錢”的財富效應又吸引了更多民間資金介入。有報道稱,溫州危機爆發前,87%的溫州家庭涉及民間借貸,甚至有不少人用房子抵押放貸。
或許2008、2009年民間借貸的利率相對合理,對很多中小企業解決資金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到了2010年開始,民間借貸的貪婪本性膨脹,以致形成了高利貸并出現信貸危機。
“溫州事件,那么多老板跑掉之后才有人來管,之前難道不知道嗎?包括鄂爾多斯,相關部門到底是不能管還是不愿意管?很顯然,我們的監管部門也在賭,賭這些借貸者和這些放貸者不會出事。”劉維明說。
那么,長期賭下去,將會是什么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