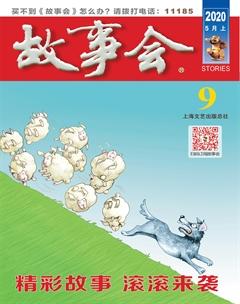拼餐
黃超鵬
下班后,阿明走在路上,尋思著找家飯店解決晚餐。突然,迎面走過來一個(gè)老頭,客氣地?cái)r住阿明,請求幫忙。老頭說拐角有家快餐店有開張優(yōu)惠,店內(nèi)套餐買一送一,不過得手機(jī)支付。
老人解釋道:“我年紀(jì)大了,不懂手機(jī)付錢,所以想請你幫忙買那個(gè)套餐,買一送一嘛,錢我們一人一半,我給你現(xiàn)金。”阿明張望了一眼老頭說的那家店,覺得這主意不壞,這不正是時(shí)下流行的“拼餐”嘛。于是,他痛快地答應(yīng)了。
老人把自己那份錢交給阿明,阿明在前臺(tái)點(diǎn)完餐,被服務(wù)員領(lǐng)進(jìn)里間坐下。阿明原本想邀老人一起坐,但老人笑笑說:“我打包回家吃就行啦!”

上菜了,阿明看看菜色就皺了皺眉,店內(nèi)沒啥服務(wù),菜品也實(shí)在一般,難怪“買一送一”都沒有幾個(gè)客人。阿明邊吃邊搖頭,心里懊悔不已。
過了一會(huì)兒,阿明吃完走出飯店,走著走著,他又看到了剛才那個(gè)老人,老人在街頭徘徊著,手里卻沒有拎外賣。阿明覺得奇怪,這時(shí),只見老人又?jǐn)r住一位路人攀談起來,沒一會(huì)兒,老人就領(lǐng)著人再次走進(jìn)了飯店。
原來……阿明看出了門道,心里直呼“上當(dāng)”。
阿明氣不過,正打算沖進(jìn)店里去揭穿老人的“把戲”,沒想到他剛跨進(jìn)店門,就聽剛才那個(gè)路人沖著老人嚷道:“呵,說得好聽,套餐買一送一,可這里的一份套餐比外頭兩份套餐的價(jià)格還貴!老頭,我前腳進(jìn)店,你后腳就空著手走了,你這不是要‘拼餐,敢情你就是個(gè)‘導(dǎo)購吧!”
(發(fā)稿編輯:丁嫻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