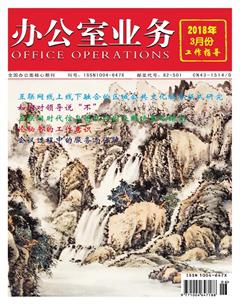爭做新時代的劃槳人
朱越嶺
【摘要】南湖紅船承載著精神力量、時代價值和鮮紅底色。要大力弘揚“紅船精神”,爭做新時代的劃槳人。堅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著紅船航道奔向遠方;堅持敢為人先百折不撓,高揚紅船風帆勇立潮頭;堅守忠誠為民初心不改,擔當紅船使命共圓夢想。
【關鍵詞】紅船精神;新時代:劃槳人
一葉紅船,時間分野。從歷史的維度審視,1921年注定是極不平凡的。那個盛夏,神州大地正是風雨如晦,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畫舫,迎來了最為神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一位宏圖在胸的世紀偉人透過蒙蒙煙雨,把目光投向了整個神州,似乎其間萌生無數火種,先是星星點點,必將浩浩蕩蕩。小小紅船,載著刷新一個時代的火炬,挾著億萬同胞的呼喊,帶著無往不勝的堅毅,跨山越水、穿林奔野,染紅萬里山河,掀起磅礴巨浪,中華民族波瀾奇偉的嶄新畫卷就此闊展開去。
時間若行云流水。80多年后,泱泱秀水蕩起的漣漪仿佛從未平息。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從容鎮定地佇立在那艘紅船上,同樣把目光投向了風云變幻的世界。每個國家民族,每段歷史時空,都要有自己的精神指引。那些熱血沸騰的信仰故事,那些閃耀星河的信仰腳印,終要轉化為激勵前行的精神動力。“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紅船所承載的精神力量、時代價值和鮮紅底色,永不褪色,永放光芒。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又來到熟悉的紅船旁,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在南湖革命紀念館熠熠生輝的黨徽下,他再提“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重申不忘初心的歷史使命,并做出了“結合時代特點大力弘揚‘紅船精神”的諄諄囑托。這一幕跨越時空,與中共一大紅船會議的景象遙相呼應,永久定格在歷史長卷中。
真理的力量,往往無懼逝水與光陰的刀刻。在黑云壓頂、山河動蕩的民族危亡時刻,開天辟地闖出一條煌煌大道,離不開“紅船精神”的指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交匯期,巍巍巨輪在世界汪洋中劈波前行,同樣需要“紅船精神”。“紅船精神”是中國革命的精神之源,凝結著黨的初心使命,體現著黨的價值追求,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筑成我們黨新時代的永恒精神和思想豐碑。
一、新時代堅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著紅船航道奔向遠方
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我們黨今天已有8900萬黨員,世界第一大黨就要有大的樣子、大的氣魄、大的偉岸。在這條接續前進、接力奮斗的道路上,我們黨以無與倫比的勇氣、智慧和定力,點燃中國革命的燎原之火,續寫奮力崛起的改革篇章,開啟走向復興的偉大征程。這種勇氣、智慧和定力,正是源于對我們所選擇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無比自信。只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上下同欲、奮發蹈厲,我們必將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二、新時代堅持敢為人先百折不撓,高揚紅船風帆勇立潮頭
奔涌向前的時代長河,挑戰與機遇交織、使命與夢想激蕩,但從來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發展之路無坦途,美好愿景須奮斗。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1年建黨100周年。這條時間軸,既是人民的幸福線,也是奮斗的路線圖。新征程、新藍圖,唯有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登高望遠、居安思危,跨越高峽平湖,趟過激流險灘,才能始終屹立于時代發展潮頭。
三、新時代堅守忠誠為民初心不改,擔當紅船使命共圓夢想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96年依水行舟、96年風雨同舟,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我們黨初心不忘、使命如磐。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是最大國情、最大實際。紅船啟航靠的是人民群眾的支持,紅船遠航更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擁護。只有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本色,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新時代、新征程、新篇章,我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在“紅船精神”指引下,推動中國號巨輪劈波斬浪,勝利駛向更加光輝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