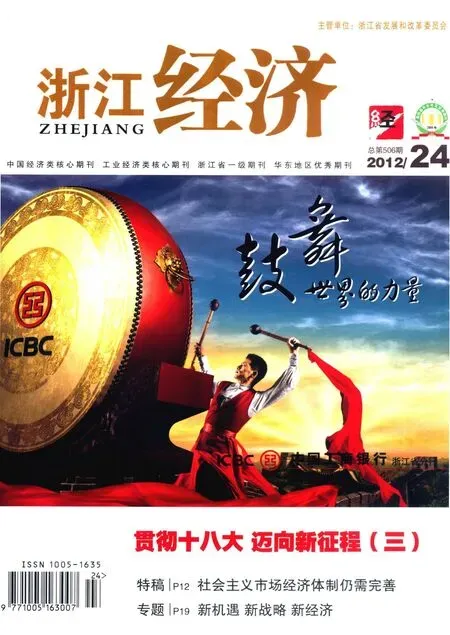關(guān)注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
□ 文/吳可人
農(nóng)村征地制度改革的破局,意味著中國(guó)將開始逐步扭轉(zhuǎn)靠犧牲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現(xiàn)狀
十八大報(bào)告提出讓農(nóng)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益,隨后11月28日國(guó)務(wù)院常務(wù)會(huì)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duì)農(nóng)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bǔ)償制度作了修改,業(yè)內(nèi)人士分析這一修改或?qū)⑻岣哒鞯匮a(bǔ)償數(shù)額至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的10倍以上。農(nóng)村征地制度改革的破局,意味著中國(guó)將開始逐步扭轉(zhuǎn)靠犧牲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現(xiàn)狀。
在現(xiàn)行土地制度下,浙江與全國(guó)相當(dāng)部分地區(qū)一樣,長(zhǎng)期面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問題。根據(jù)浙江省建設(shè)廳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1996—2011年,全省城市和縣城建成區(qū)面積年均增長(zhǎng)6.9%,而城區(qū)人口年均增長(zhǎng)4.8%。對(duì)于人多地少的浙江而言,用地矛盾更顯突出。
城市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過于依賴土地占用,新增建設(shè)用地產(chǎn)出較少。以工業(yè)為例,全省11個(gè)市區(qū)合計(jì)工業(yè)用地增加數(shù)在2003年達(dá)到54.6平方公里的峰值,同年這些地區(qū)的工業(yè)增加值增速也達(dá)到此后歷年的最快增長(zhǎng)(42.9%)。而在2003年后,由于中央采取最嚴(yán)格的措施控制耕地占用,城市工業(yè)增加值增長(zhǎng)與工業(yè)用地開發(fā)同步趨緩,多數(shù)年份甚至低于全國(guó)工業(yè)增加值增速,表明城市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土地占用形成的,一旦供地閘門關(guān)緊,就出現(xiàn)增長(zhǎng)趨緩的困局。
城市空間蔓延式向外擴(kuò)展,城市人口密度較低。這一狀況在大中城市尤為明顯。伴隨房地產(chǎn)開發(fā)迅猛推進(jìn),一方面新建住房入住率較低、空置率較高;另一方面舊城設(shè)施落后使得大量舊房空置,導(dǎo)致城市用地過多,人口分布分散,進(jìn)而造成城市公共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問題。2011年,全省11個(gè)市區(qū)平均人口密度為1773人/平方公里,列全國(guó)各省市倒數(shù)第7位。

城市用地效率較低,浪費(fèi)現(xiàn)象仍普遍存在。企業(yè)圈地囤積居奇,有些企業(yè)拿到地后,遲遲不開工,甚至閑置兩三年;有些企業(yè)申請(qǐng)土地目的就是等待土地升值,炒買炒賣,牟取暴利。某市經(jīng)濟(jì)發(fā)展局的一份內(nèi)部報(bào)告表明,全市有3000多畝工業(yè)建設(shè)用地閑置或出租,有的土地已經(jīng)閑置兩年以上。
快速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jìn)程,為土地從農(nóng)業(yè)用途向非農(nóng)業(yè)用途、從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轉(zhuǎn)帶來巨大需求。而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的非市場(chǎng)化因素,導(dǎo)致相當(dāng)部分的農(nóng)民被排除在土地溢價(jià)的獲利群體之外,成為城市化過程中的權(quán)益受損群體。土地城市化推進(jìn)過快背后,是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很大程度上的缺失,這里存在著兩個(gè)比較嚴(yán)重的問題。
一是農(nóng)民缺乏談判能力弱化了用地制約。農(nóng)用地由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行使所有權(quán),政府征地實(shí)質(zhì)上是農(nóng)用地變?yōu)榻ㄔO(shè)用地,所有權(quán)由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所有變?yōu)閲?guó)家所有,并由當(dāng)?shù)卣鎳?guó)家行使土地所有權(quán)。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與當(dāng)?shù)卣哂星Ыz萬縷的聯(lián)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聽命于政府。因此,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缺乏和政府進(jìn)行平等談判的能力,征地往往通過政府下達(dá)行政命令的方式完成。而且由于農(nóng)戶土地承包權(quán)的殘缺及其債權(quán)性質(zhì),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集體組織在土地關(guān)系中往往處于最弱勢(shì)地位,農(nóng)村土地所有權(quán)保護(hù)缺乏有效防線,農(nóng)用地迅速非農(nóng)化在所難免。特別是有些商業(yè)性項(xiàng)目以國(guó)家名義征地,用國(guó)家利益迫使農(nóng)民就范,更弱化了對(duì)于用地單位的約束。
二是向農(nóng)民征地成本較低強(qiáng)化了圈地沖動(dòng)。現(xiàn)行的土地征用制度,農(nóng)用地征用價(jià)最高按農(nóng)用地年平均產(chǎn)值的30倍補(bǔ)償,而具體補(bǔ)償多少取決于政府有關(guān)部門。土地進(jìn)入城市后,商業(yè)用地和工業(yè)用地價(jià)格則由“招拍掛”決定。同樣一塊土地,因?yàn)橥恋匦再|(zhì)的轉(zhuǎn)換就會(huì)產(chǎn)生大幅度的土地增值,形成巨額的利潤(rùn)空間。在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增值部分的分配格局中,征地的溢價(jià)收益只有10%-20%左右歸村集體所有,其余80%左右的溢價(jià)收益被政府和用地企業(yè)享用。因此,現(xiàn)行制度對(duì)于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僅是一種純粹的補(bǔ)償關(guān)系,而非等價(jià)交易關(guān)系,農(nóng)民基本上不能獲得土地改變用途、進(jìn)入城市之后的溢價(jià)。這種狀況下,圈地升值成為一些企業(yè)獲取暴利的主要手段。相關(guān)利益集團(tuán)為取得農(nóng)用地用途轉(zhuǎn)換所帶來巨額土地溢價(jià),必然會(huì)爭(zhēng)相運(yùn)用各種手段盡可能多占土地。
保護(hù)和提高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是增加農(nóng)民收入、改善農(nóng)民生活的有效手段,是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重要保障,是讓廣大農(nóng)民真正分享城市化成果、加快建成小康社會(huì)的根本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2012,征地制度改革破局,給農(nóng)民帶來最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