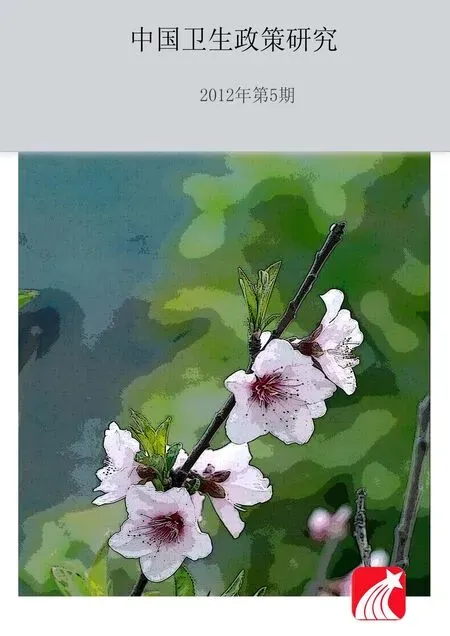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的家庭醫生制度探討
謝春艷 胡善聯 何江江 王力男 彭穎
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040
國外不同國家對全科醫生與家庭醫生有不同稱謂,但內涵基本一致。家庭醫生制度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最經濟、最適宜”的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模式,是以全科醫生為主要載體、社區為范圍、家庭為單位、全面健康管理為目標,通過契約服務的形式,為家庭及其每個成員提供連續、安全、有效、適宜的綜合醫療衛生服務和健康管理的服務模式。我國新醫改明確提出了“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目標,使社區成為實現醫改目標的重要載體,國內很多地區在原有社區衛生服務和全科醫生服務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多種家庭醫生服務模式,但關于家庭醫生的稱謂各地不同,內容各異,尚在探索、完善階段。本文主要是以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本理論為視角,結合上海市實施的家庭醫生試點探索與實踐進行的一些思考,因而采用家庭醫生的稱謂,與國務院提出的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總體框架并無沖突。
1 國內外關于家庭醫生制度的研究現狀
家庭醫生服務模式因為其獨特的優勢,受到了西方很多國家的重視,目前,世界上約有50個國家或地區設有家庭醫生組織,有15萬名以上經過正規訓練的家庭醫生為患者提供基本健康服務。[1]在這些國家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家庭醫生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通過對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家庭醫生服務模式比較成熟的國家的總結分析可以看到,盡管存在差異,但在總體上家庭醫生服務模式具有以下特點:在服務目標上,家庭醫生凸顯“守門人”的作用,在健康管理、調節衛生資源、合理控制醫療費用、雙向轉診等方面承擔著重要職能;在人才來源上,各國對家庭醫生有嚴格的資質審核要求,也建立健全了家庭醫生培養制度;在服務內容上,各國家庭醫生的服務項目覆蓋健康管理各個方面,包括疾病診斷及處置、健康咨詢、體檢、轉診、家庭訪視以及配合其它衛生機構開展專門項目如慢性病管理、計劃免疫等;在服務形式上,一是建立與居民簽約機制,二是在此基礎上建立首診制度;在服務經費上,最典型的是英國按照人頭預付制度。
在我國,家庭醫生服務模式是在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大框架內發展的。200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對社區衛生服務明確提出了完善服務功能的要求,強調“轉變社區衛生服務模式,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堅持主動服務、上門服務,逐步承擔起居民健康‘守門人’的職責”。[2]201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加強我國全科醫學學科建設、建立全科醫生制度。新醫改明確提出了“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使社區成為實現醫改目標的重要載體,而家庭醫生制度的實施是社區衛生服務改革發展的重要舉措。近兩年,國內部分發達地區開始在原有的全科團隊社區衛生服務模式基礎上,探索借鑒國際經驗,開展深化家庭醫生服務模式改革的試點工作,如上海、北京[3]、深圳[4]、青島[5]等,這些地區以常住或戶籍居民為范圍,建立與居民簽約的機制,通過政策手段引導居民自愿在社區首診,通過預約提供基本醫療、公共衛生和指導轉診等服務[6],但均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家庭醫生制度的制度設計、模式構建和實施過程仍存在很多困惑和不足,亟需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社會學等跨學科視角的研究還很缺乏。
2 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的家庭醫生制度
在醫學視角下,家庭醫生制度是衛生服務到社區和家庭。在社會學視角下,家庭醫生制度是“基于社區、以社區人群為服務對象”的衛生服務。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疾病譜的變化,醫學模式從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對健康的關注點也逐漸從治療轉向預防,從疾病管理轉向健康管理。社會發展理論認為,社區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社區衛生服務是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的重要環節,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衛生服務模式要實現社區化,要以社會發展和社區建設的理論來指導,不是簡單地把醫學知識和醫院服務應用在社區中。為了克服家庭醫生制度缺乏社會參與和社會認同的瓶頸問題,應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
2.1 社會資本的概念
社會資本的概念從表述的實際意義上主要分為兩種:一是與國家公有形式的資本相對應的來自社會個體、非營利性組織的有形資本,如土地、勞動和資金等;二是來源于社會學對社會資本的界定,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正式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7],后來詹姆斯·科爾曼和羅伯特·普特南等人進一步發展了社會資本理論[8-9],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加拿大的政策研究基金會(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PRI)在征求了全球許多社會資本研究者意見的基礎上,對社會資本給出了一個新的定義,即社會資本是建立在信任、互惠、互助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網絡,借助于這樣的社會關系網絡,個人或團體能夠獲得各種資源和支持。[10]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主要有社會制度、社會組織、社會關系、社會規范、社會文化、社會凝聚力等。社會資本各要素狀態良好并充分發揮其作用,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
與有形的社會資本相比,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資本是無形的,更強調社會結構中組織、個人動員和利用有形資源的能力和效率。[11]界定社會資本的因素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社會參與、信任與安全感、互惠與社會支持、人際關系網絡、鄰里凝聚力、非正式社會控制、社區歸屬感與認同感等維度。
2.2 社會資本理論在健康領域的應用
當前提出吸引社會資本進入衛生領域,更多的是強調有形資本,對無形社會資本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重視。有研究將社會資本引入衛生和健康領域,闡述了社會資本的衛生保健功能,認為激活和利用社會資本是保證衛生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12]國內健康領域對社會資本的測量目前還很少。哈佛大學和山東大學的一項合作研究同時測量了作為結構型社會資本的組織成員身份和作為認知型社會資本的信任、互惠、互助,對山東省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與健康的關系進行的分析表明,個人層次的認知型社會資本與自評總體健康、心理健康正相關,村莊層次的認知型社會資本也與心理健康正相關。[13]在社會衛生資源利用策略研究中,研究者同時測量了道德與價值觀、信任與安全感、友好互助、人際關系網絡、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和參與等多個維度的社會資本,研究發現,對居民健康具有保護作用的社會資本要素包括“認識本社區內較多的人”、“與同事相處融洽”以及“外出時請鄰居照看房子”。[14]對參加新農合支付意愿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是影響農民參保的重要因素之一。[15]
2.3 社會資本與家庭醫生制度的關系
社會資本與家庭醫生制度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
從微觀層面來講,社會資本的發展可以促使社區疏離狀態和人際關系的轉變,也有利于居民與家庭醫生的社會互動模式轉變。社區社會資本的引入通過改變城市社區的“原子化”和疏離狀態,增強社區信任,改善人際關系,從而潛移默化的改變居民和家庭醫生雙方的態度、角色和行為,提高對家庭醫生制的價值認同:居民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家庭醫生從被動工作到主動服務,進而轉變居民與家庭醫生的社會互動模式,由原本防范、對立的關系轉變為基于信任和互惠的良性互動,反過來進一步提高居民對家庭醫生制度的認同度和參與度,家庭醫生的工作積極性和職業成就感也得到進一步提高。
從宏觀層面來講,社區社會資本是家庭醫生制度發展的內源動力。在服務市場的運行分析上,社會資本是溝通個人和制度的中間物。個人行為能否實現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和諧,以及制度能否解決集體行為的困境,不僅取決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中間媒介——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在很大程度上營造一種文化、制度環境,引導人們的參與、合作與信任,成為影響個人態度、行為、決策以及健康和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推動協調的行動來促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得出如下假設:在一個擁有豐富社會資本的社區里,交易成本降低,則制度的僵化或滯后所帶來的阻力減小,從而效率也就提高。[16]
家庭醫生制度的順利實施,一方面需要政策和硬件支撐,包括財政投入、信息化建設和醫保政策的調整等;另一方面,更需要價值態度的轉變,尤其需要贏得社區認同和相關利益方等多方面的社會參與。家庭醫生制度在完成居民健康管理功能的同時,還應發揮其提升社區功能、擴大社區支持網絡、積聚社會資本的社會功能,實現健康管理與社會功能的整合。
3 建立家庭醫生制度中社會資本的激活與培育
要建立家庭醫生制度,社會資本的培育是個關鍵問題。以信任、合作與互惠為基礎的社會資本不是某一社區天然擁有的,而需要經過有目的的培養、演進而逐漸生成,一旦無形的社會資本形成之后,往往會成為社區衛生服務和家庭醫生制度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培養這種無形社會資本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社會對社區概念的重視、社區整體環境的改善,需要在如何促進信任、尋求合作等方面努力,并且具體的措施與對策之間彼此協同。
結合我國社會文化及衛生保健實際情況,有學者提出社會資本的激活途徑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政府行為,法律、政策(包括衛生政策、法規)、管理規章制度等;二是教育、培植:道德規范教育、文化教育等;三是引導:文化輿論導向、精神鼓勵、社會參與以及受益密切聯系等。[12]
從微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的激活與培育需要通過多種形式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惠與合作,例如居民委員會和志愿者等社會團體可以通過各種活動以增強居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增強他們之間的社會資本。從宏觀層面,結合家庭醫生制的實施來看,社會資本的培育需要通過制度規范、政策引導以及輿論導向和宣傳教育,從而推動微觀層面的態度、角色行為以及互動模式的轉變。在實施家庭醫生制的過程中,完善的制度規范和有力的政策引導有利于為社會資本培育和互動模式轉變創造良好的環境,無論是社區居民還是家庭醫生,其態度轉變和角色行為的有效發揮均需要規范和引導。例如,居民對家庭醫生制的理解需要通過社會動員和媒體宣傳來實現,居民某些不合理的醫療需求和就醫觀念需要通過健康教育來引導,其就醫行為和就醫習慣需要通過簽約、定點醫療、支付方式、報銷比例等制度和政策進行約束規范。家庭醫生的行為要通過提高待遇水平、績效考核等各種激勵機制進行規范引導,業務水平要通過培訓和繼續教育不斷提升,另外,職業成就感需要通過提高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等精神鼓勵進行引導。
4 形成社區社會資本的網絡,推動家庭醫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社區衛生服務和家庭醫生制度是社區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社區發展規劃應該納入家庭醫生制度;反過來家庭醫生制度也離不開社區發展的外部環境和配套支撐。家庭醫生制度應作為整個醫療衛生體系的核心和根本,不應僅僅局限于社區衛生的層面,還應拓展到包括二三級醫院在內的整個醫療服務提供體系,成為整合醫療衛生資源以及社會、社區多方面資源的紐帶。
除了社區微觀層面的人際社會資本,家庭醫生制度運行的外部環境還存在著多層次的中觀組織層面和宏觀社會層面的社會資本,包括街道、居委會等基層行政力量;民間社會的很多非營利組織,各種社團組織如志愿者協會、社會工作者團體、社會福利組織、慈善機構、教會組織等;公共衛生機構、二三級醫療機構等其他衛生機構,這些組織對家庭醫生制度的認同與支持,多種社會服務、社區服務與家庭醫生服務的整合與協同,也是有利于推動家庭醫生制順利實施的重要的社會資本,需要進一步挖掘和整合各方資源。
有學者認為,中國城市社區組織發育緩慢和不完全,給社區衛生服務健康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推遲了衛生服務“社區化”進度。[17]家庭醫生服務如果沒有社區非營利組織的扶持,家庭醫生就會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缺乏和居民溝通的社會橋梁,不利于調動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同時,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是社區重要的人力資源之一,沒有他們的合作,家庭醫生服務工作團隊工作方式就是一句空話。合理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多層次性,就可以形成社區社會資本網絡,有利于家庭醫生制度的茁壯發展。
[1]楊秉輝,祝善珠.全科醫學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2]David Weller,James Dunbar.General Practice in Australia:2004[M].Fyshwick:National Capital Printing,2005.
[3]方芳.北京“片兒醫”聯系卡年內發到每戶家庭[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半月刊,2008,10(7):30.
[4]王瑩.青島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亮點[J].山東社會保障,2008(4):20-22.
[5]賴光強.深圳市實施家庭醫生責任制項目路徑的分析與思考[J].中華全科醫師雜志,2009,8(11):813-814.
[6]許巖麗,劉志軍,楊輝.對中國衛生守門人問題的再思考[J].中國醫院管理,2007,27(8):39-41.
[7]Richardson 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Education[M]. 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8]Coleman J 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9]Putnam R.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0]PRI.Social Capital as a Public Policy Tool(Project Report)[R].Canada: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PRI),2005.
[11]馮國雙,郭繼志,周春蓮.我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存在的問題及建議[J].中國全科醫學,2002,7(7):478-488.
[12]盧祖洵.社會資本及其衛生保健功能[J].醫學與社會,2000,13(1):3-5.
[13]Yip W,Subramanian S V,Mitchell A D,et a1.Does social capital enhance health and wel1-being?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7,64(1):35-49.
[14]白玥.社會資本與社會衛生資源利用策略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6.
[15]張里程,汪宏,王祿生,等.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意愿的影響[J].中國衛生經濟,2004,23(10):15-18.
[16]馬吏,薛秦香,廉昭.試論城市社區社會資本對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的影響[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7,20(1):99-100.
[17]劉軍安,盧祖洵,孫奕.中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理論及其實踐缺陷[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4,20(6):32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