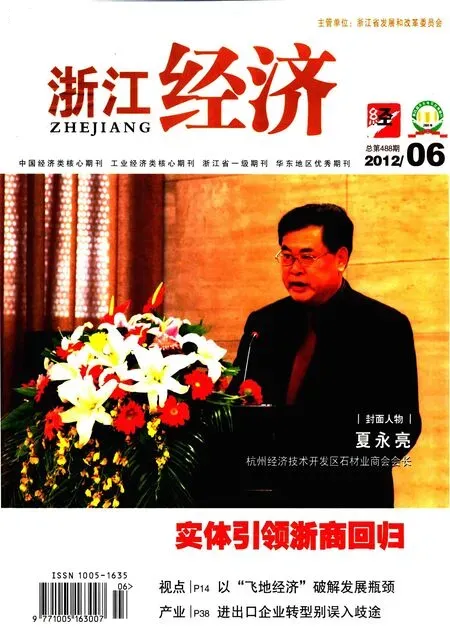以“飛地經濟”破解發展瓶頸
□文/陳建軍梁佳
“十二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對浙江發展來說,沒有比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步伐更為關鍵的事情了,近年來浙江的轉型升級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比較長三角兄弟省市來說,差距有趨于明朗的態勢。
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大趨勢下,局限于一省一市的空間范圍謀劃產業轉型,效率不理想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事。在資源要素流動的大背景下,以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構筑新的平臺——聯合開發區,以此大力推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應該是浙江轉型升級新戰略的重要內容。
聯合開發區的功能
聯合開發區,又稱“異地合作共建開發區”、“飛地開發區”、“產業轉移合作園區”等,是以跨區域合作共建為特征的一種新興開發區模式,聯合開發區的主要功能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一是資源要素的交換。一般來說,產業轉移的發動方擁有資本和技術等產業資源優勢,而產業轉移的接受方相對擁有土地和勞動力資源,或者市場資源方面的優勢,雙方通過聯合開發區這一平臺進行資源和要素交換,將產業資源的空間遷徙這一原本更多的表現為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轉化為相關地區通過資源要素的交換克服彼此發展瓶頸的宏觀經濟行為,從而有助于克服產業轉移中的區域利益失衡壁壘,推進區域協調和一體化發展,這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具有特殊意義。
二是形成區域創新空間。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創新更多來自于多元化的資源要素集聚,包括多元文化的匯聚和融合,聯合開發區的形成有助于打破相關地區由傳統產業結構支撐的相對固化的社會經濟發展格局,為該地區注入更加先進的要素資源和發展理念,通過融合發展,形成區域創新的新空間和地區發展的增長極,并通過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聯合開發區建設的蘇滬經驗
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是我國最早出現的跨國聯合開發區,在此基礎上,江蘇省2003年啟動了國內第一個跨區域合作的聯合開發區——江陰靖江工業園區;2005年江蘇省委出臺《關于加快蘇北振興的意見》,提出了南北掛鉤共建產業園的設想;2006年,江蘇省出臺了《關于支持南北掛鉤共建蘇北開發區政策措施》;2009年,江蘇省政府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共建園區建設政策措施的通知》。在自上而下的推動下,江蘇成為我國聯合開發區發展最快的地區。截至2011年底,江蘇省的聯合開發區(江蘇稱為“共建園區”)達到33個,僅2011年就新增了7個。
江蘇的基本做法是:蘇南與蘇北城市相互結對,由蘇北地區在本地省級以上開發區中,劃出一定面積的土地作為“園中園”,確定為聯合開發區,兩地分工協作,蘇南地區負責園區的規劃、投資開發、招商引資和經營管理等工作,蘇北負責園區的拆遷安置、基礎設施配套、社會管理等工作。園區還享受土地指標、省財政補貼、電價優惠等諸多政策。在園區利益分配上,雙方10年內的收益全部用于滾動發展,10年后再按一定比例分成。區中園建設遵循市場導向、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集約開發、可持續發展五條原則。在領導管理體制上,通常有三個層級,即南北雙方政府聯席會議、園區管委會、園區投資開發公司。受益與蘇南蘇北聯合開發區的成功經驗,江蘇還積極展開和上海市的合作,大力興辦跨省聯合開發區。目前上海、江蘇合作共建的聯合開發區已達11個,如上海楊浦區大豐、海安產業園、昆山浦東軟件園等,得益于聯合開發區的建設,2010年僅蘇北地區實際引資就達972.7億元。
近年來,江蘇一直保持較好的增長勢頭,大力推進聯合開發區建設是一個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江蘇省在推進聯合開發區建設時,強調政府政策干預和行政推動,聯合開發區建設在江蘇不僅成為一項經濟工作,也成為一項政治任務,上下驅動,合作速度快,效果也比較明顯。
上海也是聯合開發區的積極實行者,已在市外建立20多個聯合開發區(上海稱為異地工業園或開發區分區),其中落戶江蘇的最多,其次是浙江和安徽。上海這些年來面臨著產業轉移和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特別是制造業,正處于產業鏈再編、布局重組的關鍵時期,對內“走出去”,在外省市特別是空間距離相對較近、一體化發展基礎較好的長三角地區建立聯合開發區,對上海來說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與江蘇省自上而下的推動有所不同,上海更多地依靠開發區、企業和區縣政府。上海和外省市聯合興辦開發區大致有3種聯動類型:一是上海市屬企業或地處上海的央企,與外地開發區共建園區,如寶鋼與海門合作建設寶鋼產業園、上海紡織集團與鹽城大豐市合作建設紡織產業園等。二是上海的開發區與外地開發區共建園區,如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海寧分區等。三是上海區縣政府在市外合作建設園區,如江蘇大豐楊浦共建產業園等。
上海推進聯合開發區建設有四個特點:第一,勢頭強勁。因為上海面臨包括土地和其他要素資源甚至是政策資源的瓶頸,需要尋求新的發展空間;第二,以大型國有企業為聯合開發區的主要推動和參與方。上海國有企業大多擁有資金、技術和品牌等方面的優勢,以及和外地政府對等談判的實力和能力,無需政府出面;第三,聯合開發區主要分布于距離上海300公里半徑以內地區,蘇北、浙江內地以及皖南地區被看好;第四,資源交換目的明顯。聯合開發區所在地區基本都擁有上海方面所需要的資源如土地、能源、產業配套能力等,合作雙方是資源互補的關系,這和蘇南蘇北之間帶有某種程度的區域合作型有所區別,受市場機制推動的特征更為明顯。
聯合開發區的意義和作用
在長三角地區,浙江“走出去”的資本名列全國各省區前列,但像江蘇、上海和安徽這樣基于頂層設計,以興辦聯合開發區這樣的形式推進轉型升級的做法還未成為普遍。整體而言,浙江在聯合開發區的建設方面,無論在規模、數量以及制度設計的規范性上都落后于上海、江蘇。
浙江的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在兩個維度上同時展開,其一是在產業維度上,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其二是在空間維度上,即“走出去”和“引進來”,“走出去”就是在面臨空間資源、市場資源、知識技術資源、勞動力資源瓶頸制約的情況下,以向外省市轉移產能和產業資源的方式拓展空間,形成產業鏈空間分布的多元化,以此來整合資源和開拓市場,“引進來”就是通過從外部引進本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稀缺資源或產業鏈相關環節,由此來帶動本地產業和企業競爭力提升。以興辦聯合開發區的方式來推動產業轉移和“招商引資”,由于在制度設計上一開始就和資源要素互換、產業集聚、區域創新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源集約利用緊密相關,具有更好的社會經濟效益。
浙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一直以產業轉移和企業跨區域發展為重要特征。本世紀初,浙江的民營企業就開始了“東擴西進”的跨區域發展進程,浙江已經是全國最大的資本輸出地。實踐證明,單純的對外轉移包括資本、生產環節在內的產業資源,并不能解決浙江的發展方式轉型問題,在民間資本流出相對較多的溫州地區,當地的產業轉型升級步履緩慢是導致經濟社會發展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單純地把產業資源的流動看做是企業微觀決策的問題,無論是希望留住本地企業的政府勸說努力,還是采取各種公關手段吸引地屬企業家的回歸,可能都是沒有把握這一系統工程的關鍵所在。事實上,產業資源的移動包括企業的各個生產環節的空間遷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產業鏈的空間離散化和資源要素的空間整合問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這些要素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差異在相當程度上和各地各級政府的政策導向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整合政府和企業的資源,以制度創新為手段,通過興辦聯合開發區來形成資源要素跨區域交換的平臺,打造產業鏈和產業集聚的空間載體,才能促使企業遷徙成為一個更具宏觀社會經濟價值的微觀行為。
加快聯合開發區發展
——考慮在省級層面上建立聯合開發區的領導、規劃、協調機構,推動和指導浙江聯合開發區的建設和協調工作,配套出臺有關聯合開發區的相關政策。同時,加快聯合開發區的規劃指導,可以結合省級產業轉型升級規劃一并進行,也可以制定專門的聯合開發區規劃。
——借鑒江蘇經驗,在浙江已有的山海協作工作中增加創辦聯合開發區的內容。考慮現有的省內企業跨區域遷徙的既有路徑,可在相關地市間建立若干個省級聯合開發區,如溫州和麗水、杭州和衢州等。
——規劃跨省聯合開發區建設。可以考慮在嘉興、湖州等地和上海合作建設聯合開發區,促進滬浙間的產業鏈跨區域布局,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在浙東和浙南地區可以結合發展海洋經濟,結合大項目的引進,與中央和外省市的大型國有企業興辦聯合開發區,鼓勵浙江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進行產業鏈合作。
——考慮到浙江既有的產業布局和開發區、高科技園區和產業集聚區的建設狀況,建議以園中園(區中園)的形式推進聯合開發區的建設,即依托已有開發區或產業集聚區來建設聯合開發區。
——聯合開發區實行政府引導、政企協同、市場主導、滾動發展的戰略。在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政府間合作框架下打造省際產業轉移合作區(即聯合開發區),為推行跨區域發展的浙商提供“抱團出海”的空間戰略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