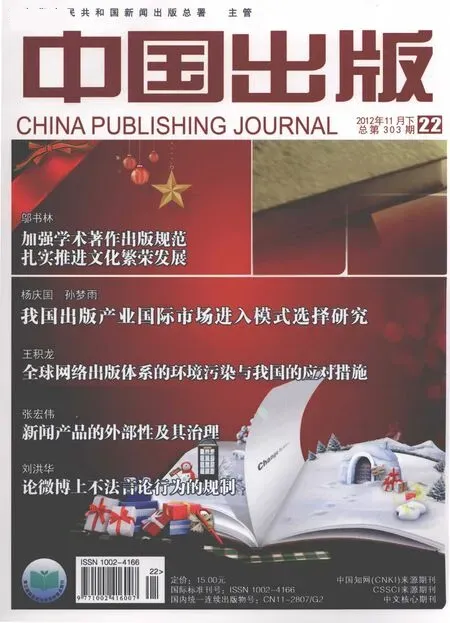上世紀20年代《現代評論》捍衛白話文的論辯*
文/沈 毅
自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舉起文學改良的大旗后,白話文的長處和優點很快為人們所接受,地位不斷鞏固,甚至徐世昌做總統時還下令廢止文言的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課本。[1]但反對白話文的勢力并沒有偃旗息鼓, 1925年魯迅感慨道,“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2]胡適也指出,“有幾個行省公然禁令白話文,學校也不取做白話文的學生”。[3]1927年10月,行將就木的北洋政府,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準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4]章士釗在青年時代鼓吹反清、討袁,但他的文化觀卻是保守的,對新文化運動抱有很大的偏見。20年代中期他做了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后,更是在《甲寅周刊》上頻頻撰文攻擊白話文。1927年掌權的國民黨所管轄的南方若干省份也上演過“取締白話”、“祭孔”等鬧劇。[5]面對著這種情況,主張新文學,反對舊文化的人士勇敢地站出來捍衛白話文,北京大學教授們的同人周刊《現代評論》就是當時一個重要的輿論陣地。
一、對于文言文是否利于繁榮文化和普及教育的辯論
章士釗在1925年8月的《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中稱,中國自古便是一個出版大國,歷代好書層出不窮,可惜白話文把大好形勢葬送了,計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余;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6]陳源(署名西瀅)在《現代評論》一則《閑話》中指出章士釗“實在可笑”,“好像只要大家廢止白話,高文典冊便可叱嗟而來似的。可是試問在《新青年》提倡白話的前十年里有過什么偉大的作品?……這二十年來,有過什么文言著作可以比得上吳稚暉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都是些白話作品 ?”[7]
10月章士釗在《評新文學運動》文中指責胡適的講演《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提出的舊文學為死文學,乃是煽惑之詞,章氏給“死文學”下的定義為:“凡死文學,必其跡象于今群渺不相習,僅少數人資為考古而探索之,廢興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歐人,于希臘拉丁之學為然”。[8]胡適在多種場合講過的白話文學的意義,核心思想是反對拘泥古人和死人,強調語言文字的時代性,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以充滿生命力的時代語言行文,以經過洗練的白話文進一步優化日常語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從而繁榮文化,提升民族素質。以僵死的文字做不出好文章,少數窮人科舉成名也無法改變整體上勞動階級沒文化的現實,更何況科舉恰恰是民族文化復興的一大障礙。章士釗罔顧事實,拼命為舊文學辯護,結果破綻百出。[9]
二、對于恐“白”癥的病因的辯論
唐擘黃(署名擘黃)在《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一文中有理有據地剖析了恐懼白話文的原因。文章認為,恐懼者不外乎出于兩個原因,一是自私,一是無知。關于自私,擘黃很贊成此前北大教授陶孟和的判斷,即白話文打破了那些以文言文為生的人的飯碗,使之不再奇貨可居了。擘黃引述陶孟和的話:“中國文字的通俗化,對于人民一方面是使他們得到一個新的發表意思的工具,幾千萬以先緘默的人如果學到三五百字就可以發表他們簡單的意思,而對于士的階級一方面正是剝奪了他們唯一的武器。他們所寶貴的奧秘完全為人所吐棄了。老先生們反對白話文不是無意識的,那正是他們最末次的奮斗,他們生命最終的光焰。”[10]
關于反對者提出的白話文詞匯量不夠用,章士釗稱各階層人都有各自的“白話”,農牧者雖人數多,但日常詞匯又少又簡單,若他們的語言寫入文章,豈不是白話文越做越干巴?擘黃反駁說,“因為今日的白話文,不過要使文字接近白話。實際上,農牧之白話文接近農牧之言,士大夫之白話文接近士大夫之言;并不是要人人的白話文,都做得與農牧的說話一樣。”如此說來,白話文的詞匯量,肯定要比文言還要豐富兩三倍。[11]
有人稱白話文文法呆板,擘黃認為該項指責是“對于白話文完全沒有經驗的人的話”。他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白話文的文法上變化,全局看,只有比文言多,不會比文言少”。有人稱白話文不古雅不簡潔,擘黃承認他本人也曾擔心白話文“冗贅”,但仔細考慮之后,卻不認同,“因為天下只有用不著東西才是冗贅的”。比如“夜夢不祥”改為“昨夜做一個不祥的夢”,雖添了幾個字,卻沒有一字是多余的,反而更加的明白和準確。[12]
有人稱文言、白話勢同水火,擘黃認為白話文不僅未曾刻意地回避一切文言文中的字句,實際上還吸取了好多大家都熟悉的字句。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區別并不在于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而在于代詞、關聯詞、助詞,一定程度上文言文是“之乎者也”之文,白話文是“的了么呢”之文。即便如此,白話文也在普遍地使用著“之”“也”“者”,也在使用著文言文中使用過的很多成語,如“相形見絀”“變本加厲”等。
擘黃講道理,重事實,語氣和緩,一些地方還聯系自己思想變化的實際來談感受。對反對者的“自私”和“無知”的總結到位而全面。對推廣白話文很有說服力。
三、關于因為不擅文言文而倡導白話文的辯論
《新青年》時代胡適擎起文學改良大旗的時候,有人妄猜胡適動機不純,說他不擅文言文才來鼓噪白話文的好處。《現代評論》的同人又一次運用辯論的武器。
陳源(署名西瀅)在一篇連載的《閑話》中下了一個斷語:“人們都說白話文好做,古文難做,我總覺得白話文比古文難了好幾倍。古文已經是垂死的老馬了。你騎它實在是用不著鞭策,騎了它也可以慢慢地走一兩里,可是它的精神早就沒有了。你如要行數百里,或是要跋涉數千里,那么你就不得不另覓坐騎。白話文是沙漠里的野馬。它的力量是極大的,只要你知道怎樣的駕馭它。可是現在有誰能真的駕馭它呢?”[13]
陳源認為,時代在進步,舊有的文言文表達形式嚴重地落伍了。陳源的切入點與新文化運動時又有所不同。新文化運動時強調喜歡白話文的人同樣寫得出來文言文,固然很有說服力,但也容易授人以柄,即寫好白話文要以古文為基礎。胡適曾給青年們開列了一長串的“必讀”國學書目,無意中也使守舊者有了新的口實。陳源認為,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的語言中“實在有許多很優美的達意表情的字句”,但長期以來“語”和“文”是分離的,好的白話沒有及時地化為文字,沒能推廣普及開來,“語”和“文”之間沒有形成良好的互動。所以難免落入“白話文不得不采用文言的字句”的尷尬。[14]陳源還大段地摘引了胡適在《〈老殘游記〉序》的話,證明浸潤于古書中是不利于寫出好白話文的。胡適、梁啟超的白話文比一般人寫得好,并不是“因為他們古書讀的很多”,而在于熟讀了白話的古典小說;而他們的白話文之所以還有種種瑕疵,恰恰是因為“深受古文的束縛”、“古書讀得很多”的緣故。[15]
陳源還強調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成就是與外國文學影響密不可分的。他說,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16]
四、結語
《現代評論》為了捍衛白話文的成就和地位而進行的宣傳和報道是很成功的。無論是組織起來的文章的數量,還是文章選擇的論述角度以及所提出的觀點和使用的材料,都是經得起質疑和推敲的,說明編輯者對問題的重視和籌劃宣傳所花費的心血。
提倡白話文,是《新青年》時代最重要的訴求之一。所以《現代評論》捍衛白話文地位的論辯,實質上就是旗幟鮮明地捍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和成就,也是中國處在文化變革和倒退十字路口之際以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同人一次集體發聲。推廣白話文的意義首先在于它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傳播載體和工具,方便生活,方便受眾,促進交流。白話文的使用有利于國人打開眼界,探尋真理,追趕時代和進步。提倡白話文是一場思想解放,同樣的,捍衛白話文也是新形勢下的思想解放。《新青年》時代提出的白話文原則,如不模仿古人、不無病呻吟、不要濫調套語等,實質上反映的是獨立的意識、老實的態度、科學的精神。《現代評論》再次向世人重申和強化了這一可貴的思想主張。
在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國度里要建設現代民主與法治社會,白話文的價值或許還包括喚醒人們的主體意識和尊嚴。包括《現代評論》在內的社會輿論界的呼吁在緩慢地發酵和生效,1930年年初,國民政府教部下令中小學厲行國語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書,而教部的文件用的就是白話。[17]1934年胡適給《大公報》撰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欣慰地指出了幾年來報紙上標點符號已經普遍使用,白話文章進一步增多。他稱贊福州的政府公文通用白話和標點符號。他也希望報紙能進一步“白”起來,新聞和電稿也用白話。[18]21世紀的今天,作為日常傳播載體的文言文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由于一些原因,某種意義上的現代“文言文”,即套話連篇、了無新意的文章還有回潮之勢。我們重溫白話文運動的歷史,或許會引發一些深層次的思考。
注釋:
[1]胡適.胡適文集(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79
[2]魯迅.魯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22
[3]胡適.胡適文集(12)[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0
[4]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5)[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44
[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5)[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315-317
[6]章士釗.章士釗全集(5)[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147
[7]《現代評論》,岳麓書社1999年影印版,第2卷,第37期,第13頁
[8]章士釗.章士釗全集(5)[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365
[9]郁達夫.郁達夫全集(10)[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126
[10]《現代評論》,第3卷,第54期,第4頁。
[11]《現代評論》,第3卷,第54期,第5頁。
[12]《現代評論》,第3卷,第54期,第6-7頁。
[13]《現代評論》,第3卷,第62期,第11頁。
[14]《現代評論》,第3卷,第62期,第9頁。
[15]錢玄同.錢玄同文集(3)[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298
[16]《現代評論》,第3卷,第63期,第12頁。
[17]胡適.胡適日記(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660
[18]胡適.胡適文集(12)[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