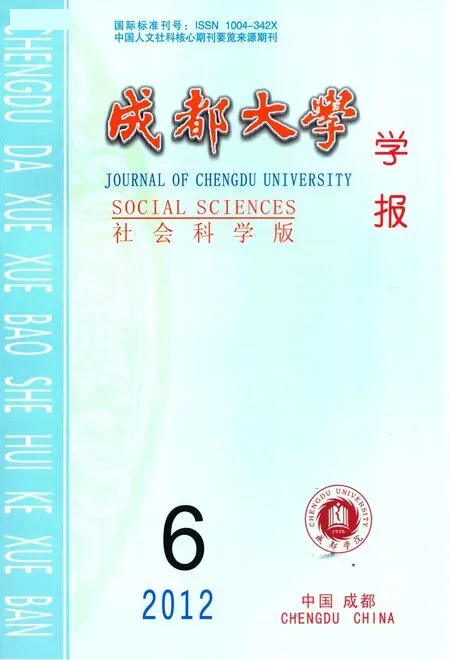宣泄與補償:虹影小說的“弒父”書寫及其心理機制
秦香麗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南京210093)
葉舒憲先生在《文學與治療》一書中將文學的治療分兩種:治療他人和治療自己。治療自己,即作家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將苦悶情緒在作品中宣泄出來,克服自我苦悶和心靈的錯亂,達到精神上的健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普魯斯特才說寫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廚川白村才認為文學是“苦悶的象征”,川端康成才將文學視為“拯救人生的大道”。“生命通過藝術(shù)而自救”,尼采的這句話道出了無數(shù)作家走向?qū)懽鞯牟欢▌t,那就是通過創(chuàng)作來緩解、消除自己的精神癥結(jié)。
“宣泄與補償”是文學治療最基本也最常用的功能,虹影的創(chuàng)作也印證了這一點。對她而言,內(nèi)在的心靈創(chuàng)傷(這里的創(chuàng)傷絕非一個,私生女身世、18歲時與歷史老師的不倫之戀,第一次的婚姻等均在其中,但究其根源則是“私生女”的身世。因此,本文的創(chuàng)傷特指“私生女”的身世創(chuàng)傷)是激起創(chuàng)作沖動的基本原因,而寫作則是醫(yī)治創(chuàng)傷的表意符號系統(tǒng)。作為一個“私生女”,她飽受邊緣身份之苦,以“原罪”之身應對這個世界,這使得她對自己的“父親”心生怨恨,拒絕承認他的存在。此種隱秘的心理體驗體現(xiàn)在小說中就是“弒父”,藉此宣泄自己的壓抑情緒;但是,“缺父”也使她產(chǎn)生了強烈的補償愿望,為此她迫切地需要父親或者父親的替代者來紓解自己的精神苦悶;歷經(jīng)幾段不徹底的“愛情”之后,在“尋父”與“弒父”的矛盾中掙扎的虹影終于認識到必須回到自身,審視自己才能真正獲救。
一
熟稔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大概不會否認此種觀點: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往往乃作家的宣泄之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文學創(chuàng)作的紓解苦悶與壓抑的功能,他說“《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旨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正是借助文學創(chuàng)作這種特殊的宣泄渠道,作家才得以保持心態(tài)平衡和身體健康。
自西方的“原罪說”誕生以來,很多哲學家如叔本華將人的災難追溯到“原罪”。“人之大孽,在其降生”,虹影一直強調(diào)這一點,但顯而易見,一開始這個“罪的源頭”的特指對象是父親(當然,也指向母親等人,就其本質(zhì)而言,還是父親),而不是自己。在《饑餓的女兒》中,“饑餓”有三重意蘊:食饑餓、性饑餓、精神饑餓。這三種饑餓中,筆者以為最重要的是“精神饑餓”[1]。在中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倫理國家,“私生女”的身份烙印注定虹影無法得到生父的愛,即便他是那么含辛茹苦地愛著她,也終為世情所挾持;養(yǎng)父對她的愛盡管也不乏倫理基質(zhì),但始終未能走進她的心……而哥哥姐姐、同學、社會上的人則以集體共謀的方式將她放逐,使她飽受“邊緣人”的切膚之痛。《饑餓的女兒》中,有這樣一段心理描寫:
“我無法忍受委屈,我總沒能力反抗;退讓,反使我情緒反應更強烈:我會很長時間不說話,一個人面對著墻壁,或是躲到一個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經(jīng)被每個人拋棄。我的自怨自艾會變成憤怒,刺刺冒火,心里轉(zhuǎn)著各種各樣報復的計劃,放火的打算,各種各樣無所顧忌的傷害仇人、結(jié)束自己的計劃。總之,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nèi)魏窝a救贖罪的機會。”[2]
由此可見,虹影心中的怨憤之情已有火山爆發(fā)之勢。可以這樣說,釋放缺乏父愛的痛苦,既是主觀情旨的使然,又是她寫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和動因。事實上,小說敘事和她的心理構(gòu)成了一個系統(tǒng):“弒父心理——作品表達——精神療傷”,這是一個由內(nèi)而外的心理宣泄的自足系統(tǒng)。
虹影小說有關(guān)“父”的宣泄敘事雖形態(tài)各異,但基本模式卻有章可循,大致呈現(xiàn)這樣的敘事流程:主人公(以女主人公為主)身陷“無父”的囹圄——主人公為了擺脫困境開始尋父并遭遇一段戀情——由于種種原因,愛情破滅,主人公“自食其果”,開始反省愛情,對“父親”的認知也隨著加深——主人公審視自己的隱秘心理,自省與懺悔,重新承認自己的父親。這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心理原型”敘事,換句話說,在虹影這里,寫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寫作,她通過寫作來宣泄自己的“無父”怨憤。
“弒父”最直接的體現(xiàn),就是否認父親的存在,將人物處理為“孤兒”。虹影小說中一個重要的人物譜系便是“孤兒”,小六(《孤兒小六》)、少年圓號手小羅和玉子(《綠袖子》)、筱月桂和余其揚(《上海王》)、于堇(《上海之死》)、蘭胡兒和加里(《上海魔術(shù)師》)等人無不是孤兒或半孤兒。即便主人公有著如常人般的家庭,虹影也刻意強調(diào)他們形同孤兒,甚至干脆宣稱這是一個“無父”的世界:
“三個父親,都負了我:生父為我付出沉重代價,卻只給我?guī)硇呷?養(yǎng)父忍下恥辱,細心照料我長大,但從未親近過我的心;歷史老師,我情人般的父親,只顧自己離去,把我當作一樁應該忘掉的艷遇。”
“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父親。”[3]
由此可見,在虹影這里,“父—女”構(gòu)成了一種典型的“對位空缺”。她用人物晦暗不明的身份及其艱難的生存際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父親”。但虹影又意識到她不可能否認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親,她也沒有選擇父親的權(quán)力:“你能對自己的父親有選擇嗎?包括他的習性長相愛好,絕對不能。退一萬步講,只要他不棄你而去,他就是一個殺人劊子手,他還是你的父親。”[4]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弒父”幾乎不太可能,合理而又安全的方式必須予以重視。這就涉及到“弒父”的第二種方式,“殘父”形象的刻畫。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發(fā)現(xiàn),虹影作品中幾乎沒有正常的父親形象,要么身體殘缺、要么父性殘疾:《饑餓的女兒》中養(yǎng)父雙目失明,不得不由母親承擔整個家庭的責任(這其實是以“母強父弱”的轉(zhuǎn)喻顯示父親的被閹割境遇)。大姐的生父是個流氓頭子,在外花天酒地,打跑老婆女兒。被捕后,經(jīng)他招供的人全被抓獲,他才得以茍延殘喘地活了下來。《孔雀的叫喊》中,柳璀的父親具有嚴重的人格缺陷,他蓄意冤枉玉通禪師和妓女紅蓮,誣陷他們?yōu)橥榉福脙蓚€冤魂謀取平步青云;在柳璀母親難產(chǎn),母女只能保存一個的兩難選擇時刻,他卻有違常理,毫不顧惜柳璀母親哀求的目光,斷然選擇了要孩子。《鴿子廣場》中的父親不但沒有對為了救他而委身他人的妻子表示絲毫的感激與愧疚,反而還不斷地打罵她。《康乃馨俱樂部》中的父親竟然強奸自己的親生女兒,還恬不知恥地說“我養(yǎng)女兒就是為了我喜歡,我養(yǎng)兒子就是為你媽高興”,完全喪失了父性……正是借助種種不稱職的父親形象,虹影才達到了精神弒父的目的。
從前面所總結(jié)的敘事流程可以看出,“男人”的出場實際上是一場預謀:通過愛情來“殺死”父親。無論對虹影還是對其筆下的女性而言,男人不過是“父親的替代者”。他們多以老師、長者、引路人與保護者的身份出現(xiàn),給女主人公父親般的溫暖,不管這種溫暖是否持久可靠。換言之,愛情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尋找父親,彌補女主人公的“缺父”遺憾。虹影坦言自己的“缺父情結(jié)”,她說:“我以后與男人的關(guān)系,全是建立在尋找一個父親的基礎上,包括我的婚姻”,“我非常尊敬我的養(yǎng)父,但因為我是私生女,他沒有給我一個完整的父愛。生父也是。他們都沒有給我一個完整的父親形象。所以,會有‘歷史老師’的出現(xiàn),會有我和前夫的結(jié)合。”[5]我們知道這些男人不管如何努力都是不能替代父親的位置的,他們的“被弒”也就在所難免。最典型的如《好兒女花》中,六妹自以為找到了一個可以依靠一生的男人,到頭來卻發(fā)現(xiàn)這是一場幻夢,不由得心生怨恨:
“……在我最后一次發(fā)現(xiàn)他與別的女人,比以前走得更近,仍在忽悠我時,我想對他吼叫,把積壓在心中的憤怒喊出來,我要告訴他,他這個父親是如何失去了尊嚴,如何親手把他這棵大樹,從我的土地上連根拔起,他有多殘忍、冷酷,我是多么恨他,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原諒他!”[6]
由此可見,虹影小說中的弒父書寫很大程度上脫胎于她的現(xiàn)實境遇。正是基于這種現(xiàn)實的苦悶,在拒認父親的存在之余,她設置了一系列的“弒父”場景。最典型的是《康乃馨俱樂部》,一群復仇女神組成俱樂部專門閹割男性生殖器。《好兒女花》中,幾個姐姐剁掉小唐的小拇指也極具隱喻性,同樣意味著對男性的閹割。根據(jù)弗洛伊德的“性欲說”,女性將曾經(jīng)艷羨的“生殖器”割去以后,陽物崇拜自然也就消失了,也即意味著對男性特別是父親的崇拜與依靠消失了。
“文學是人類獨有的符號創(chuàng)造的世界,它作為文化動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園,對于調(diào)節(jié)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消解內(nèi)心生活的障礙,維持身與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健康均衡關(guān)系,培育和滋養(yǎng)健全完滿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弗洛伊德稱作家為“神經(jīng)官能”者,他們和常人一樣,也有種種不得不排遣的壓抑,只是他們能夠從內(nèi)在的情感狀態(tài)出發(fā)經(jīng)由創(chuàng)作活動的中介,實現(xiàn)了以“文學對抗精神疾患,排遣、釋放”被壓抑的苦悶,達到了以文學治療心靈、走向健康的效果。而虹影正是通過“弒父”書寫,發(fā)泄掉現(xiàn)實生活中不能實現(xiàn)的隱秘愿望,才不走向死亡的幽谷。
二
寫作在宣泄的同時,也具有補償作用。弗洛伊德的“作家與白日夢”、“作品是改裝的夢”、“文學是性欲的升華”等文藝思想則是其體現(xiàn)。在他看來,作品無非是作家們經(jīng)過喬裝改扮、經(jīng)過“投射”和“文飾”過濾掩蓋的“未得滿足的”“欲望”的陳列。作為一群文學患者,作家需要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來維持他們的精神平衡。如同美學家阿恩海姆在《作為治療手段的藝術(shù)》中指出的:“將藝術(shù)作為一種治療救人(包括本人)的實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藝術(shù)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要求,源于困境之中人的需要。”[8]在《饑餓的女兒》中,虹影處于怎樣的精神狀態(tài)呢?
“母親從未在我的臉上親吻,父親也沒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沒有這種舉動。如果我在夢中被人親吻,我總會驚叫起來,我一定是太渴望這種身體語言的安撫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摟在懷里,哪怕輕輕拍拍我的背撫摸我的頭,我就會忘卻屈辱,但我的親人從未這樣對待過我。這里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會有撫摸、親吻、擁抱之類的事。沒有皮膚的接觸,他們好像無所謂,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憶在夢中被人親吻的滋味。”[9]
……
“他就是那樣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決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時,我禁不住又想著他,我不明白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對。我撫摸自己的臉,想象是他的手,順著嘴唇、脖頸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內(nèi)衣觸到自己的乳房,觸電般閃開,但又被吸了回去,繼續(xù)朝身體下探進,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傳遍全身,我閉上了眼睛。”[10]
……
此時此刻的虹影,基本上處于一種“病態(tài)”,如果找不到精神的出口,后果難以設想。她既是患者也是醫(yī)生,拯救她的只能是自己。在《饑餓的女兒》、《好兒女花》中至少呈現(xiàn)了兩種拯救方式:愛情和寫作(《好兒女花》中還提到六妹曾經(jīng)求助于心理咨詢,但這并不占主要方式,所以本文忽略不計)。在這里,我們重點考察的是寫作對虹影的精神補償作用。
“文藝家童年或青少年時期失去家庭的幸福時,這種缺失叫他們痛苦,但同時也激發(fā)著他們的創(chuàng)作沖動。這種創(chuàng)作沖動往往促使他們通過文藝創(chuàng)作沖動去努力換回一個逝去的世界,或重建一個新世界。也就是說,文藝家的缺失性體驗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動因。”[11]“缺失性體驗與創(chuàng)作動因的關(guān)系主要表現(xiàn)在缺失帶給人痛苦,但也喚起他們力圖重新得到缺失對象的頑強意志。”[12]“私生女”所經(jīng)歷的痛苦、失落、尷尬、掙扎等童年的缺失性體驗,給虹影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但她同時又意識到,她必須擁有一個父親。盡管,她自始至終沒有寫出一個完整的父親形象,但她一直渴望能找到他:
“我想我是天生的女權(quán)主義者,我從小就在尋找父親,我特別需要父親,我的生命里面不能沒有父親,但是實際上在現(xiàn)實世界里,我沒有得到父親的愛。包括我自己,比如說找男人也是找父親那樣的人。我覺得這就完結(jié)了我的一個情結(jié)。但也是我的一個失敗,我不可能找一個父親,在我童年的時候命運就注定了,我不可能有父親。但是在我的成長過程和寫作過程當中,我想找到這個人……”[13]
創(chuàng)作是一種“替代的滿足”,它成為心靈上需求的、不能滿足的一種意志“轉(zhuǎn)移”。對于虹影來說,她一直強調(diào)可以沒有婚姻的愛,并稱愛對她是至關(guān)緊要的,她要的就是這么一丁點東西。實際上,她需要通過愛情來轉(zhuǎn)移與彌補自己“父愛”的匱乏。一方面,虹影在小說中設置一種追尋結(jié)構(gòu),在時空的跨越中凸顯人物的身份悲劇和漂泊心態(tài);另一方面,虹影一再強調(diào)性愛的和諧,寫出性的奇妙,以狂歡敘事的手法在釋放壓抑的同時想象性地補償自己匱乏愛的靈魂。
“追尋結(jié)構(gòu)”是在時空的騰挪中尋找身份,也即尋找自己的父親。虹影寫作一個的最大母題是“創(chuàng)傷”,它有兩個子題:出逃和性愛。出逃是為了尋找愛,這種心理動機雖說可以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援引證據(jù),但它更多地得益于虹影的生命體驗。在《饑餓的女兒》、《阿難》、《綠袖子》等小說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從家庭到社會,還是從中國到外國,故事總依附在“追尋結(jié)構(gòu)”中。尋找父親,邂逅男人,弒殺男人或父親,再次尋找,這種無窮無盡的尋找,使得人物永遠呈現(xiàn)出一種“在路上”的漂泊心態(tài)。顯而易見,此種尋找絕大多數(shù)以失敗而告終,但畢竟在這個過程中,虹影找到了一系列父親的替代者,體會過父親之愛。
同樣的,不管是基于書寫策略的考慮,還是內(nèi)心真誠表達的需要,我們都能發(fā)掘出“性愛敘事”與補償心理的隱秘關(guān)系。趙毅橫在《唯一者虹影與她的神》中說“虹影描寫性的焦烈渴望,愛的沉醉升華,中國作家?guī)缀鯚o出其右”,并稱《K》乃“性愛主題之登峰造極”。林一直處于性的壓抑之中,無法紓解內(nèi)心的孤獨感。朱利安的出現(xiàn),讓她找到了一個擺脫庸常壓抑生活的突破口,在她的引導下,兩個人的性愛達到了完美的結(jié)合。文中大量直白的性場面的描寫,不過是女性渴望愛、實現(xiàn)自我的直接表露。正是在性描寫的狂歡化敘事中,虹影完成了情感表達的本能宣泄與補償。她的書寫證明的是女性也可以愛,可以在一次次的創(chuàng)傷之后,仍然擁有愛的能力,只有抓住愛,才能獲得拯救。在《阿難》中,“我”的丈夫艷情不斷,使“我”深受精神折磨,但她還是一如既往地去愛。小說如此寫道:
親愛的蘇菲霏,我活過來了,在男人把我扔掉以后,你看我還可以愛人,不在乎他愛不愛我……[14]
正是大不斷尋找愛的過程中,她們才擁有一種替代性的滿足。趙毅橫曾用“女性白日夢”來形容虹影的小說,確實如此,雖然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擁有父愛,但她可以在文學作品中寫出愛的極致,從而獲得一種象征性的滿足。
三
虹影小說關(guān)于“父”的敘事基本上遵循這樣一個模式:尋父——弒父——認父。而與之相應的創(chuàng)作心理卻遠非那么簡單,并不能將“宣泄”與“補償”視為某個階段的對應物。也不能說,通過這樣的寫作,藝術(shù)治療的目的就完全達到了。不過,總體而言,到了《好兒女花》時,虹影基本上抽離了對“父親”的仇恨,寫作心理發(fā)生了很大轉(zhuǎn)變。
在前期,虹影的寫作是心靈的大活躍、大解放,是情感的涌現(xiàn),是想象力的活躍。它強調(diào)情感的一瀉千里、激情澎湃、心力張揚、癲狂恣肆、震撼淋漓。它必須伴隨著音樂的喧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將心中的怨憤、不平之氣噴射出來,將痛苦傾力釋放……總之,她的寫作一味尊崇“感情的本能宣泄”,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盡管“私生女”是她一生的心理創(chuàng)傷,始終貫穿于寫作的各個階段,但在寫作治療的前期,她基本上將矛頭指向父親,并未審視自己。她用一種叛逆的反抗精神來對抗整個世界,她不僅恨自己的父親,也恨自己的母親。她離家出走,選擇流浪和寫詩,孤注一擲。“瘋狂約會,瘋狂寫作,瘋狂做愛”,唯有“瘋狂”、“驚世駭俗”才能概括該時期的寫作心理。
虹影一再聲稱:“《饑餓的女兒》只是我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它是一把可變幻的鑰匙,掌握得好,可打開我其他的作品。”[15]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她所有關(guān)于“父親”的敘事也必須回到這里來。這個追尋身份的悲劇故事是虹影小說中的父親敘事的底本,按照此底本演繹而成的其他小說都彌漫著一種怨憤情緒;到了《好兒女花》這里,虹影的“父親敘事”有了較大轉(zhuǎn)變。盡管我們?nèi)匀豢梢愿Q到一個壓抑靈魂的釋放欲望,但總體而言,狂飆式的宣泄不見了,其敘述也呈現(xiàn)出隱忍的風格。她第一次將苦難的根源指向自己,剖析自己的“缺父情結(jié)”,并對“既往之我”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作為自我治療的寫作,是否實現(xiàn)它的初衷,能否讓作家走出精神的困境,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的寫作發(fā)生了什么變化。眾所周知,成功的心理治療,必然是一個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的過程。治療師所扮演的不過是一個引導者的角色,他誘導患者傾訴自己的故事,重組自己的故事。我們會注意到故事的底本基本未變,變的只是講述的角度和看待故事的方式。但恰恰因為這“角度”的轉(zhuǎn)換,患者才有了某種重生的感覺。源于文學治療的特殊性,特別是治療者和被治療者的合一性,注定了寫作既是一個涅槃重生的過程,也是一個反省自我的過程,只有完成這個過程,治療才算完成。
以續(xù)篇面目出現(xiàn)的《好兒女花》,主旨就是“回家”,其隱現(xiàn)的前提就是回到“女兒”的位置,重新審視既往的一切,與“父親”和解。筆者將該部作品視為重建記憶、重建自我的努力,是“饑餓的女兒”歸家的一次嘗試。從彌補缺失到承認缺失,從“尋父”到“弒父”最終到“認父”,虹影借助小說完成了自己的歸家之旅。盡管,小說的主線是母親的故事,但里面關(guān)于“父”的敘事仍占了相當比例。仍然是那個帶給她生命的生父,其形象卻不再蒼白猥瑣,一再強調(diào)他對女兒的想愛又不能愛的孤苦與無奈。正是基于這樣的寫作心態(tài),虹影與生父和解了:
“生父與我在夢里和解了,他像一個嚴父那樣打我,以此來處罰我對他對母親做的所有不是。生前我從未叫過他,我恨他。可是在夢里,在我陷于絕望之中,我走向他的懷抱。”[16]
對“父親缺失”的認知與對“愛情”的認知原本是一對雙生兒。虹影是抱著“尋找父親”的心態(tài)去尋找“男朋友”、“丈夫”的。《饑餓的女兒》中的六六在得不到父愛,甚至得不到任何來自親人的關(guān)愛時,開始尋找一種“叛逆的快意”,她總想“把自己交給一個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當作一件禮物拱手獻出”。而在《好兒女花》中,在寫到六妹和前夫的愛情時,虹影的文字客觀冷靜,不帶有任何怨恨的筆調(diào),而是將筆鋒指向了自己的“原罪”——私生女。它拋卻了《饑餓的女兒》中的那種“這個世界本來沒有父親”的“弒父”心態(tài),并正確認識到“親情之愛”與“愛情之愛”的區(qū)別,“只想找個愛人,而不是一個父親”,以一個正常女人的心態(tài)開始了新的婚姻,并有了自己的女兒。
就連對背叛自己的“丈夫”與小姐姐,虹影也有了比較冷靜的態(tài)度。“丈夫”和“小姐姐”,都是她至親的人,對她的打擊可想而知。但在處理這一情節(jié)時,虹影擯棄了過去那樣的“怨毒”情緒,選擇了理性的節(jié)制,既同情小姐姐將她視為受害者,又怕小姐姐報復“小唐”,處處為他著想。更難能可貴的是,虹影將這場悲劇歸咎于自己:
“我、小姐姐和他,只是我們?nèi)擞鲈谝黄穑瘎【桶l(fā)生了,我們在不該遇見的地方時間遇見了。要說有罪,那就是我,我是罪的源頭。”[17]
此時此刻的虹影,帶有深刻的自省與自審,對自我的拷問已經(jīng)超出了此前“懺悔”的意味,走出了“缺父”記憶的沉疴,用最真實的自我贏得了對自己的尊重,達到了自我療治的目的。正因為如此,在《好兒女花》中,虹影的小說第一次出現(xiàn)了家人團聚、和睦融融的場景:兄弟姐妹親密無間,他們相約做一道父母生前做過的菜,像正常的家人一樣團聚在一起吃著晚飯。這一場景告訴我們,“饑餓的女兒”終于回家了。
結(jié)語
對于虹影而言,其獨特的成長經(jīng)歷,那些充滿了痛苦和矛盾的生命記憶,那些邊緣人晦暗不清的慘痛的生命表象,迫使她一次次追問,她的痛苦來自哪里?當“私生女”成為一個堅定而又不可抗拒的答案時,虹影認識到自己帶著“原罪”而來,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不得解脫。在這種情況下的虹影和許多作家一樣,選擇了“自救”。“誰也無法剝奪我最后一個選擇——寫作或自殺”[18],寫作承擔起靈魂救贖的重任,她說,“我覺得自己曾經(jīng)被毀滅過,曾經(jīng)走到了絕境,曾經(jīng)進入了死城,但后來又重生了。我確實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這真是個奇跡……”[19],“我把這些不堪回首的過去寫下來,就是要把自己送上審判臺,進行一次尋找自我救贖和懺悔之途!因為一切的悲劇因緣都在于我,在于我的私生女身份,在于我隱藏在血脈深處的原罪!反過來說,把這些命運的殘酷寫出來,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解脫,我放下了,釋懷了。我坦然,淡然。”[20]
她的寫作始終繞不開“父親”,正是通過“父”的敘事,虹影才完成了對自己的治療,以及重返家園的路。
[1]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兩種“饑餓”不重要,而是因為“食饑餓”在虹影的生命歷程中是間接而又短暫的,而“性饑餓”是“精神饑餓”的衍生物。從這個意義上講,“精神饑餓”才是最根本的。
[2][3][9][10]虹影.饑餓的女兒[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33,254,108 -109,113.
[4][6][16][17]虹影.好兒女花[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89,89,185,223.
[5]虹影.今天,我要把自己送上審判臺[EB/01].信報獨家專訪披露《好兒女花》背后的心路歷程.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9 -10/30/content_18096562.htm.
[6]虹影.好兒女花[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7]黑格爾.朱光潛譯.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8]阿恩海姆.作為治療手段的藝術(shù)[A].郭小平等譯.藝術(shù)心理學新論[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1]張佐邦.文藝心理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2]童慶炳,程正民主編.文藝心理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3]王紅旗.難在道“女人”之所未能道[A].愛與夢的講述:著名作家心靈對話[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4]虹影.阿難[M].北京:知識出版社,2003.
[15]止庵.關(guān)于海外文學,泰比特測試,以及異國愛情的對話——虹影與止庵對談錄[J].作家,2001,(12).
[18]虹影.饑餓的女兒(附錄)[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19]孫康誼.虹影在山上,女子有行(附錄)[M].北京:知識出版社,2003.
[20]信報獨家專訪披露<好兒女花>背后的心路歷程[EB/01].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9 - 10/30/content_180965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