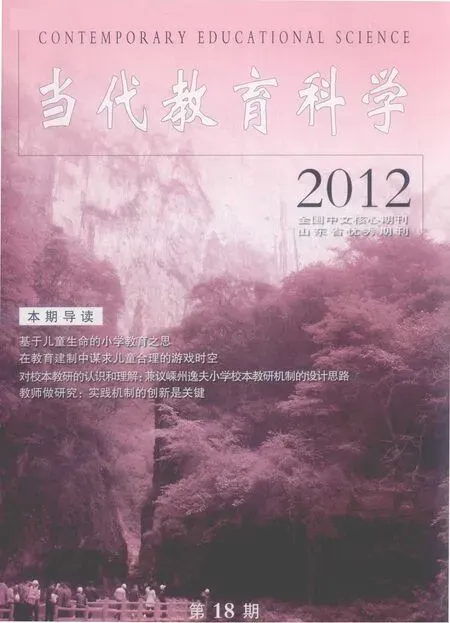教師課程創生的角色踐行意義及其實現*
●殷 潔
作為整個當代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教師角色”的話語反思和內涵開掘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各種觀點競相提出,畢竟“角色本身對于教師個人生命發展的意義是重要因素,它直接影響著教師角色踐行的水平、角色興趣、角色動機以及角色創新”[1]。然而,當我們濃墨重彩于教師超越自身角色內涵來回應教育的挑戰和機遇的契機時,整飭和刷新著教師作為 “典范”、“楷模”、“權威”的理想角色卻極有可能滋長著某種緣木求魚的危險,對“理想的教師”和“教師的理想”道學式的審視和說教并不能越俎代庖,教師對投身現實與實踐的角色能否真正有所擔當并踐行,必然取決于——至少在充盈著新奇與變化的課程世界中如此——有充分的機會去對那些聲稱美輪美奐角色期望的人提出的各種課程方案進行認知、理解、反思、建構,并最后加以體驗和創新。也就是說,教師角色的豐盈與踐行,必然要求教師在不斷的課程批判反思和與實踐情境交互作用中,即課程創生中進行,課程創生是實現教師角色轉變和踐行的重要通道。
一、教師課程創生:基于實踐立場的教師與課程的多維關系
課程創生是教師在整個課程運作 (包括從開發、實施到評價的整個過程)中通過批判反思而實現的對課程的持續、主動建構[2],課程創生是教師實現角色自我和專業發展的存在世界。依循以上定義詮釋的軌跡,或實踐、或反思、或生成、或建構,兼有持續的歷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教師課程創生即教師依托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文化積淀,以學校的實際發展和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基礎,通過不斷地批判反思、主動地、創造性地在課程開發、實施、評價過程中建構適合學生發展的課程實踐。教師課程創生不僅包含著一個多元、開放和動態建構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實踐的課程立場,彰顯著教師與課程關系的多種角度:首先,“教師課程創生”體現了課程的多元化與層次性。按照美國學者古德萊德關于課程不同層次的劃分,課程可分為理想的課程、正式的課程、感知的課程、操作的課程、經驗的課程。這其中,盡管課程實踐情境具有不確定性,不同教師與不同學生之間也具有差異性,但正式的或官方的以及書寫在教科書中的文本式課程在傳統觀念下卻具有絕對的權威,其它課程形態常常被忽視。而“教師課程創生”這一命題則強調教師在具體的情境中自主建構全新的不同于計劃形態的課程,無需完全服從、復制官方的正式課程,教師層面發展而來的感知、操作課程得到認可與賦予;其次,教師和學生都是建構課程的主體。教師對課程的創生會把教師的個人知識、人生觀念、思維方式乃至社會閱歷放入到課程思維框架中去,自覺地、深入地對課程進行改編、拓展、補充或整合,并在課程之中通過多元方式引導學生與被稱為課程的東西進行對話和反思,努力建立一種合理的可能生活方式,從而確立教師和學生應有的生命立場、主體立場。最后,教師課程創生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個結果,在創生課程中,診斷、實踐、反思、完善課程存在的問題,關照與共構適合學生發展的課程實踐。
二、教師課程創生的角色踐行意義
(一)改造作為“日常教學生活”直接延伸的固有“角色習性”
當代課程改革的歷史反復呈現著一種獨特的“景象”:課程改革不斷地推陳出新與持續展開,而教學實踐則相對穩定守成,作為“日常教學生活”直接延伸的教師角色亦在這種穩定守成中因循成習。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的“習性理論”所言,實踐者基于日常生活的社會行動乃是 “來自于社會制度,又寄居在身體之中的”[3]習性。“習性”在主體的行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是一種持久的、可轉化的潛在行為系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像‘恰當的意見’‘適得其所’,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過程,就這樣,性情傾向和位置彼此適應,‘游戲感’和游戲互相契合”[4]。從而告訴我們,作為日常教學生活主體的教師往往是依據其長期的日常生活、教育經驗以及教學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角色認識圖式(本文稱之為“角色習性”)來理解和展開角色實踐活動的,教師在角色習性的內在引導與自發作用下習慣并重復建構著特定的角色狀態和角色模式。角色習性一旦占據主導地位,人們往往不再是“通過對新問題的自覺的和創造性的解決而修正或突破原有的規則和模式,而是理所當然地把各種新問題和新情況都納入給定的歸類模式或一般圖式中。結果,日常生活很少表現出創新,而是像春夏秋冬,寒暑冷暖一樣在同一水平上循環往復”[5]。
循環往復意味著固化,而教學改革需要推陳出新,教學實踐需要嘗試省思,教師角色在知識信息的更新、教育技術的跟進、學習方式改變的語境下需要傳承發展。教師課程創新為教師角色的踐行打開了心智和行動之門,把教師從一般性的技術成長和角色習性的規訓中解放出來,將教師專業素養中的教師主體性和創造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喚起教師的內在精神,促使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從他人的視角和自我的反觀,去檢視不同課程及課程不同層面所顯示的理論、思想、行動中的要義,去挖掘尚未被注視到的潛在課程觀念,以及它們對教學、對教師角色所產生的影響,從而推動教師對自己的日常教學活動進行深入感受、自我反思、批判創新,超越固有經驗的限制和束縛,不斷成就教師角色的成長和豐富,達到角色坐標的彰顯和價值的弘揚。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才能更智慧的生活,獲得課程發展和角色踐行的主動權,而不是繼續成為他人思想的被動傳聲器,在不斷地批判反思和與實踐情境交互作用的同時,厘定與廓清自身的角色內涵和發展軌跡,在主動地課程創造中自覺、自律的找出用來表達、改造“角色習性”的預設機制,實現教師角色的認同與轉型。
(二)縮小“自我與他者”規范和期望的角色距離
1959年,美國社會學家E·戈夫曼通過觀察游樂場里電動旋轉木馬游戲發現,只有三四歲的兒童對此游戲異常認真,能夠真正“進入角色”。由此,他認為,在個人與其承擔的角色之間,在一個人所做的與其本性之間存在一道裂痕,即“角色距離”。簡單地說,人們對某一個角色的期待與個體扮演這一角色的表現之間往往存在差距,個人在某種角色上是否能積極的發揮作用取決于他與該角色相適應的程度,只有當某種角色不僅適合一個人承擔,而且對他具有某種“挑戰”意味時,這個人才可能充分施展其才能,達到“進入角色”的程度。對現代教師而言,現代教育觀念和教育意識在客觀上要求教師角色有更豐富的內容,“教育者”、“學習者”、“研究者”……諸如此類,教師角色話語的紛繁和多元綜合地呈現著教師自己、學生家長、學校管理者、學生和其他社會成員的殷殷期待,“角色叢”的身份使教師角色承載的“枷鎖”的厚重遠甚于“光環”的閃亮,因為并不是每一個處在教師崗位上的教師都能如超人般“完美圣化”,都能滿足角色期待。之于教師,自身的素質、能力、水平與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之間總會存在差異。
角色差距普遍存在,卻不意味著可以任其擴展拉大。扮演多元角色的教師在課程行動時,課程創生能夠闡釋課程的多種意義,使課程由教師的獨自言語轉向眾聲參與,從隱匿個體的套裝課程轉向宣揚主體的建構課程,教師在其中得以突破觀念固有的狹隘和束縛,有意識地去判斷和選擇更適切的課程決策和教學實踐活動,而且在課程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再滿足于忠實地傳遞設計者和決策者的意圖,而是通過積極的參與和多元主體的對話賦予課程新的理解、解釋和再創造。與此同時,教師課程創生也嬗變著教師的角色:教師以開發和創造的實踐者身份甚至是專業的研究者的身份進入課程領域,教師由過去課程活動中單純性的“工具”上升為具有專業自主權的真正主體。所以說,教師課程創生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尋索,它使教師能夠在課程中“自在”、“自為”,能夠在課程建構中認識自己,創造一個有系統的自我更新基礎,發掘潛在的能力,藉此縮短“自我與他者”不同期待造成的角色距離。
三、教師課程創生的角色踐行策略
(一)實踐反思中提升角色自覺意識
每個人都會用以往的經驗和意識來觀看世界,當他擁有了某種特定的文化,往往就會有其文化模式下固有的角色和思維方式。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課程運作模式孕育的是課程的忠實執行者,“教師應該、也可能施展才華的領域轉交出去了,更重要的是‘執行者’角色的長期認同,壓抑了教師創造的愿望”[6],相比之下,教師課程創生賦予了教師新的角色——反思型建構者,并主張教師的課程能力在于主體能于復雜課程情境中以選擇、判斷、反思、審察而獲得實踐性智慧,此間,教師的專業形象是反思性實踐家,其課程能力不是停留在制度化的科學技術、理論知識、合理技能層面,而是在融合這些知識的過程中,能對問題情境作出反思和合理判斷,進而有效建構課程。也就是說,“通過對實踐的反思,思想的碰撞,催生出一系列解決問題的策略”[7],并以此為基礎促成教師角色在自身層面上自然而然的拓展和上揚,喚醒教師角色自覺的能動意識。畢竟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有自覺能動的意識,能夠不斷地認識客觀世界,根據發展的需要改造客觀世界。同樣的道理,正是有了對實踐的深入反思,教師在習以為常的課程實踐中才能不被“角色習性”所左右,經常審視課程及其展現的角色行為,認識到課程本身和所處角色存在的問題,才能噴薄出發自內心的聲音,產生“自我控制、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在對課程理論、課程意義、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與資源的反思中實現角色自覺意識的萌發和提升。這樣,伴隨實踐反思的課程創生即充當了修正自身舊有的角色意識的新意識。
(二)師生互動中引發角色認同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必然有其社會屬性。這種屬性最終決定了每個人的社會角色并由此產生“我是某類人”的感覺。這種感覺在社會心理學當中被稱為“角色認同”。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特定社會位置的意識和認可。教師作為一種古老職業的特殊實踐主體,自然也存在著對自己作為專業人員身份的辨識和確認、對社會界定的教師內涵的認知和體驗。不過,這種辨識和確認主要是通過向他人發出暗示,以確認某一角色實現的。這樣,互動就成了角色領會和角色執行過程的連接點。教師要驗證角色認同的有效性,要縮短角色距離,就必須投入到角色當中,與課程中的人、事、物真誠互動,特別是學生。因為“行動的社會意義不是由社會賦予的,而是取決于行動者本身,行動者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不但給自己的行動賦予了意義,也給他人的行動賦予了意義”[8]。就如教師課程創生的過程,強調師生皆為建構新經驗的主體,在具體的課程實踐情境中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闡釋、建構著課程,進而使課程突破其預定目標和計劃的限制,走向創生和開放的廣闊天地,使同一學科、同一內容在不同師生的互動和參與下呈現出多樣化和個性化的色彩。教師從知識的權威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者、支持者、學習的合作者與伙伴以及學生意義建構的促進者;而學生要自由地表達見解、提出疑問,進行討論,教師在學生的探究中,是學習情景的創設者、學習活動的支持者;學生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地學習者,意義建構的主動者。這些角色的轉變,使教師由舞臺的主角變成了幕后的導演,使學生成為一個需要點燃的火種,他們在交流、共享、對話、磋商的和諧互動中悄悄進入角色,實現著自身角色的認同。
(三)使能社團創設中共構創生愿景
在很大程度上,教師角色的踐行是一個立體而多元的復雜過程。課程創生情境中,教師所攜帶的角色既在保持自身的傳承性,也在交互主體的行動中進行著轉換,磋商出新的意義,生成新的角色樣貌。因此,教師的課程創生不僅囿于看到并揭示教師角色的多元與差異,還需要在批判、反思的同時創設使能社團,從自己所屬的群體那里獲得角色踐行的支撐點和直接推動力。就像麥克爾·富蘭所說的那樣:“如果你想……人的信念和行為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持久的、能夠對他人產生示范作用的變化,你需要在他們周圍創造一個社團;在這個社團中,新的信念可以得到貫徹實施、自由表達、培育成長”[9]。一方面,使能社團追求于成員的交互論述中最大限度地群體共享和集體推進。在使能社團里,個人與團體不是對立的兩方,在肯定個人能力的同時,參與的個體也會共同生成充滿相關意義的團體網絡。不同的課程觀念在此能夠得以容納和擴展,通過與環境、他人的反思性交往作用,關照每一個社團成員在異質化的創生共享中生成 “自我探索”、“結交伙伴”、“建構世界”的意義性課程實踐,旨在使教師主體間在生活、生命、人性、價值、倫理等層面實現精神共生、資源共享、課程共建,促進彼此共同的成長;另一方面,使能社團貴在“使能”,“使”參與者在課程創生的過程中彼此更有“能力”,更添“能量”。使能社團所蘊含的豐厚的價值能夠轉變成課程創生參與者討論事物的潛在能量,形成一個多維的課程生存空間,以超越的姿態,對共有的課程內涵自動生成富有想象的內在角色轉化,并通過創生成員間的支持、陪伴、分享或批判實現“賦量增能”,共享群體創生課程成就,以此擴展到以共同愿景為目標的課程創生系統。
[1]張愛琴,謝利民.教師角色定位的本質透視[J].教育評論,2002,(5).
[2]李小紅.論教師的課程創生[D].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
[3][4]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5]依俊卿.文化哲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郭良菁.邁向養成自主探究與反思的實踐者的教師教育[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1999.
[7]虞永平.論幼兒園課程審議[J].學前教育研究.2005,(1).
[8]錢撲.教育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9]麥克爾·富蘭.變革的力量——深度變革[M].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加拿大多倫多國際學院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