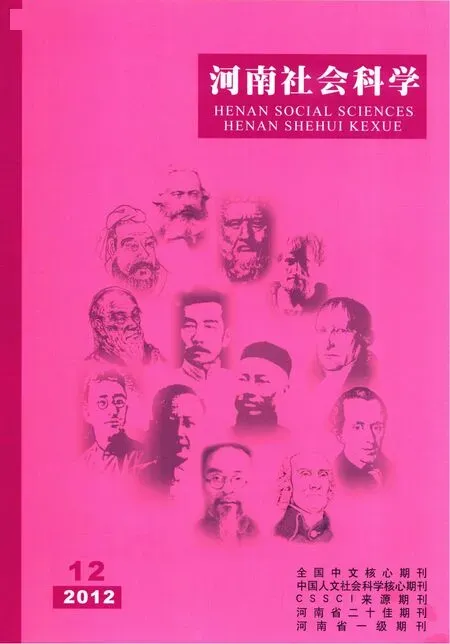“仁”與“敬畏”——儒家與施韋澤的道德生命觀比較研究
崔婷婷,李效民
(1.南京中醫藥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部,江蘇 南京 210046;2.濟寧學院,山東 濟寧 273155)
一、引言
“仁”與“敬畏”分別是儒家與施韋澤道德生命觀中至關重要的道德原則。儒家踐行“仁”,主張人克服自身種種感性欲望的誘惑,純化道德動機,從而契合“天道”與“天命”,達到與宇宙萬物為一體的境界。施韋澤主張敬畏包含動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要求人類不僅不要迫害其他物種生命,還要幫助它們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因為人類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著人道、愛和同情。儒家與施韋澤道德生命觀異同點在哪里?其對現代人的啟示何在?筆者將在本文逐一探討。
二、儒家與施韋澤道德生命觀的概念透視
儒家學說里最核心的觀念即為“仁”字,儒家認為“仁”重于生命。儒家道德生命觀的主要特點是:其一,儒家認為人才是天地間最杰出、最偉大的生物。儒家一直持有重生、貴生的道德思想,十分強調人在天地間的高貴地位。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主張“知天盡性”[1]。其二,儒家更關注人的現實生命,反對作無謂的犧牲。孔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1]儒家提倡對生命和死亡持負責任的態度,不要隨意去冒險和招禍惹災。其三,儒家認為比生命更為貴重的是仁義道德。“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1]。在利害沖突面前,“仁”是君子對生死的取舍標準,仁人志士是不會舍棄道德而茍且偷生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2]朱熹也說:“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于死;不當死而死,義不在于不死:無往而非義也。”[3]其四,儒家提出“以道制欲”,試圖擺脫物欲對道德生命的遮蔽,防止生命被異化。儒家主張人們通過勞動自食其力,即使生活貧困,也要做到“安貧樂道”。當然儒家也并不排斥人們獲取生存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并不排斥富有本身,反對的是人們過度放縱自己的物質欲望,毫無節制地索取和享樂,以至于見利忘義、損人利己而不顧仁義道德。其五,泛愛眾而親仁。儒家告訴我們,人不但要愛惜自己的生命,還要愛惜他人的生命,推己及人,具有“泛愛眾”的思想。孔子雖然講究禮數,強調男女授受不親,但如果“仁”的外在表現形式“禮”同人的生命安全發生沖突,那么人就要以挽救生命為先而不必過多考慮“禮”了。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2]孔子“泛愛眾”思想還表現在他極力反對戰爭的思想上。衛靈公曾經向孔子請教關于用兵打仗的方法,孔子這樣回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學也。”[1]這表明孔子是不希望看到戰爭中生命被血腥屠殺的場面的,因此他沒有正面回答衛靈公的問題。
與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生命觀不同的是,施韋澤道德生命觀提出“敬畏”的主張。“敬畏”是施韋澤對待生命的基本態度和根本立場,“敬畏”一詞不僅表達了施韋澤對生命的“崇敬”之情,更體現了他內心深處對生命的原始“畏懼”。伴隨現代生物科技的發展,人們對生命的神秘感正在消失,當代人更多強調的是生命的價值感和如何超越之,而施韋澤卻獨樹一幟地認為社會越是發展,人們越要首先保持對生命本身的原始敬畏,這才是生命道德的根本。具體來說,施韋澤敬畏生命區別于以往倫理學的主要特征是:其一,敬畏生命的“生命”不僅指人的生命,還包含了所有其他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施韋澤對生命物質性的存在保持著最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他看來,生命存在本身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還據此推論,既然人的生命是神圣的,那么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的生命也應該受到尊重,而且應該和人的生命同等敬重才是合理的。把倫理的范圍擴展到所有動植物,是施韋澤倫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其二,敬畏生命的道德主體是人,人是否敬畏生命是其是否道德的依據。施韋澤也意識到敬畏所有生命是較高的道德要求,這項工作只能由人來完成,人有道德的自覺性,能主動去敬畏生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整齊劃一的思想,其中能否產生敬畏之情正好可以成為區分人是否道德的尺度。施韋澤說:“善即是保存生命和促進生命,使得可發展的生命實現最高的價值。惡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和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和絕對的倫理原理。”[4]在施韋澤這里沒有相對倫理,是否敬畏生命被視為人性善惡的分水嶺。其三,敬畏生命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更好地敬畏人類生命。施韋澤提出敬畏生命,始終堅持敬畏所有生命。施韋澤并不是為了敬畏所有生命而去敬畏,而是他認為人類要想形成敬畏生命的道德理念,就必須學會或者是先懂得敬畏動植物的生命,這是人類發展到敬畏自己生命的一個前提或是一個過程的連續。他認為人類如果隨意屠殺動物、砍伐植物,喪失的將是人類的同情和愛的能力,人們對看似低級生命的輕視會傳染到對高級生命的冷漠。其四,敬畏生命作為人類最重要的道德理念,其動機重于結果。施韋澤也看到,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人對人的戰爭還是人對自然界的掠奪,可以說,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如果一味要求人們追求敬畏生命的行為效果,現實的遭遇往往會使人們產生道德悲觀主義,甚至會懷疑敬畏生命倫理主張的可行性。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提醒人們首先要具有敬畏生命的意愿,要保持道德上的樂觀主義,可以暫時把有關行為效果的問題擱置一邊。
由上述論述可見,儒家和施韋澤的道德生命觀都主張人們愛惜生命,反對無謂犧牲。不同的是,儒家踐“仁”是愛有等差的,對人生命的重視和關愛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儒家生命觀里,道德是外在于生命且高于生命本身的,儒家宣揚的道德生命觀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鼓勵人們為實現成“仁”可以犧牲自我生命。而施韋澤的生命觀對于人和動植物的生命是一視同仁的,他更看重對自然生命的原始敬畏,在他那里生命與道德也是融為一體的。
三、對儒家與施韋澤道德生命觀的理論基礎之探析及評價
筆者認為,儒家以“踐仁”為特點的道德生命觀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之上的。首先,儒家思想里“天”是個本源性的概念,自然萬物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都來源于天,人珍視生命是來自形而上的天的命令,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正當的。其次,人與萬物共處天地一體之內,它們必然彼此聯系,互相依靠,遵循共同的自然規律。儒家認為“天人合一”的關鍵還在于“天人同道”,“天道”就是宇宙間必然和普遍的規律,“仁”是“天道”的顯現,人只有遵循它,愛惜萬物生命,與萬物和平相處,才會實現天地間的和諧。朱熹說:“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為心。如此看來天地全是一團生意,覆載萬物,人若愛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3]再次,人和萬物都有生,但體現為各自不同的“性”。“性”代表著生命的展開方向,萬物憑借各自不同的本性,形成豐富多彩的萬千世界。人踐行“仁”去保護生命就是在“知性、盡性”,主動與“天”合。牟宗三曾說:“仁以感通為性,以潤物為用。”[5]人給予人和萬物以仁愛,人自己的精神層面也逐漸擴大,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人與天地萬物也就融為一體。
與儒家相比,施韋澤“敬畏生命”的理論基礎則是生命之間的普遍聯系。人的生存發展需要依賴與其他生命乃至是整個世界的和平、友善相處。施韋澤認識到我們與其他生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生命存在于彼此的聯結之中,不是可以隨意分割的。人具有道德自覺性,就應該認識到不僅是人,其他生物也都是一種目的性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內在價值,人只有懂得這一點才會更好地學會尊重其他生命,更好地與它們和平共處。施韋澤指出,人與自然沒有尖銳的對立,人的生命依賴于其他生命,人要始終努力成為自覺和慈善的人,努力揚棄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盡力捍衛人道和解救痛苦的生命。“誰習慣隨便把哪種生命看成是沒有價值的,他也會陷于認為人自身的生命也是沒有價值的危險之中”[4]。施韋澤批評近代歐洲世界觀的根本錯誤就在于沒有真正認識到世界、人生和倫理的內在聯系,因此使得這個世界變成殘害無辜生命的血腥戰場。其實,在施韋澤看來,這個世界原本就是一個統一的世界,和諧的世界需要不同種類的生命的休戚與共而不是彼此傷害。
由此可見,儒家和施韋澤都認識到人類的生存和生存質量依賴于人類和其他生命之間的關系以及人類所生存的環境。人與自然萬物的相互依靠和休戚與共,正是施韋澤和儒家生命道德觀的共同的理論基礎。
儒家與施韋澤道德觀都探討了生命的本質和意義。首先,儒家關注生命的道德屬性,關注人的精神領域和內心世界,認為人對于生命的道德責任在于珍視生命、踐行仁義,當自然生命與精神生命發生沖突時,舍棄前者才是道德的。而施韋澤是把生命作為倫理關懷的對象,人的道德責任本身就在于維護生命、敬畏生命,舍棄生命自然就是不道德的。其次,儒家生命觀主要關注人自身的生命,其他生命的生存利益最終還是次于人的生存利益的。在儒家那里,道德是高于自然生命的,于是人既然因為踐行“仁”可以舍棄自己的生命,就更容易因為道德的需要而舍棄其他生物的生命。而施韋澤卻要求關注一切生命,認為人不能忽視動植物的生命,因為如果人連動植物的生命都關注,那么人就會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反之,人對其他生命一味輕視,最后也會輕視自己的生命。再次,無論是儒家還是施韋澤,兩種不同文化所孕育的生命觀的共同特征在于都彰顯了人類無私高尚的道德情懷。儒家對生命的道德思考是純粹的,是不夾帶任何自然欲望和利害考慮的,一切以仁義為先凸顯了儒家生命觀的神圣。而施韋澤同樣具備道德的純粹性,在他那里,是否敬畏生命已經成為人類善惡的分水嶺,同時他還指出人對于生命的敬畏不僅在于不去迫害它們,還在于必須從屬于更高的目標,那就是人道、愛和同情,人可以幫助它們實現其生命的最高價值。最后,儒家與施韋澤都關注倫理的動機,考察道德生命主體是否已經去踐行“仁”或是否去“敬畏”生命,而對于現實的結果是否道德,則可以暫時不過分計較。
以“仁”或“敬畏”為指導的道德生命觀在理論上都十分有道理,但是在實踐中是否有實施的可能性?在現實中,突破自我利益而踐行“仁”和“敬畏一切生命”都不是易事,但是人們從內心形成對它們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說,儒家的生命哲學造就了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道德生命觀成為無數仁人志士的人生態度和人生信念。儒家更難能可貴還在于十分注重人的生命超越性的一面,強調生命的自我實現和充分發揮,鼓勵人們積極入世,與自然、社會以及整個世界融合在一起。儒家對生命價值的訴求、對生命本質的探究和對生命境界的追求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濃重的一筆,這種踐行“仁”的生命觀對人們的生命實踐影響深遠,意義非凡[6]。施韋澤提出的“敬畏生命”倫理學,是對西方近代物質主義文化的批判、對造成生命威脅的核武器的反對和對頻頻出現的生態危機的反思。敬畏生命倫理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正是由于施韋澤的揭露使人們進一步認清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有啟發意義。可以說,儒家和施韋澤的道德生命理論都進一步擴展了人類的道德責任、深化了人們的道德意識、擴大了人們道德活動的領域。二者雖然由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孕育,但都在強調積極入世和本人的身體力行,都在為創造更有益于生命發展的各種價值和實現人類的和平進步而努力。
但是,筆者認為儒家踐行“仁”的道德生命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道德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在“仁”與生命發生沖突時,儒家主張用“仁”來排斥生命,把“仁”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很容易把人們的生命觀引入歧途,使人們陷入道德與生命的兩難境地。其二,儒家的生命道德主體,更多關注群體生命,缺少對個體生命主體地位的認知,這很容易陷入道德虛無主義,同時也會造成因為道德主體的缺失而對于“仁”的道德判斷尤顯不足,這即使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并非完全正確,而這往往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對于個體的生命發展是極其不利的。其三,儒家生命道德觀踐行“仁”主要是通過強調個體的道德自律和自覺來完成的,更強調個體的“慎獨”,而并不追求法律和制度的規范。事實上,人們依靠道德自律僅僅可以約束少部分人的道德行為,依靠它顯然是不能解決社會整體道德失范的。其四,儒家道德生命觀更關注于生命的道德意義,過度追求精神生命容易忽視對生命質量的思考。《論語》里就談到“子罕言禮,與命與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可以說,儒家這些傳統生命道德觀都切實地影響了國人對生命質量的合理追求。
相比起來,敬畏生命倫理學則敬畏一切生命、愛一切生命,它敦促人類承擔起無限的責任和義務,偉大且博愛,但自身也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其一,施韋澤提出敬畏一切生命的倫理思想是美好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為了生存,人們往往要消滅一些生命,而敬畏生命卻把對待其他生物的道德和對待人類生命的道德完全等同,“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的和低級的、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4]。這種道德觀念在理論上過于絕對化、機械化和片面化,在實踐中讓人們完全忽視生物之間的價值序列也是不可能的。在現實中,人們習慣于依據他物與人的關系來確定不同生命的價值,并據此舍棄那些在人看來是無價值的或低級的生命。施韋澤倫理學過度追求道德的完美主義,忽視人們內心的道德渴求和當下的社會現實,雖然對人類能夠起到警醒和提高境界的作用,但是也極有可能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局面。其二,施韋澤反對戰爭和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認為掌握核武器的人類已經成為超人,是非人道的,但是他僅僅是以倫理為依據嘗試反擊暴力,提出人類的道德信念可以成為維護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保證,確實有些理想化。不可否認的是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需要道德來推動,敬畏生命倫理思想也的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敬畏生命絕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也不可能成為反對暴力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僅僅依靠道德維護世界和平只能是施韋澤一廂情愿的想法,現實的遭遇有可能引起人們道德上的虛無主義。其三,施韋澤在道德信念上,更關注敬畏生命主體的主觀動機。施韋澤看到現實生命被掠殺的殘酷,為幫助人們樹立信心,他考慮到希望人們先有保護生命的意識,培養對生命的敬畏情感,但是這種較少考慮行為過程和結果的道德是很容易造成人們實際道德行為的盲目和無序的。道德最終還是要落實到行動上,人們對生命是否敬畏、如何敬畏,還是要看人們以何種方式對何種生命展開保護,人們對生命敬畏的道德的養成除了通過對其他生物的敬畏逐漸擴展到對人類的生命敬畏之外,還需要在每一次實在而具體的行動中,感受生命、升華生命,比如在疾病、戰爭、自然災害面前,人們實際行動起來,參與拯救之后帶給人們心靈的震撼是最能促進人們敬畏生命的道德觀念的形成的。敬畏生命不僅僅是由內而外的發散,更是由外而內的促動與提升。
[1]劉寶楠.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2]焦循.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敬畏生命五十年來的基本論述[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5]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楊珺.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要實現“三個轉向”[J].理論探索,2011,(1):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