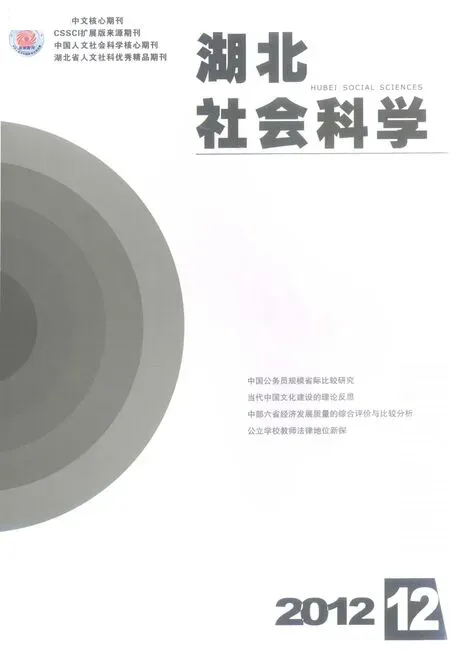公立學校教師法律地位新探
石正義
(湖北科技學院,湖北 咸寧 437000)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公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法律地位的探討和爭論持續了近20年,形成了多種觀點:教師是公務員,教師是勞動者,教師是專業人員,教師是特別公務員。由于教師法律地位直接關系到教師聘用糾紛的法律適用,因此關于教師聘用糾紛適用何種法律調整也存在較大爭議: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的,認為聘用糾紛適用公務員法;將教師定位為勞動者的,認為聘用糾紛適用勞動法;將教師定位為特別公務員的,認為聘用糾紛適用公務員法和教育法。教師法律地位的不明確,教師聘用糾紛法律適用的爭議,直接影響到教師權益的救濟。據廣州市法院統計,從2003年10月受理第一起學生起訴高校的行政案件開始,到2005年6月,廣州市兩級法院已處理了18起類似案件,但尚未受理一起教師起訴學校的案件,原因并不是沒有教師提起訴訟,而是此類糾紛在行政訴訟法上的可訴性爭議太大,司法權的能動性有限而且解決此類糾紛的技術不成熟,司法在面對教師糾紛的時候采取了謹慎介入或不介入的態度。[1](p248-250)因此,明確教師的法律地位,是解決教師聘用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的前提,是維護教師權益的法理基礎。在當前教師維權意識不斷增強、聘用糾紛案件直線上升的背景下,從理論上進一步認清教師的法律地位,對于指導司法實踐、明確教師聘用糾紛的法律適用、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教師法律地位幾種觀點的評析
教師是公務員的觀點認為,教師的主要職責是完成國家交付的教學任務,教師的這一職務行為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國家對教師的管理都是比照公務員來進行的,如《教師法》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應當不低于或高于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教育法》賦予學校對教師行政處分權,行政處分是國家機關對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工作人員的一種行政制裁措施,只有國家公職人員才可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國家與教師的關系應屬于公職關系,教師具有類似公務員的法律地位。①成有信教授認為,現代國家的公務員由三類人員組成:政務公務員(行政干部)、軍務公務員(軍事干部)和教育公務員(教育干部——公立學校教師,特別是公立普及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即人們俗稱的公教人員,它們是構成現代國家公共事務及其管理的三大支柱。教師職業具有公務性質,因為教師與行政人員一樣,其工資由國稅開支,屬第二次分配。而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來自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要打入成本,屬于第一次分配,兩者具有本質的區別,因而應在《教師法》等法律中明確教師的公務員身份。參見成有信:《教師職業的公務員性質與當前我國師范院校的公費干部學校特征》。《教育研究》,1997年第12期。持教師是公務員觀點的學者還有:王斌泰:《應將教師納入公務員序列管理》,《中國教育報》,2007-03-13;王秋麗:《建立義務教育教師國家教育公務員制度的思考》,《教學與管理》,2009年第8期;銀小貴、李龍剛、彭光明:《論公立學校教師公務員身份的確立》,《教育探索》,2009年第4期;張靈、宮君美:《中小學教師公務員身份探析》,《教育探索》,2009年第12期,等等。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對于教師的職業保障、工資福利待遇有一定好處,但它不利于教師的專業自主和學術自由,也無法解釋教師和學校雙方為什么能在平等自愿原則前提下簽訂聘用合同,特別是1993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2006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相繼將教師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排除在公務員隊伍之外的情況下,①1993年8月14日國務院公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三條:“本條例適用于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2005年通過200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以上法律表明,公務員限指國家機關中行政編制的工作人員,不包括事業單位人事編制的工作人員。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顯然與現行法律規范不一致。
教師是勞動者的觀點認為,《教育法》和《教師法》規定學校實行聘用制,學校與教師在簽訂聘用合同中遵循地位平等原則,而且聘用合同的主要內容和程序與勞動合同基本相似,因些,聘用合同本質上就是勞動合同,教師就是勞動者,應該納入勞動法調整。②持教師是勞動者觀點的學者有:吳開華:《教師聘任糾紛法律適用的現實狀況與未來走向》,《教學與管理》,2008年第4期;王鵬煒、司曉宏:《勞動者:高等學校教師法律地位的合理定位》,《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1期;陳璽名、肖鳳翔:《公立高校教師法律身份的變遷與思考》,《現代教育管理》,2010年第4期。這種觀點是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頒布后產生的,由于我國勞動法主要是從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出發的,這種觀點就特別強調有利于對教師權益的保護,因而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但是由于教師與企業職工的職業性質、工作任務、工資定級、管理制度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別,將教師聘用糾紛完全納入勞動法調整,不能體現教師的職業特點,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學校能對教師給予行政處分的事實。反對者認為,“這種說法其實混淆了勞動者概念的兩種用法。一種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也即廣義的勞動者。在我國,憲法規定每一個人都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每一個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是勞動者。在這個意義上,不僅教師是勞動者,公務員也是勞動者。另一種用法是勞動法意見上的勞動者,乃是特指《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勞動者,是狹義的勞動者。”[2](p192)
教師是專業人員的觀點,是依據《教師法》的規定而定位的,《教師法》第三條規定“教師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并且認為對教師的這一定位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教師地位的建議》中的表述是一致的。[3](p441)但是有學者對這一提法持有異議,認為專業人員的身份并不能深刻地揭示教師的法律地位,只是對教師職業特征的簡單描述,缺乏法律規范價值。[4](p214)將教師定位為專業人員,“與其說是對教師法律身份的認定,不如說是對教師社會地位的象征性宣示。”[5](p182)所以,可以認為,教師是專業人員的觀點,不是對教師法律身份的定位,而是對教師職業性質的界定,對于探討聘用糾紛的法律問題沒有參考價值。
教師是特別公務員的觀點,是在考察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考察我國臺灣地區關于教師身份定位的做法,以及考慮我國教師職業性質、薪資來源和相關法律規范的基礎上得出的。這種觀點首先認可教師應當具有與公務員類似的地位,屬于國家公職人員,先納入公務員法調整,然后根據教師的職業性質與特點,與公務員不同之處,再由教育法作出特別規定,以體現教師是特別類型的國家公職人員。[6]應該說,這一觀點比以上幾種觀點全面,它既考慮了教師的職業淵源、現實狀況,也考慮了教師的職業性質與特點。但是將教師定位為特別公務員,說明教師還是屬于公務員,這與教師是公務員的觀點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同樣與公務員法將教師排除在外的現行法律規范不一致。
二、確定教師法律地位應考慮的因素
教師法律身份的定位,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技術問題,既要符合法理,也要便于實務,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第一,要考慮學校與教師的法律關系。明晰學校與教師的法律關系是確立教師法律地位的理論基礎。就學校與教師的法律關系而言,實際上存在三種法律關系:公勤關系(或行政關系),勞動關系,民事關系。民事關系對于所有用人單位與其職工都存在,屬于所有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的共性關系,不在討論范圍之內,余下的只有公勤關系和勞動關系。因此,有學者認為,公立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法律關系體現為兩重屬性,即公勤關系屬性和勞動合同關系屬性同時并存[4](p217)。所謂公勤關系,即公法上的勤務關系,存在于行政主體(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組織)與其工作人員之間。學校不是行政機關,但它是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是行政主體,能對教師實施行政管理,如教育法賦予學校對教師行使獎勵和處分的權力,國家授權學校為教師評定職稱的權力,這些行為都是具體的行政行為,具有明顯的公法色彩。勞動關系是勞動法調整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實現集體勞動過程中形成的關系。雖然學校與教師簽訂的是聘用合同,不是勞動合同,但從勞動關系的性質和特征來看③勞動關系的性質是指,在集體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將勞動力有償讓渡給用人單位使用。勞動關系的特征表現在:①一方是勞動力所有者,即勞動者,另一方是勞動力使用者,即用人單位。②內容以勞動力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為核心,勞動力所有權歸勞動者,使用權歸用人單位。③人身關系屬性與財產關系屬性相結合。一方面,由于勞動力的存在和支出與勞動者人身不可分離,勞動者將勞動力提供給用人單位,實際上就是勞動者將其人身在一定限度上交給用人單位,因此勞動關系本來意義就是一種人身關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將勞動力讓渡給用人單位使用,用人單位必須向勞動者支付報酬,因此,勞動關系也是一種財產關系。④平等性質與不平等性質兼有。勞動關系由簽訂勞動合同建立,簽訂勞動合同須經雙方平等協商,這一過程是平等的;勞動關系一經締結,勞動者須服從用人單位管理,用人單位成為支配者,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成為指揮與服從為特征的管理關系。⑤對抗性質與非對抗性質兼有,對抗性表現在,用人單位追求效益最大化,勞動者追求報酬最大化;非對抗性表現在,雙方又是利益伙伴,雙方相互依存,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事業發展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公立學校與教師的聘用關系也符合這些特征。王全興教授在他的《勞動法》一書中認為勞動關系包括聘用關系。參見王全興:《勞動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頁。,聘用關系也完全符合。有學者認為,聘用合同本質上就是勞動合同,[7]聘用關系本質上就是勞動關系。鑒于教師與學校具有公勤關系和勞動關系的特點,教師的法律身份也應該具有兩重性,一是公法上的教育者,二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
第二,要考慮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過去教師一直被賦予國家干部身份,列入公務員隊伍。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開始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等三類具有不同特點的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先從機關和企業入手,先后頒布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1993)和《勞動法》(1994),以后又修訂頒布了《公務員法》(2005)和《勞動合同法》(2008)。 相比之下,事業單位由于主體多樣,涉域較廣,關系復雜,職能特殊,改革相對滯后。鑒于事業單位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國家首先對事業單位進行了分類改革,劃分為監督管理、經營服務和公共服務三大類,然后對三類事業單位區別對待,采取的方法是回歸、改制和保留,即對監督管理類事業單位回歸行政序列,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公益服務類保留事業編制。文化、教育、衛生和科研院所屬于保留下來的事業單位。為了解決保留下來的事業單位的依法管理問題,國務院辦公廳于2002年轉發了《人事部關于在事業單位試行人員聘用制度的意見》,隨后國家又對該“意見”進行了修訂和完善,國務院法制辦于2011年11月發布了 《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可以預見該“條例”正式文件不久將會正式頒布,這將是事業單位一部非常重要的法規。以《公務員法》、《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為標志,機關、事業單位、企業三類不同特點的分類管理制度基本形成。縱觀近二十年的改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事業單位不再實行機關的管理模式,事業單位將獨立于機關和企業,成為第三類獨立的組織。
事業單位自成一類后,雖然會有符合事業單位特點的管理制度,但由于機關和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先于事業單位,因此事業單位有些管理制度仍然會比照機關和企業的成功管理模式。那么事業單位對其工作人員的管理是更多地參照公務員管理,還是參照勞動者管理?從改革過程中的幾個重要事項中可以窺見一斑:一是大部制改革。由于聘用關系和勞動關系性質的相近性,國家開始將人事管理與勞動管理進行融合,以統一人力資源市場,2008年將人事部、勞動部合并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二是《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的頒布和實施。過去,我國事業單位聘用糾紛適用的是人事爭議仲裁,企業勞動糾紛適用的是勞動爭議仲裁。2009年1月1日《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頒布并實施后,結束了我國多年人事爭議和勞動爭議相分離的管理模式,將勞動、人事“合二為一”。另外,《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第六十條規定:“事業單位與工作人員發生人事爭議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有關規定處理”。三是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指出:“完善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政策,逐步建立起獨立于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體系。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養老保險費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個人繳費全部記入個人賬戶。”這一政策表明,在社會保險制度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企業勞動者沒有區別,實行相同的制度。從以上幾項重要的改革動作中可以看出,勞動管理和人事管理在許多方面是可以“合二為一”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從公務員隊伍分離后,事業單位對其工作人員的管理許多方面參照企業對勞動者的管理,少數事項參照機關對公務員的管理,這就是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這一改革走向表明教師的公務員身份逐漸淡化,而勞動者身份則逐漸顯現。
第三,要考慮與現行法律規范的銜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明確地將教師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說明公務員法沒有為教師聘用糾紛的法律適用留下空間,也就是說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無法與現行法律相銜接。但是勞動法等相關法規并沒有拒絕事業單位,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3]13號)第一條指出:“事業單位與其工作人員之間因辭職、辭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發生的爭議,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處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適用法律等問題的答復》(法函[2004]30號)第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的程序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相關規定。人民法院對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的實體處理應當適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規定,但涉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勞動權利的內容在人事法律中沒有規定,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有關規定。”《勞動合同法》吸納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適用法律等問題的答復》(法函[2004]30號)的意見,《勞動合同法》第96條規定:“事業單位與實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員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未作規定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執行。”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勞動法等相關法規從來就沒有排除聘用糾紛的法律適用,一直為聘用糾紛留有適用的空間。《勞動合同法》第96條提出這樣一個法律適用的原理,即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法律適用方面,我國法律規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即先適用特別法,特別法沒有規定的再適用一般法。對于教師來說,這里的特別法指的是教育法、《人事部關于在事業單位試行人員聘用制度的意見》以及即將頒布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一般法指的是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因此,從當前現行的法律規范看,《勞動法》為人事爭議留有適用空間,但《公務員法》則未留空間。也就是說,將教師定位為公務員的可能性為零,而將教師定位為勞動者則能夠與現行法律規范很好地銜接。
第四,要考慮教師職業的性質和勞動特點。教師不是公務員,但教師也不像企業職工一樣是普通的勞動者,必須承認教師與普通勞動者的區別。教師是教育者,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承擔著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質的使命。所以國家針對教師的職業性質和勞動特點,對教師進行專門立法,通過教育法律法規特別規定了教師的權利義務、薪酬待遇、工作條件,以及國家和學校對教師實行管理的教師資格制度、職務制度和聘用制度等基本制度。同時教師作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規定,事業單位可以對其工作人員實行獎勵和處分,執行國家統一的工資制度和工時制度。法律法規對教師的這些特別規定,都是企業等普通勞動者所不具備的。
三、教師的法律地位——公務勞動者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教師的法律地位作出這樣的設計:第一,由于學校和教師的法律關系存在公勤關系和勞動關系兩重屬性,因而教師的法律地位不可能是單一的,即不可能是單一的公務員或單一的勞動者,而應當是雙重的,即公務員性質與勞動者性質并存。第二,考慮到我國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和與現行法律規范的銜接,特別是《公務員法》排除了教師,而《勞動合同法》則為解決教師與學校之間的人事爭議留有適用空間,因此應當將教師歸入勞動者。第三,由于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又不能將教師簡單地與普通的勞動者同樣看待,而應作為勞動者中的特別群體,在管理制度上區別對待。鑒于這樣的分析,教師法律身份的正確定位是——公務勞動者(或特別勞動者)。
這種定位的理由在于:一是考慮了教師與學校存在公勤、勞動兩重法律關系。《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對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兩重身份表現得非常明顯,一方面事業單位與工作之間的聘用合同管理、社會保險基本上相同于企業對職工的管理;另一方面事業單位對工作人員的獎勵處分和考核又基本上類似于機關對公務員的管理。二是考慮了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教師不是一般的勞動者,而是特殊的公務勞動者。三是與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是一致的,將教師從公務員隊伍中分出,同時打破干部、工人身份之別,將人事關系和勞動關系一并納入人力資源統一管理。四是可以與現行法律規定很好地銜接,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教師聘用管理中的糾紛首先適用特別法,即人事法規和教育法規;人事法規和教育法規沒有規定的再適用一般法,即勞動法規。五是與公立學校的法律地位一致,公立學校的法律地位是公法人,學校首先是法人,同時又是公務法人,教師的地位與之相對應,教師是勞動者,而且又是公務勞動者。六是國外也有先例,如美國、英國將公立學校教師定位為公務雇員,這里的“雇員”類似于我國勞動法的“勞動者”。
需要指出的是,有學者擔心,將教師定位為勞動者,會使教師與學校的關系向“私”法關系發展。本文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勞動法并非私法,它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產物,是公法和私法兼有的社會法。教師作為公務勞動者,某些方面納入勞動法調整,并沒有改變教師職業“公益”的性質,而是有利于對教師權益的保護,因為勞動法主要是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
[1]劉躍南,鞠曉雄.超越理論爭議和現行制度局限的實踐——廣州市兩級法院裁判學生訴高校行政案件的實證研究[A].湛中樂.大學自治、自律與他律[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申素平.教育法學:原理、規范與應用[M].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
[3]勞凱聲.變革社會中的教育權與受教育權:教育法學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4]湛中樂.公立學校法律地位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蔡海龍.學校法律地位變遷中的教師身份與教師社會經濟地位[C].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6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
[6]申素平.對我國公立學校教師法律地位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9).
[7]吳開華.教師聘任糾紛法律適用的現實狀況與未來走向[J].教學與管理,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