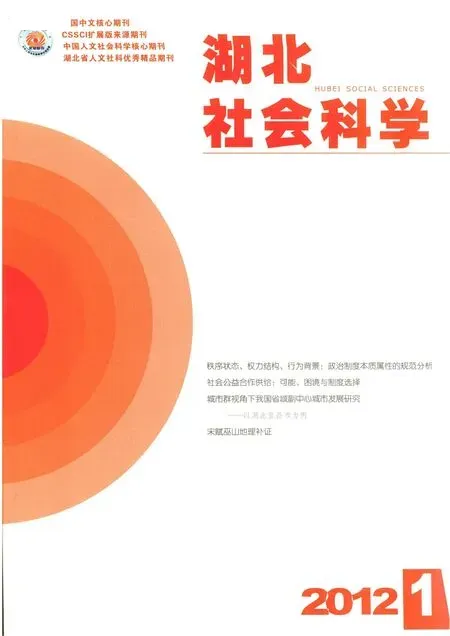秩序狀態、權力結構、行為背景:政治制度本質屬性的規范分析
馬雪松,劉乃源
(1.中國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所,北京 100732;2.吉林大學 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秩序狀態、權力結構、行為背景:政治制度本質屬性的規范分析
馬雪松1,2,劉乃源2
(1.中國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所,北京 100732;2.吉林大學 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制度作為人類的實踐性結果,構成了政治生活的根本背景,也為政治交往和公共領域提供了必要的媒介。政治制度是社會科學各學科及研究領域進行現實考察與理論探究的重要對象,因而對于政治制度本質屬性的揭示和闡述也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規范分析的研究視角出發,突出強調政治范疇的核心要素及制度概念的基本涵義,能夠揭示政治制度的本質屬性包括具有內在聯系的三個方面:政治制度是政治領域的秩序狀態、政治權力的結構與安排、約束和引導人類行為的背景性因素。
政治制度;秩序狀態;權力結構;行為背景;本質屬性
首先,政治制度對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為秩序的確立。基于這樣的分析視角,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政治秩序的確立過程。一方面,從政治秩序的實現前提來看,政治秩序需要某種規則來約束、引導、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行為,因而政治秩序在形式上表現為政治規則的制定、實施并獲得相應遵守。阿倫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在缺乏一個普遍原則的條件下,不可能確立起任何的秩序”。[4](p8)另一方面,從本質上理解政治秩序的確立,需要理解作為政治秩序核心內容的政治統治以及國家的實質功能。恩格斯在論證國家的起源時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5](p170)從中可以發現,其一,政治制度的內涵包括具有約束作用并被強制實施的規則性要素,政治制度發揮作用就反映了社會生活在整體上或行動者在某一層次或方面的交往從無序轉為有序。其二,將社會沖突控制在秩序范圍之內的論斷,不僅探究了國家產生的根源并深刻揭示出國家的本質,這實際上也是將政治制度理解為構成政治秩序的主要力量。“國家通過自己的權力系統和法規體系建立的秩序,是把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合法化、制度化,把階級沖突保持在有利于統治階級的秩序所允許的范圍以內”。[6](p12-13)根據這樣的認識,可以認為作為國家統治重要形式的政治制度不僅蘊含著階級統治的實質,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秩序狀態的確立。
其次,政治制度所蘊含的秩序內容還體現在制度研究者關于秩序的理論闡述。一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者傾向于將秩序狀態同某種制度安排等同起來。例如,韋森在其研究中嘗試性地將制度同秩序予以整合,并提出“制序”這一范疇來對譯英文中的“institution”。具體而言,“制序”是“由規則調節著的秩序”,這就是習慣、習俗、慣例在成為制度以后并未失去作為一種秩序和非正式約束的特征,而是潛在地包含在作為單一規則或規則體系的顯在性制度之內,同時與其他制度性規則同構在一起。因此,“制序包括顯性的正式規則調節下的秩序即制度,也包括由隱性的非正式約束所調節的其他秩序即慣例”,“制序是規則中的秩序和秩序中的規則”。[7](p63)這表明制序作為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復合體系,不僅構成了社會秩序的重要內容,也使制度概念的范圍得到一定的擴大。盡管這是建立在演化博弈分析基礎上的制度觀,但無疑對制度的概念闡釋及理論建構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此外,一些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者十分重視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之間張力,認識到由一定規則構成的制度不僅有助于促成合作均衡,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均衡、制度和秩序三者本身也具有內在一致性。[8](p10-11)另一方面,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奠基者馬奇和奧森指出,政治理論尤為重視政治制度在創造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強調制度結構將秩序性要素施加于人類生活這一重要過程,因此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理論視域下的制度包含歷史秩序、時序秩序、內生秩序、規范秩序、生活秩序和象征秩序等六個方面。[9](p743-744)
二、作為權力結構的政治制度
就其基本含義而言,政治制度既可以是得到實施和貫徹的規則也可以是施加強制性影響的組織,能夠對政治利益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因而有研究者據此認為政治利益分配本身決定了政治制度的本質。“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利益博弈的結果,政治利益在不同政治主體或利益集團中的分布決定了政治制度的本質與形態,反過來,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又成為不同利益集團實現利益的規則”。[10]這種認識盡管深刻把握了政治利益及其分配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意義,卻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根本性利益分配的決定作用,沒有充分認識到政治權力構成了作為利益分配機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內容。“權力是理解政治制度的實質要素”,[11](p32)從這個思考角度出發,政治制度實際上是政治權力的一種結構與安排,同時也是政治制度本質屬性的重要方面。這一點在薩拜因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社會中的某些制度稱為政治制度,因為它們代表著權力或權威的一種安排。這些制度被看作是權威的合法的運用者,它們運用這種權威為整個社會作出各種決定(如果在一定的地區或在一定的人類集體中不存在這樣的制度,那也就很難說在那里存在著一個真正的社會或政治共同體)。集體和個人當然非常注意這些制度所采取或作出的決定,因為他們的利益和目的將受到這些制度的影響”。[12](p4)
政治制度的本質是強制性政治權力的結構與安排,這也可以概括為政治制度是一種權力結構,對于這樣的認識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政治制度就其含義而言,本身就同權力結構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一方面,政治作為社會交往活動的重要形式,它意味著人們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涉及強制性權力的運用,這也是政治學者所強調的“政治意指權力的實施”。[8](p52)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本身的結構性和層次性特征,政治制度也被看作是政治權力在結構性或框架性要素中的存在與實施,因而可相應地將政治制度概括為某種權力結構。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權力結構是政治制度本質屬性的重要方面,并不是說兩者具有等同的含義,這是因為權力結構的內涵要比政治制度更為豐富。另外,從個體與結構關系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政治制度作為某種權力結構,并不是僅僅堅持政治權力在結構性要素中分布這一觀點,而是同時堅持政治權力蘊含于制度性規則之中并在制度性組織中實施,這對個體或集體行為乃至能動性而言無疑是一種結構性的權力安排與運作。
其次,從現實政治運作方面考慮,政治制度與政治權力具有明顯的伴生關系。政治制度的生成、維系、變遷同政治權力的實施存在直接關聯,政治權力在產生、配置和運行方面也受到政治制度的根本影響。一方面,政治制度存在的意義就是圍繞政治利益的分配,以強制性力量的運用作為必要措施與最終手段,從而實現某種政治秩序。這種強制性力量實際上就是政治權力,圍繞著政治權力進行的斗爭也往往導致以規則或組織為基本形式的政治制度的創設與演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者瑟倫與斯坦默指出,“制度在針對政治權力的斗爭中創造出來或發生變遷”。[13](p22)其他政治制度理論者也認為,“制度產生和消亡的過程既涉及新的觀念,也涉及新的權力架構”。[14]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不僅受權力運作方式的塑造,也對政治權力的產生、分配、作用方式及范圍發揮重要影響。例如,在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中蘊含著明顯的權力結構,而這一權力結構又是由作為政權組織形式的根本政治制度所規定的。[6](p28)因此,根本政治制度不僅對于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產生影響,也必然塑造其他層級和方面的政治權力運作和分配方式。這樣的認識還充分體現在制度理論者奧菲的論述中,“制度同社會權力的產生、分配、實施和控制密切相關”,“制度通過某種機制影響社會權力在行動者之間的分配”。[11](p1)
三、作為行為背景的政治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5](p56-60)這揭示了作為行動者的人們通過能動性的發揮和交往性的行動構建了社會生活,社會并非個體在數量上的加總,而是由實踐性與能動性在相互關聯的過程中產生的。有研究者在這個意義上指出,“社會既不是簡單地從個人開始的,也不是外在地給定的所謂整體”。[16](p11)由此可見,一方面,人們作為具有意志的實踐者,通過發揮能動性而將目的加諸客觀世界和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人們的能動性和實踐能力受到生產方式及社會交往的限制。政治制度作為社會關系的某種結果和社會互動的重要形式,它同人類能動性具有密切關聯。政治制度是人類政治實踐的結構模式,盡管受到能動性和實踐活動的影響,但也構成了對于人的行動乃至能動性產生約束或引導作用的背景性因素。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豐富的研究成果中,很多學者指出制度對理性行動者的行為選擇施加重要影響。例如,歷史制度主義者霍爾和泰勒認為,“制度分析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如何影響個體行為”。[17]日本政治學者加藤淳子也指出,政治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各流派均關注“制度是如何塑造政治行為和后果的問題”。[18]政治制度作為約束和引導人類行為的背景性因素,對此可從如下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政治制度對個體或集體行動本身具有約束作用。一方面,作為規則的政治制度能夠限制個體或集體行動者的活動方式。具體而言,制度性規則通過限制可選行動方案的范圍、約束人們的交往模式、塑造利益相關者的激勵結構,會對政策產生明顯的影響,有理論者將此概括為“作為一套規則的制度決定了個體行動聚合為集體決策的方式”。[19](p179)在他們看來,具有執行效力的規則不僅限制了個體行動,而且使個體行動在制度性規則的約束下轉化為特定類型的集體行動,這既是對個體行動的限制,也是對集體決策構成的約束。另一方面,部分堅持文化因素具有重要作用的學者認為,由于政治制度在規范層面上具有“適宜邏輯”的特征,也就是政治制度“對于那些位于社會系統之中并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們來說,界定了他們正當的和可預期的行為”,這導致行動者在政治制度的影響下表現出某種固定的行為模式。[20](p239)這說明了在行為選擇受到限制的過程中,行動者的能動性實際上也受到了某種約束。
其次,政治制度對個體或集體行動者的激勵結構或偏好具有約束作用。隨著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特別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不斷發展,制度理論者在思考人與制度的互動關系及偏好是如何產生的問題時,不但承認外衍性偏好受結構性或程序性制度的塑造,還認為某些偏好可能內生于組織性制度之中。具體來看,部分經濟學者如諾斯關注制度對偏好的塑造作用,強調政治制度所蘊含的規則要素能夠塑造相關行動者的激勵結構,“制度為經濟提供了激勵結構,制度演化方式因而塑造了長期性經濟偏好”。[21](p242)同理性選擇理論者的分析方式存在一定差異的是,一些政治學者根據規范理論指出,“利益和偏好在人類行為的制度背景下產生”。[9]這意味著行動者在政治制度的規范作用下往往根據角色與情境的關系來界定適宜行動,從而在分析中把利益與偏好視為內生性要素。當行動者的激勵結構與偏好受到制度限制,此時能動性的發揮無疑也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約束。
再次,政治制度對個體或集體行動者的能動性具有引導作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認為,對于個體或集體行動者來說,政治制度在某種意義上也為行動者賦予了政治制度闕如情況下不可能具備的行動能力。一方面,政治制度以促進合作的方式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為行動者發揮能動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塑造了行動者的意圖,有助于引導行動者更好地發揮能動性。“制度不但允許人們通過協調其行為以達成目的,還可以創造并改變目的本身”。[11](p72)當行動者的意圖由于制度的塑造而使能動性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也意味著能動性本身得到了積極和有效的引導。
最后,作為行為選擇背景的政治制度對于能動性而言并非是一種外在的給定性力量,而是融入了人類能動性的實踐結果。政治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由人類創設的,但具有創造能力的人們通過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能動地改變政治制度。一方面,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人類實踐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存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產物”。[14](p77-78)薩拜因也認為,“政治制度和政治學說兩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們是人這個物質實體的延伸部分,人類團體經常創造制度和慣例”。[12](p4)另一方面,人與制度之間不斷地發生交互性作用。“政治不是簡單的權力與制度及其運行,而是人與制度的不斷互動所構成的政治生活”。[22](p3)實際上,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中,并沒有將制度或結構性要素視為決定個體行為的最終因素,也拒絕把個體能動性看作獨立于制度約束或決定結構性要素的先在力量。由于人類行動與制度結構在邏輯上是相互關聯的,因此所有社會生活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在強調制度結構的約束性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同時肯定人類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23]
[1]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2][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3]Stephen Skowronek.Order and Change[J].Polity,1995,(1).
[4][美]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M].竺乾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王惠巖.當代政治學基本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韋森.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Karol Soltan,Eric M.Uslaner,and Virginia Haufler.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9]James G.March,Johan P.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3).
[10]曹曉飛,戎生靈.政治利益研究引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11]Ian Shapiro,Stephen Skowronek,and Daniel Galvin.Rethink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Art of the Sta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12][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 [M].盛葵陽,崔妙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3]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and Frank Longstreth.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James T.Kloppenberg.Institutionalism,RationalChoice,and Historical Analysis[J].Polity,1995,(2).
[1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學[M].文軍,趙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7]Peter A.Hall,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s [J].Political Studies,1996,(1).
[18]Junko Kato.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2).
[19]Elinor Ostrom.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2.
[20]Talcott Parsons.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M].Glencoe:Free Press,1954.
[21]Uskali Maki,Bo Gustafsson,and Christian Knudsen.Rationality,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Methodology[M].New York:Routledge,1993.
[22][美]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M].張華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3]馬雪松.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內在張力與理論取向[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1,(1).
D03
A
1003-8477(2012)01-0018-04
一、作為秩序狀態的政治制度
馬雪松(1982—),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吉林大學行政學院講師。劉乃源(1982—),女,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項目編號:11JZD030;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項目“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理論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11QY032
責任編輯 申 華
制度作為人類交往的產物和實踐性結果,一直是社會科學考察的主要對象,因而在政治研究的歷史演進與當代發展中,制度分析往往占據著重要地位。一般而言,可以把政治制度理解為圍繞利益的競取與分配,以政治權力的強制執行作為保證,同法規制定和政策選擇活動緊密關聯的規則和組織的結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制度在發揮效力的過程中對人的行為產生限制或塑造作用,從而影響行動者能動性的發揮。基于這樣的認識,從規范分析的研究視角出發,突出強調政治范疇的核心要素及制度概念的基本涵義,能夠揭示政治制度的本質屬性主要表現為具有內在聯系的三個方面,即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礎性意義的秩序狀態,是強制性政治權力的結構與安排,還是對個人及集體行為與能動性產生約束與引導的背景性因素。
人類社會的組織建構與發展延續無法在始終動蕩不安和爭斗不休的環境下進行,因而秩序對于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來說極為重要。哈耶克指出社會生活之中存在著某種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的社會秩序,該秩序如果不復存在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社會成員不僅無法進行正常的生活,他們的基本需求也往往難以實現。[1](p160)也有學者從積極方面指出秩序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一個維持著基本秩序的共同體之中,人們通過對未來的合理預期能更好地與其他社會成員開展合作,這意味著秩序有助于增強人們之間的相互信賴,從而降低合作行為的成本。實際上無論在經濟學還是政治學的研究視域中,制度的重要性都突出表現為它對秩序的促進作用。例如,制度經濟學者柯武剛和史漫飛所著《制度經濟學》一書的副標題就是“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這是由于“制度的關鍵功能是增進秩序,它是一套關于行為和事件的模式,它具有系統性、非隨機性,因此是可以理解的”,通過審視制度在經濟交往中如何促進秩序的實現,考察共同體內部個體或集體行動者在面對資源稀缺性問題時的行為模式,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社會秩序同公共政策之間的聯系。[2](p33)此外,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者斯科倫內克也指出對于關注政治制度的研究者而言,幾乎所有研究框架都把制度視為秩序的支撐性力量與政治生活的規制性結構,因此政治制度“將各種人類行為融入政治過程并協調政治利益,從而使行為同組織化的系統連結起來”。[3](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