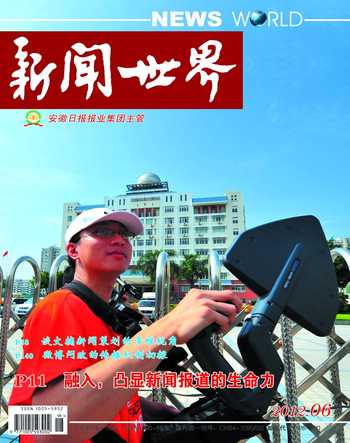試論微博實名制實施的正當性
丁麗瓊
【摘要】隨著微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引發了一系列的負面問題,如謠言的傳播、虛假信息的發布、“粉絲”買賣、言論侵權、以及利用微博進行欺詐等。為了減少上述問題的不良影響,微博實名制在今年3月中旬開始實施。本文認為微博實名制實施后,一方面可以利用隱私制衡微博這一公共領域中個人的不理性行為,并限制消費、買賣隱私的行為;另一方面在言論自由方面提醒諸人警惕“網絡暴民”。
【關鍵詞】微博;實名制;言論自由
微博網站在中國創辦至今,發展不過4年,微博賬戶就已增長到3.2億,約占中國網民的65%。微博已經超越網絡論壇,成為僅次于新聞媒體報道的第二大輿情源頭,宣告了“自媒體”時代的來臨。但是,隨著微博在信息傳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如謠言的傳播、虛假信息的發布、“粉絲”買賣、言論侵權、以及利用微博進行欺詐等。
去年12月16日,為了規范微博的發展管理,維護網絡傳播秩序,保障信息安全,保護互聯網信息服務單位和微博客用戶的合法權益,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注冊微博賬號要用真實身份信息,否則只能瀏覽不能發言。此規定一出,立刻得到了新浪、搜狐、網易、騰訊四大微博網站的響應,并從今年3月16日起開始采取“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方式,全部實行實名制。
微博實名制的實行,掀起了網上如潮般的論戰,微博實名究竟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成為論戰的中心,通過分析發現,持微博實名制弊大于利的觀點的人對于弊的闡述主要是著眼于以下兩點:微博實名會侵犯用戶的隱私、微博實名不利于言論自由的實現。
本文認為,微博實名制的實施是規范網絡環境的必然要求,該舉措不僅不會對用戶的隱私和言論自由造成威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們理性地認識個人隱私與言論自由,從而規范自身的言行,共同維護微博這一平臺,并助力于建立良好的網絡秩序。
一、公共領域呼喚隱私制衡
微博實名制實施后,很重要的一個論爭就是是否會對公民隱私權造成侵犯,筆者認為,這個論爭背后其實指向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微博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
關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探討,本文主要參照漢娜·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理論來分析微博。漢娜·阿倫特在其《人的條件》一書中,她區分了人類實踐的三種形式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三種領域。即“勞動”、“生產”、“行動”。其中,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是“行動”,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意味著:排除了任何僅僅是維持生活或服務于謀生目的,不再受到肉體性生命過程那種封閉性的束縛。如果說漢娜·阿倫特較多地從人類本性的角度出發探究這一概念的話,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則更加注重政治制度層面,他意指一種不受官方干預,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社會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與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或公共場所。
根據上述論述筆者個人認為,微博是屬于“公共領域”的,那么“公共領域”內的隱私又意味著什么呢?根據漢娜·阿倫特的理論,她指出,“按字面意思理解,隱私意味著一種被剝奪的狀態,甚至是被剝奪了人類能力中最高級、最具人性的部分。一個人如果僅僅過著個人生活(像奴隸一樣,不被允許進入公共領域,或者像野蠻人那樣不愿建立這樣一個領域),那么他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①她認為隱私是屬于“遮蔽的空間”,即私人領域的,相對應的,她把公共領域稱之為“顯現的空間”,從這兩者的概念對比中,筆者認為,隱私與公共領域雖然看似對立,卻是對應存在的。外界的壓力越大,人們對于隱私的認識就越加清晰,隱私在與顯現的空間進行博弈的過程中,獲得了其存在的價值,所以不會有人因為隱私的緣故而拒絕進入公共領域。通過上述分析,個人認為隱私是個相對的概念,是基于公共領域而存在的,它存在的價值在于保護個人生活免受社會干擾和侵犯,同時也壓制個人行為中與社會價值不符的部分。
在微博實名制實施以前,在微博這一公共領域中,個人雖然在其中行動,但是與之對應的個人身份卻是不明的,能夠對個人的行動起到限制以及保護作用的隱私是缺席的,這就會導致微博環境的失調。微博實名制實施后,用戶的真實身份會在后臺中顯示。這對于已經加V認證的用戶來說基本沒有影響,普通用戶只需實名注冊就可完成升級,在發言及評論時,出于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意識,會更傾向于避免發布不負責任的言論。
但是,微博實名制的實施并不只是通過隱私制衡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發表不負責任言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遏制一些不法之徒消費隱私、買賣個人信息的行為。在微博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將對某個特定的言論大量轉載引發關注度,或者進行言語攻擊,從而影響輿論的正常發展;而水軍的行為與上述行為類似,只不過更具有組織性。這種行為不僅是對隱私的侵犯,它甚至會導致公共領域的消亡。
漢娜·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一書中提到,“行動”占據了人類實踐行為的制高點,屬于私人領域的“勞動”,為人們進入屬于公共領域的“行動”提供了生活必需品,連接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紐帶就是私有財產。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財富與資本的累積成為社會共同的目標,這種累積最大的驅動力正是人們無休止的消費的欲望,“行動”的優勢主導地位逐漸被勞動與消費占據。那么失去了“行動”意義的公共領域“既不是公共領域,也不是私人領域”②,哈貝馬斯則稱其為社會領域,它是財富或資本體系對公共領域殖民化的產物,財富或者說資本的邏輯直接決定著社會領域的邏輯。
微博作為一個公共領域,無疑正在遭受著社會領域的滲透。微博變成了營銷平臺和利益的角斗場,隱私不僅被拿來販賣、消費,成為盈利的商品,并且時常成為罵戰中的殺手锏,即使被害人還擊,他面對的只是虛擬的賬號。
微博實名制實施后,個人身份信息是專有的,對于別有用心的人來說,不能再批量注冊賬號意味著“失勢”,這樣就使得正常的用戶免受無名氏的攻擊與誹謗,同時有利于良好的輿論環境的形成。
二、言論自由拒絕“得勢輿論的暴虐”
微博實名制引發的不僅是隱私權的爭論,還包括對言論自由的探討。學界對于言論自由的定義很多,但是側重點不同,本文參照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對自由的認識:“唯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只要我們不是圖剝奪他人的這種自由,不試圖阻礙他們去的這種自由的努力”。③
我們通常所講的言論自由是以不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為前提的,但是,筆者認為在微博這個環境中,更應該強調密爾提到的表達“個體性”的自由。在這個開放互動的媒介環境中,壓制個體表達自由的最大因素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制度,而是被密爾稱為“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
據新浪微博公布的數據,微博中的話題主要以情感、娛樂、休閑為主,政治不到5%。經常暗潮洶涌,動輒就演變成口水大戰的反到是涉及大眾日常生活的領域,“圍觀”很容易就變成“圍攻”,“網絡暴民”遠比幾個人不負責任的言論要可怕。
“網絡暴民”要么是有著共同愛好的群體,如明星粉絲;要么是對社會現狀有所不滿,借機發泄的普通人。他們的言論表達方式經常是不理性的,缺乏寬容的,通過人肉搜索、言語攻擊、惡意揣測等達到發泄情緒的目的。前不久的影視明星舒淇退出微博事件,起因其實微不足道,當時正值另外兩大武打明星隔空對罵,她站出來為其中一人說了一句話,卻被網友翻出了成名前的舊賬,受到了各種人生攻擊乃至誹謗,最后迫不得已關閉微博。另外一件是中國兩個在美留學生在學校外附近寓所被陌生男子槍殺,引起了中外各大媒體的關注,紛紛譴責殺人兇手,但是微博流傳的聲音卻大大不同于媒體的報道:兩個受害者被擅自戴上了“富二代”的帽子,各種嘲笑、譏諷、幸災樂禍的評價成為主流,不禁令人心寒。
網絡暴民的危害不僅僅在于對他人隱私權、名譽權等的侵犯,還有一點是如“沉默的螺旋”理論所說:“輿論的形成不是社會公眾的‘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動這一非合理過程的產物”④,“得勢的輿論”必然會壓制其他聲音,而微博由于其強大的即時發言及評論,可以迅速擴大這種影響力。如果長此以往都是這樣一種言論氣氛:窺視、揭露、攻擊以及冷眼旁觀,這對于社會道德體系的建設以及社會風氣的破壞會是很大的。
此外,還會表現為一種約翰·密爾所認為的:“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而只能找到這樣一類的人,不是濫調的應聲蟲,就是真理的應時貨”⑤,這意味著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個人將逐步消亡,即使擁有言論自由,那也只是異口同聲的、如同死水一般的言論。
微博實名制實施以后,很大程度上可以遏制這種“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微博實名制的實施雖然表面上限制了用戶發言的權利,但卻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媒體”中由于自發、盲目以及暗箱操作導致的負面影響;其次,微博實名制的實施增強了個人的身份認同,個人的著作權具有明確的歸屬,現實的個人與他在網絡中的言論密切地聯系起來,既可以鼓勵個人發表見解,也可以防止個人不負責的言論的產生;最后,微博實名制有利于對那些打著“言論自由”幌子四處造謠、蠱惑人心的網民的追責與查處,很大程度上節省了國家的行政資源。
參考文獻
①②漢娜·阿倫特 著,竺乾威 等譯:《人的條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222
③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著,許寶骙譯:《論自由》,商務印刷館,2005:14
④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221
⑤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與制度的變遷》,學林出版社,2003:34
(作者:均為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