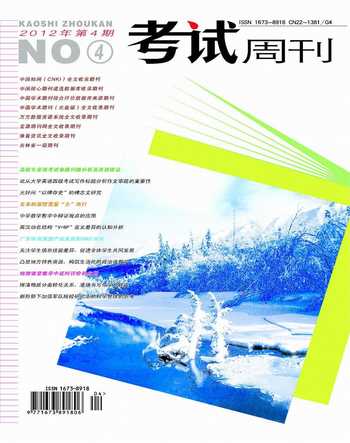英漢動名結(jié)構(gòu)“V+NP”意義差異的認(rèn)知分析
陳蓮潔
摘要: 本文從認(rèn)知語言學(xué)和構(gòu)式語法的角度對英漢“V + NP” 結(jié)構(gòu)中論元成分的語義和語用差異現(xiàn)象進(jìn)行分析,指出漢語NP在“V + NP”中不一定是受事標(biāo)記,并說明這種結(jié)構(gòu)可能對中國學(xué)生正確掌握英語動詞短語搭配造成一定的困難。
關(guān)鍵詞: 認(rèn)知語言學(xué)構(gòu)式語法英漢動名結(jié)構(gòu)“V+NP”意義差異
一、引言
張云秋,王馥芳在分析漢語“V + NP”(原文標(biāo)記為“V+ON”)時指出,漢語有受事標(biāo)記過度的現(xiàn)象,他們從優(yōu)選論(Optimality Theory)的角度對此現(xiàn)象提出解釋,認(rèn)為漢語的結(jié)構(gòu)限制條件的階層排列體系有兩個,造成了受事標(biāo)記過度:“忠實性條件>標(biāo)記性條件”和“標(biāo)記性條件>忠實性條件”[1]。但是,從他們列舉的五種“V+ON”例句看,動詞V的后面不一定就是“受事成分”,即,一般語法所謂的“賓語”現(xiàn)象,標(biāo)記為“V+ON”似乎不夠精確,“寫文章”的關(guān)系是受事還是結(jié)果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吃西餐(受事)
(2)寫文章(結(jié)果)
(3)吃食堂(處所)
(4)吃小灶(方式)
(5)吃大碗(工具)
同時,文中引用王艾錄、司富珍的例句,認(rèn)為下列例句每一句只符合語義、句法、語用當(dāng)中的一項規(guī)則,顯然有悖常理:
(6)?香蕉吃大象。(句法)
(7)他吃了兩個饅頭。(語義)
(8)你去洗個澡吧。(語用)
因此本文從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角度和構(gòu)式語法角度探討這一現(xiàn)象,并討論英漢動名結(jié)構(gòu)“V+NP”的意義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可能對中國學(xué)生造成的認(rèn)知困難。
二、認(rèn)知語言學(xué)和構(gòu)式語法
認(rèn)知語言學(xué)主要指以Langacker為代表的認(rèn)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和以Goldberg為代表的構(gòu)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簡寫為CxG.)。關(guān)于他們的主要學(xué)術(shù)思想,國內(nèi)近年來介紹評述頗多,其影響力也日益擴(kuò)大。
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基礎(chǔ)是體驗哲學(xué),主要概括為三條基本原則:“心智的體驗性,認(rèn)知的無意識性和思維的隱喻性”[2]。心智的體驗性說明語言認(rèn)知是人類認(rèn)知能力的一個部分,認(rèn)知必須建立在人們對客觀事物的體驗基礎(chǔ)上。人類基于經(jīng)驗,獲得基本范疇概念,進(jìn)而在大腦中形成完整的概念。Taylor認(rèn)為語言知識屬于的一個部分,隱喻以概念化形式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概念的理解借助于人們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積累。認(rèn)知的無意識性意味著認(rèn)知不一定完全依靠形象語言,存在著非語言思維。人類思維過程是運用隱喻、轉(zhuǎn)喻和心理表征的結(jié)果[3]。認(rèn)知語言學(xué)同時強(qiáng)調(diào)思維的完形特征,即一個概念的形成不能夠從各構(gòu)成部分特征之和簡單疊加而來。前文提及,相同的“V+NP”:“吃飯、吃辣、吃食堂、吃蒼蠅、吃槍子兒、吃官司、吃虧”表示不同的句式意義。英語的“V+NP”結(jié)構(gòu)大多是受事成分,但不是全部:
(9)He sneezed his tooth right across town.
(10)She smiled herself an upgrade.
(11)The legs agitated themselves once more.
(12)We changed train in Shanghai.
(13)Your argument does not hold water.
(14)He kicked the bucket.
因此,傳統(tǒng)的形式語法不能對此做出全部解釋。作為對Chomsky學(xué)派的批判,構(gòu)式語法家強(qiáng)調(diào)語言的特殊性,反對語言有普遍共性的觀點。一個構(gòu)式的意義應(yīng)由構(gòu)成該構(gòu)式的要素和構(gòu)式本身共同決定,即構(gòu)式是形式與意義的結(jié)合[4]。構(gòu)式應(yīng)當(dāng)借助于語義,語用,認(rèn)知和功能需要說明意義,而不必借助于普遍語法和轉(zhuǎn)換生成語法的深層、表層結(jié)構(gòu)。構(gòu)式語法不僅能解釋常規(guī)語言結(jié)構(gòu),也能解釋非常規(guī)語言結(jié)構(gòu)(“patterns with unusual quirks”)。Goldberg在各類文章中,多次列舉了“Time-away construction”,“Incredulity construction” 以及“The co-variational construction”等構(gòu)式來說明觀點。構(gòu)式可涵蓋的范圍很廣,既有一般意義的短語,句法結(jié)構(gòu),也包括成語復(fù)合詞語素。另外,Goldberg強(qiáng)調(diào)觀察研究語言構(gòu)式,認(rèn)為兩種語言構(gòu)式相同的前提條件是“完全排除其他任何類似的結(jié)構(gòu)”,語言知識在大腦中從零散的語言知識,積累成網(wǎng)絡(luò)化狀態(tài)。“the difference ...is due not to semantic generalizations,but to generalizations about information structure properties of the construction”[5]。
3.英漢“V+NP”結(jié)構(gòu)意義差異分析
漢語許多內(nèi)在語言結(jié)構(gòu)還沒有得到充分解釋。漢語“V+NP”的意義隨論元成分的具體意義和話語主旨不同而變化。漢語的施事受事位置是相當(dāng)靈活的:
(9)這人我見過。他脾氣古怪得很,魚翅他不愛吃。
(10)北京白領(lǐng)置業(yè)時尚—租四環(huán)、買七環(huán)、開中檔車
考察語言的模式必須從語言內(nèi)部規(guī)律著手。“認(rèn)知句法的任務(wù)就是描寫有關(guān)的內(nèi)在語言知識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范圍和具體運作”[6]。在談到漢語語序與語義語用關(guān)系時,劉丹青認(rèn)為,話題優(yōu)先是漢語語法語用優(yōu)先的全息映現(xiàn)。因為“漢語句法的顯性形式標(biāo)志較少而且使用中缺少強(qiáng)制性,許多范疇不得不借助于語義語用來建立,漢語的構(gòu)式既表句法又表語用或語義”。“睡沙發(fā)、沙發(fā)睡人、在沙發(fā)上睡、睡在沙發(fā)上”,其中“睡”和“沙發(fā)”在結(jié)構(gòu)上分屬動賓、主謂、狀中、動補(bǔ)四類,而認(rèn)知義都是行為和處所的關(guān)系。”。他據(jù)此提倡漢語研究應(yīng)該是“語用優(yōu)先方法論”[7]。構(gòu)式語法認(rèn)為,構(gòu)式本身就應(yīng)改涵蓋語義,語用,功能等特征:
(11)我們坐頭等艙;那邊拐子,流子和兩個武師在賭牌九。(工具)
(12)我父親被發(fā)配新疆了。(地點)
(13)醫(yī)生:先吃點藥,觀察兩天再說。(補(bǔ)足)
(14)我在北京幫人家跑生意。(方式)
隱喻和轉(zhuǎn)喻是思維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8]-[9]。部分“V+NP”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成語化,或至少是詞匯組快(word chunks)其用法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
(15)給我們少爺來碗扒糕,小爺愛吃辣。(轉(zhuǎn)喻:辣的食物)
(16)他居然穿鱷魚。(轉(zhuǎn)喻,鱷魚牌服飾)
(17)自然災(zāi)害加上苛捐雜稅,破產(chǎn)農(nóng)民被迫吃大戶。(方言,隱喻,哄搶地主財物)
(18)我昨天打牌手氣真背,老吃蒼蠅。(隱喻,出錯牌)
中國學(xué)生的概念形成無疑受到漢語作為主題突出語,英語為主語突出語,漢語突出語用英語突出語義的語言影響。受母語遷移影響,中國學(xué)生可能會把“V+NP”結(jié)構(gòu)簡單轉(zhuǎn)換成“V+O”。在學(xué)習(xí)英語句式時,由于句法,語用知識薄弱,詞匯組快理解也容易在漢語中找一一對應(yīng)的漢語詞匯,因此造成理解偏誤,如“kick the bucket”被理解成“踢桶”,“hold water”理解為“存水”。
4.結(jié)語
Goldenberg認(rèn)為,兒童學(xué)習(xí)母語必須依賴積極輸入(positive input),在反復(fù)演練后形成語言構(gòu)式(construction)。論元結(jié)構(gòu)本身構(gòu)成了結(jié)構(gòu)和意義的統(tǒng)一[10]。最初的語法構(gòu)式可能是膚淺的,過分簡單化的(oversimplified)。只有反復(fù)練習(xí),才能形成語言知識的網(wǎng)絡(luò)(mental network)。由此推及二語習(xí)得也遵循類似的模式。不斷接觸相同構(gòu)式,不同意義模式,才能真正掌握英漢“V+NP”的內(nèi)涵。
參考文獻(xiàn):
[1]張云秋,王馥芳.受事標(biāo)記過渡使用的優(yōu)選論解釋[J].外國語,2005,(3):23-28.
[2]王寅,李弘.體驗哲學(xué)和認(rèn)知語言學(xué)對詞匯和詞法成因的解釋[J].外語學(xué)刊,2004,(2):1-6.
[3]Taylor,John.R.Cognitive.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J].四川外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05,(9):10-17.
[4]陸儉明.詞語句法,語義的多功能性:對“構(gòu)式語法”理論的解釋[J].外國語,2004,(2):15-20.
[5]Goldberg,Adele,E.,Devin Casenhiser.English construction[C].Ms.Princeton University,2005.
[6]張韌.功能解釋與認(rèn)知句法的根本目標(biāo)[J].現(xiàn)代外語,2005,(2):27-34.
[7]劉丹青.語義優(yōu)先還是語用優(yōu)先——漢語語法學(xué)體系建設(shè)斷想[J].語文研究,1995,(2):10-15.
[8]Langacker,W.Ronold. Metonymy in Grammar[J].外國語,2004,(6):2-23.
[9]魏紀(jì)東.認(rèn)知語義學(xué)與認(rèn)知語法:差異與同一[J].外語學(xué)刊,2005,(1):51-55.
[10]Goldberg,Adele,E.Construction:A New Approach to Language[J].外國語,2003,(3):1-22.
本論文為南京理工大學(xué)科研發(fā)展基金項目“基于語料庫的中國學(xué)者英語學(xué)術(shù)論文定語成分分析”的后續(xù)研究成果,項目標(biāo)號:XKF07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