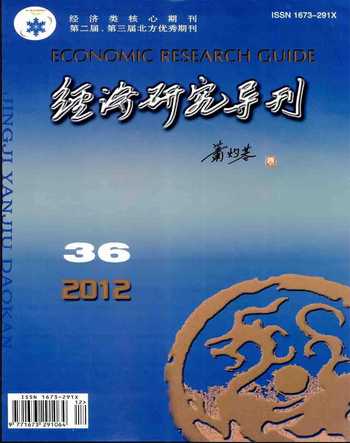從追隨到競爭
孫璐
摘 要:20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眼中的蘇聯(lián)“領導權”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追隨階段(1949—1955),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對蘇聯(lián)領導者地位是絕對服從和仰視的;第二階段為過渡階段(1956年前后),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依然尊重蘇聯(lián)“領導者”地位,但已經(jīng)不再像以往那樣仰視,并且能夠客觀地看到蘇聯(lián)存在的種種問題;第三階段為競爭階段(1957—1959),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對蘇聯(lián)領導權威的“心態(tài)”已經(jīng)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已經(jīng)開始與蘇聯(lián)展開了爭奪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競爭。
關鍵詞:中蘇;“領導權”;社會主義陣營;追隨;競爭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6-0236-03
20世紀50年代,與一般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相比,中蘇關系存在著某種特殊性,即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上,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是暗中較勁的。盡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這十年中,不論在領導人講話中,還是官方的文件中都一直是倡導以“蘇聯(lián)為首”。但在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的以“蘇聯(lián)為首”和50年代中后期的以“蘇聯(lián)為首”已經(jīng)有了本質上的區(qū)別。蘇聯(lián)在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者地位的變化,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這種變化也沖擊著蘇聯(lián)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權威和影響力。中國領導人眼中的蘇聯(lián)“領導權”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追隨階段:蘇聯(lián)“老大哥”的絕對權威(1949—1955)
從20世紀30年代起,完成了“造神運動”的斯大林,對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蘇維埃國家,對共產(chǎn)國際和其他國家的共產(chǎn)黨,對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各國,實行從組織上到思想上直到精神上的“ 大一統(tǒng)” 統(tǒng)治,很少有人敢于對這種絕對的領導權威發(fā)出疑問和挑戰(zhàn);雖然20世紀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南斯拉夫同蘇聯(lián)分道揚鑣,但鐵托和南斯拉夫人在很長時間內(nèi)還相信斯大林是不會犯錯誤的,是“ 無辜的”,整個陰謀是由貝利亞集團造成的 [1]。蘇聯(lián)一直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國家,蘇共也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陣營中的領頭羊。
中國共產(chǎn)黨在尚未奪取政權時即提出世界革命應“以蘇聯(lián)為首”。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以蘇聯(lián)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己經(jīng)形成”,“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使之不能發(fā)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統(tǒng)治,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2]1949 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強調(diào):“目前的重要任務,是鞏固以蘇聯(lián)為首的世界和平陣線,反對戰(zhàn)爭挑撥者,鞏固中蘇兩大國家的邦交,和發(fā)展中蘇人民的友誼。”[3]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目前的國際條件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是有利的。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強大的,內(nèi)部是團結的。”[4]
盡管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斯大林曾發(fā)過牢騷、提過意見,但不是向斯大林的權威挑戰(zhàn),而是針對兩黨兩國間一些具體問題的不滿而與之抗爭。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心目中,一直把斯大林尊為朋友、先生、導師,而視自己為他的學生 [5]。自建國后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斯大林和蘇共作為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地位是沒有爭議的,而且是完全擁護的。毛澤東及中共對蘇共和斯大林及其后繼者赫魯曉夫也是心懷敬意的。正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對蘇聯(lián)領導者地位的絕對服從和仰視,使得蘇聯(lián)與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狀態(tài)。中國領導人對于蘇聯(lián)領導權威的無條件服從使得毛澤東與其他領導者們在面對蘇聯(lián)方面的建議和意見時,也采取了步步請示、亦步亦趨的態(tài)勢。
二、過渡階段:依然尊重蘇聯(lián)“領導者”地位 (1956年前后)
1956年前后,中國領導人已經(jīng)開始辯證地看蘇聯(lián)模式和蘇聯(lián)經(jīng)驗,并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蘇聯(lián)模式和經(jīng)驗的不足之處了,正如薄一波回顧的,“從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lián)發(fā)生的事情,包括貝利亞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對農(nóng)業(yè)的加強,圍繞以重工業(yè)為中心的方針發(fā)生的爭論,對南斯拉夫態(tài)度的轉變,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換等,已使中共中央陸續(xù)覺察到斯大林和蘇聯(lián)經(jīng)驗中存在的一些問題。”[6]
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國領導人提出,蘇聯(lián)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正確、合理的關系問題應該有所反思,勸告赫魯曉夫不要試圖用武力去干涉東歐國家的內(nèi)政。作為回應,蘇聯(lián)政府于1956年10 月30 日發(fā)表了《關于發(fā)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lián)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檢討了他們過去在處理兄弟國家關系方面的錯誤,并表示今后將互相尊重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原則,準備同有關國家的政府共同討論一些措施,以避免類似的事情發(fā)生。11 月1 日,中國政府發(fā)表聲明對蘇聯(lián)政府的宣言給予積極評價和支持。認為“這個宣言對于改正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方面的錯誤,對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具有重大的意義” 。聲明指出: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系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 聲明對蘇聯(lián)表示愿意通過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協(xié)商,解決相互關系中的各種問題表示歡迎。同時指出: 在社會主義各國之間,“某些工作人員常常容易在相互關系中忽略各國平等的原則。這種錯誤,就性質來說,是資產(chǎn)階級沙文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特別是大國的沙文主義錯誤,對于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共同事業(yè),必然會帶來嚴重的損害 ”[7]。中國政府通過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分析,既委婉地對蘇聯(lián)處理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批評,也表達了自己對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原則立場。
在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雖然對蘇聯(lián)領導者地位已經(jīng)不再像上一階段那樣的仰視。但是,在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蘇聯(lián)在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地位仍然沒有改變,蘇聯(lián)與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仍然沒有完全不平等的。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中國也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毛澤東在修改《關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時,明確了中國屬于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三、競爭階段:與蘇聯(lián)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1957—1959)
中蘇兩國的關系在這一時期,不僅在實際上,關鍵是在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的心目中都發(fā)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經(jīng)歷了一場嚴酷的黨內(nèi)政治斗爭后,開始掌握權力。而后經(jīng)歷了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后,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影響力急劇上升。中國開始追求與蘇聯(lián)“平起平坐”的地位,關鍵是毛澤東在共產(chǎn)國際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超過了赫魯曉夫。
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平息了蘇共二十大對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所引起的蘇聯(lián)黨內(nèi)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極大思想混亂。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兩篇文章,《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和《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對穩(wěn)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情緒各方面起了積極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來以后,蘇共中央印了20萬冊,全黨學習。第二篇文章出來更不得了了,印了100萬冊。原來都是全世界共產(chǎn)黨學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文件,現(xiàn)在是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學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件,地位發(fā)生了變化。而且到1957年,莫斯科大學哲學博士考試,前提條件是你有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如果沒有讀過,就沒有考試資格。現(xiàn)在我們外交部檔案,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那時候東歐各國的思想非常活躍,一批斯大林,雙方在爭論什么問題,最后爭論不下去的時候,就用一句話結束,就是我們等等,看看中國共產(chǎn)黨怎么說,看看毛澤東同志怎么講 [8]。其次,在波匈事件的處理上,因為赫魯曉夫沒有經(jīng)驗,辦事莽撞,因此,非常倚重中國幫其進行處理,在波匈事件發(fā)生時,劉少奇坐鎮(zhèn)莫斯科,毛澤東在北京進行指導,波匈事件過去后,面對著東歐的反彈情緒,赫魯曉夫又一次邀請中國領導人去進行斡旋,周恩來在這一時期,在東歐各國和蘇聯(lián)之間進行旋風外交,最后就平息了波匈事件后東歐的混亂局面。通過這件事情后,赫魯曉夫非常佩服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如此,中國和中國共產(chǎn)黨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這一點可以從對比毛澤東在1949年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量兩次訪蘇之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態(tài)進行分析。
第一次訪蘇前,毛澤東表現(xiàn)出強烈的訪蘇愿望,從1947年初,毛澤東就先后5次提出要訪問蘇聯(lián),但都遭到斯大林的婉拒 [9]。① 直到1949年11月,斯大林才正式發(fā)出邀請,11月1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回電:“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10]。從上述史實中不難看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是非常急切地希望與斯大林會晤,通過面對面的商談爭取蘇聯(lián)對中國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的。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時,毛澤東和蘇聯(lián)方面的心態(tài)和第一次恰恰相反,毛澤東表現(xiàn)出了沉穩(wěn)的心態(tài),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則表現(xiàn)出了焦急的心態(tài)。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魯曉夫首次訪華時就積極邀請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lián),吳冷西在《十年論戰(zhàn)》中寫道:“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本是早就答應過的。在1956年和1957年初,毛主席一再對蘇聯(lián)駐華大使說,‘我1949—1950年已經(jīng)訪問過一次,我還是要做第二次訪問,但最好是在你們國家元首回訪中國之后我再去。就是說,希望伏羅西洛夫能夠先訪問中國,作為毛主席1949年訪蘇的回報。毛主席說:‘這以后,我就可以去蘇聯(lián)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向中國人民交代得過去,不要老是我們的國家元首往蘇聯(lián)跑,而蘇聯(lián)國家元首不來,那樣對中國老百姓就不好說。” [11]于是1957年1月,毛澤東正式向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提出邀請對中國進行了友好訪問,伏羅希洛夫在訪華期間又一次向毛澤東提出了訪蘇的邀請。伏羅希洛夫回國之后蘇聯(lián)黨和政府再一次正式邀請毛澤東訪蘇的時候,毛澤東才回電答應再次訪問。
此外,在1957 年的莫斯科會議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參加莫斯科世界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文中已經(jīng)提到了,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儼然成為了共產(chǎn)主義陣營中的“領袖”,但是,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仍然多次提及“以蘇聯(lián)為首”或“以蘇共為中心”。使得赫魯曉夫非常感激,毛澤東在會見赫魯曉夫時說,我們所以提出以蘇聯(lián)為首,是因為只有你們才能領頭,你們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搞了四十年社會主義。赫魯曉夫表現(xiàn)出少有的“ 謙虛”,提出以蘇中為首。毛澤東說,兄弟黨之間是平等的,但在為首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跟你們平起平坐,我們還差得遠。我們中國為不了首,沒有這個資格。如果以我們兩個為首,我們是負擔不起這個責任的。其實,毛澤東的倡議正合赫魯曉夫的心意。因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加上波匈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沖擊,使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威信下跌到最低點。習慣于充當領導者的蘇共領導人欲借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機,讓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齊集莫斯科,按照蘇共的意圖為國際共運制定統(tǒng)一的綱領和路線,重樹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威信,恢復其領導地位。雖然中蘇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存在分歧,盡管很多東歐國家對于蘇聯(lián)存在很大的疑慮,但從國際共運的大局出發(fā),經(jīng)過毛澤東的努力,中國黨提出的“ 以蘇為首” 獲得了與會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們的認同,并寫進了《莫斯科宣言》中 [12]。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對蘇共領導人發(fā)泄郁積于心的怨氣,說第一次訪問蘇聯(lián)時不偷快,“‘兄弟黨,那是一句話,講得好聽,實際上“不平等” [13]。稱贊這次莫斯科會議改變了過去對兄弟黨的不平等態(tài)度,能平等相待,共同商量問題,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這種關系。通過中共的努力,黨際和國家平等原則寫進了《莫斯科宣言》中。《宣言》規(guī)定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關系建立在“ 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國家獨立和主權、互不干涉內(nèi)政的原則基礎上”。“以蘇為首”并非“以蘇聯(lián)為尊”,如過去那樣任何問題由蘇共說了算,而是對其職權范圍加以限制并建立在各國黨平等的基礎之上。這次會議使毛澤東追求的平等在紙面上得到了落實。
1957年開始,蘇聯(lián)開始逐漸喪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絕對領導者地位,中國領導人對蘇聯(lián)的權威也不再是絕對服從和仰視了,蘇聯(lián)與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逐步走向平等,盡管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國仍然堅持以“蘇聯(lián)為首”的口號,但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對蘇聯(lián)領導權威的“心態(tài)”已經(jīng)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已經(jīng)開始與蘇聯(lián)展開了爭奪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競爭。
四、結語
蘇聯(lián)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在這十年中是發(fā)生著變化的。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對于斯大林的批判,加上波匈事件、1957年反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沖擊,蘇共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陣營中的威信下跌到了最低點。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在應對蘇共二十大造成的思想混亂以及幫助蘇聯(lián)處理波匈事件的過程中,不僅在共產(chǎn)主義陣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在社會主義政治和理論方面還走在了蘇共的前面,逐步坐上了與莫斯科共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寶座。對于中國來講,蘇聯(lián)的領導地位意味著權威、權力和正確性。中蘇兩國兩黨地位的相對變化必然會使得中國領導人在面臨蘇聯(lián)影響的時候,所受影響程度和表現(xiàn)方式是不同的。
參考文獻:
[1] 王逸舟.赫魯曉夫與我們的時代[J].世界歷史,1989,(3):44.
[2] 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9-1260.
[3] 毛澤東.抵達莫斯科時在車站的演說[Z],1949-12-16.
[4] 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2.
[5]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7-658;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G]//毛澤東文集:第5卷,P260;毛澤
東.在莫斯科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大會上的祝詞[Z],1949-12-21.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M].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1998:472.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6—1957) [C].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148-150.
[8] 沈志華,主講人,呂崢,整理.從毛澤東兩次訪蘇看中蘇同盟變化[J].文史參考,2011,(3):42-44.
[9] 袁南生.毛澤東與斯大林、蔣介石[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Z],P135.
[11]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95.
[12]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年中蘇關系回憶錄: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社,1999:100-132.
[13]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Z],1957-11-14.
[責任編輯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