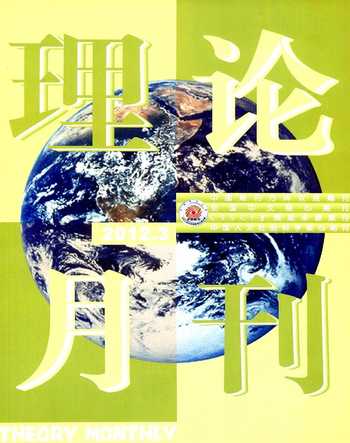二元社會及其權力制約
王建芹
摘要:有限政府作為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思潮背景下的一種制度性建構,通常被視為憲政文明制度內涵下界定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的政治表達,其文化基礎和思想源流內生于上古歐洲和近代西方特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及其制度實踐。而西歐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以來以圣俗二元分立為基本特征的政治文化傳統,蘊生了他們審視國家、社會、個人三者權力關系的思維方式、政治心理和價值取向,并外化為一種政治與社會秩序。這一特有的文化積淀建構了西方憲政文明的歷史基礎,從二元社會及其二元政治文化的視角研究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承繼。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思考人類憲政文明的歷史淵源,同樣也可以對當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提供一個更寬泛的視野。
關鍵詞:二元社會;權力制約;有限政府;憲政;基督教
中圖分類號:D502文獻標識碼I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3-0099-03
在一個社會共同體內,平行存在著兩個相對獨立的權力體系。兩種權力體系有著相互交叉但相對獨立且性質不同的權力范圍,這是歐洲中世紀一個獨特的政治景觀,由此出發,演繹出歐洲特別是西歐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以來以二元分立為基本特征的政治文化傳統,亦可稱之為二元社會。這種二元分立以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分立為基礎,表現為教會與世俗國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相互分立,并體現在教會與國王、國王與封建領主、國王與市民、市民與封建領主之間不斷的權力斗爭和權力制衡過程中。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社會呈現出一種權力體系多元的政治文化生態。
二元分立的政治文化引致的重大社會影響,就在于沒有一個絕對的最高權力的存在,任何一種權力都要被另外的一種或幾種權力所制衡,它構成了近現代西方以權利保障和權力制約為核心的憲政理念和有限政府理論及其制度設計的社會文化基礎。
一、西方權力制約理論的思想源流
西方權力制約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復雜的歷史和理論背景,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時期思想家們的哲學思考及其政治實踐。進入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則將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進行了二元分離,并通過教權與王權的斗爭限制了世俗國家的政治權力,中世紀中期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出現則使得西歐社會的兩個二元分立直接為資本主義分權理論與實踐提供了社會基礎。
嚴格說來,古希臘早熟的政治文明形態盡管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豐富的哲學思想與政治理念,但尚未形成系統化的分權學說。一般認為,古希臘的分權政治實踐并非刻意的政治設計的結果,而是其特殊的城邦產生機制所造就的,也就是說,原始國家形態的城邦的產生直接源自于氏族社會,由于未受到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干涉,在其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原始社會那種人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理念直接被吸收和借鑒,亦即形成原始的分權政治觀。進入羅馬共和國時代以后,這一政治設計既為共和國政體所吸收,更為共和國在一個更為廣大的地域范圍內實現統治進行了適應性改造,進而為古代分權理論的產生提供了系統化素材。羅馬思想家波里比阿是最早以理論形式創立分權學說的,其學說的思想來源既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和混合政體學說,也借鑒了羅馬數百年成敗興衰的國家政治實踐,波里比阿的貢獻在于指出了國家的權力必須合理地分配于不同的部門,部門之間的權力既要保持張力也要保持制約,更要保持某種平衡。波里比阿是混合政體論的積極推崇者,他認為,任何單一政體的缺點,在于它的不穩定,單一政體只能體現一個原則,就其本性而言,這一原則容易蛻變為自己的反面,而混合政體其優點主要是限制權力的幅度,在幾種權力機構之間形成穩定、協調的關系,從而有助于國家的強盛。到西塞羅那里,則更系統地設計了國家各權力機關之間相互關系的模式,其核心是權力的均衡與相互制約,特別是對行政權力的限制,是西塞羅分權學說的亮點之一,他最早敏銳地洞察到了行政權力是一種最危險的權力,因此在各類國家權力之中,限制行政權力是分權制度的最主要目標。
中世紀可以被視為基督教的世紀,基督教一統歐洲社會的精神生活,也深刻地進入了人的世俗生活世界。一部中世紀史,基本上可看成是教權與王權的博弈和斗爭史,雖然說在上層建筑領域,基督教所向披靡,但在教會所代表的神權政治和王權所代表的世俗政治之間卻在現實的世俗政治權力分配上爭斗不休。中世紀早期,王權占有明顯的優勢,教權還不能與王權相抗衡,雙方以合作為主;到了中期,隨著教權的成長,權力斗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狀態,以“教皇革命”為代表,教權占有了一定的優勢;而到了中世紀晚期,隨著歐洲社會民族國家的興起,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的發展,世俗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斷強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市民社會迫切地要求清除市場壁壘和保證交易安全。而這些是羅馬教廷不愿意做的,只有通過強化王權才有可能做到。而夾在封建領主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王需要借助自治城市和市民的巨大經濟支持來強化其權力……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結合迅速強化了王權”。民族國家興起及其王權的強化,客觀上使得體現市民權利要求的近現代分權制度和憲政實踐成為可能,也直接催生了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和“議會主權”政體,從而拉開了近代歐洲憲政實踐的歷史帷幕。
可以看出,西方二元分立的政治文化傳統是歷史的產物。“基督教的二元主義給西方社會帶來了深刻的二元裂變。在基督教統治的一千多年中。這一系列二元裂變是西方社會各種沖突的根源。二元主義是理解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一把鑰匙。”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中世紀兩種權力的長期博弈與斗爭,雙方都需要為自身的權力來源和行使尋找理論依據,從而引發了思想界的一系列大辯論,在持續數百年的辯論與思考中,有關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及其人民主權學說等得到了有效的豐富和發展,權力分立與權力制約的理論體系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得以確立的。
二、二元政治下的國家權力觀與權力的有限性認知
權力分立與權力制約的前提是區分不同性質的權力邊界,在上古希臘羅馬時期,思想家們多是以抽象的思辨方法來認識權力的,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直接探討的是城邦的起源與不同政體之優劣等組織形式上的政權模式,并沒有直接涉及權力自身的本源與性質。亞里士多德以至善作為城邦的目的,將政治問題倫理化、道德化,因而在他的理論體系中,雖然涉及到權力的約束,但與柏拉圖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是,試圖通過政治制度對人的行為約束內化為人們內在的道德情感,亞里士多德盡管提倡法治,但依然為賢良君王的治理留下空間,這一點仍然可以看到柏拉圖“哲學王”思想的巨大影響。希臘化時期和羅馬時期影響最為廣泛的伊壁鳩魯學派、犬儒學派及早期的斯多葛學派均沒有偏離以上范式,更多關注的是國家政體模式以及人生的幸福、意義、價值等相對抽象的哲學性思辨。
用當代的眼光來看,中世紀在人類思想史上是一個缺乏原創性理論和價值的時代,基督教神學世界觀、政治
觀統治了人的精神乃至物質世界,但其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塑造了西歐人的二元世界觀,在人的世俗世界以外,獨立出一個個人相對可以自主的內在精神領地不受世俗政治的干預,特別是宗教改革以后,教會不再具有了上帝與個人之間獲得救贖的“中介”地位,個人可以獨立與上帝溝通,既為個人的精神領地之獨立提供了溫床,同時更直接的影響是,引申到世俗世界,則為個人與國家,市民社會與國家間亦劃定了不可逾越的權利邊界。
以二元社會的眼光來審視權利與權力。國家權力從來都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與歐洲社會上千年的基督教文化積淀有著直接的關系。通常認為,對國家、政府的權力制約思想即源自于基督教觀念中人對自身的罪性和有限性的認知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中對人性中的“幽黯意識”有著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它承認人有不可侵犯的尊嚴;另一方面,它又認為人有原始的罪惡潛能和墮落趨勢。這就決定了其文化觀是以“人性惡”為基本的出發點,由此,基督教文化重視以法律制度去約束人的行為,不主張通過道德的人格去凈化權力,而是強調對危險的權力進行制度上的防范。
早期基督教教父學代表人物圣奧古斯丁以上帝之城和人間之城之兩分奠定了基督教圣俗二元的經典論觀,同時也界定了世俗權力的性質及其邊界。它的超驗性意味著,世俗權力并非絕對,在世俗權力之上還有一個高貴的神圣權力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世俗統治者的權力及來源是受托的和有限的,它的存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替上帝維護俗世間的秩序。同時。正義僅僅是屬于上帝的理性,而原罪則屬于人間之城的所有成員,包括最高統治者也不能例外。既然人是有罪的,更是有限的,因而,世俗的任何權力者都不可信任,需要受到制約,無論他是世俗統治者還是精神統治者。
由基督教原罪觀導引出的對權力及其權力者的不信任,始終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深刻影響著西方社會的思想家們。托克維爾就說過,“無限權威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在我看來,不管任何人,都無力行使無限權威。我只承認上帝可以擁有無限權威而不致造成危險。””美國建國之父之一的麥迪遜也異常直白地指出:“不應信任所有的當權者,這是一條真理。”從本質上說。基督教文化中的教義理論決定了國家的政治權力永遠是有限的,因為它從三個方面限制了國家的政治權力,首先是上帝的尊嚴,其次是教會的尊嚴,再有就是個人的尊嚴,這三種尊嚴被認為是神圣的、不容國家權威所褻瀆和侵犯的。事實上,歐洲的君權從來就沒有像東方的君主那樣擁有過絕對的權力,這樣的一種文化基礎無疑是以保障權利和限制權力為核心的有限政府理論及憲政思想得以傳播、憲政制度得以生成濫觴的內在基因。
關于國家(政府)權力的有限性,基督教是從三個方面來認識的,其一,世俗生活與精神生活。在基督教的神學政治中,盡管認為世俗國家是不可或缺的,但卻是一種“必要的惡”,世俗國家本身不具有終極的目的,它只是人類向更高一目標亦即“上帝之城”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因此國家不能以神圣價值的承擔者自居,國家的權力只能限定于世俗領域而不能進入人的精神生活即信仰領域。這一觀念自奧古斯丁起便成為基督教教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其二,宗教改革特別是加爾文新教更加強調人的罪性與淪落,也正是由此出發,基督新教發展了基督教教義中平等觀的意義,認為人既是平等的同時又是不平等的,平等是因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且罪無差等,皆需要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不平等是在于一部分人在世俗社會中是屬于統治者而另一部分人則屬于被統治者。世俗社會的現實安排意味著不平等雖然無法更改,但從人的罪性而言,統治者也必須受到統治,從而達到終極平等的目的。引申到社會政治層面,就意味著統治者的世俗權力同樣需要受到制約;其三,基督教認為上帝賦予了人一些最基本的權利,例如生存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以及財產權等一些“基本人權”,這些權利是屬于絕對的權力,國家包括其他人都無權剝奪與干涉,國家的作用在于在被治之民的同意下維護這些權利。這一觀念既為后來的社會契約論及其人民主權學說提供了思想基礎和養分,也為界定國家的世俗權力邊界及其有限政府理念的生成提供了依據。
三、二元社會建構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文化根基
二元社會帶給西方的最重要思想成果是自由主義,它構筑了西方政治學理論的主流。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學說,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一種運動。它的理論體系大體上由歐洲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個人主義、自由、平等、民主、社會契約理論等若干原則構成,但自由主義的理論內核則是建構在對個人權利與國家(政府)權力的界分之上。可以說,近現代乃至當代西方的一系列政治社會思潮都與自由主義內在地具有直接的聯系,是在其基礎上派生的。
二元社會文化及其二元政治觀直接為自由主義思想的理論前提和精神基礎——個人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二元社會在分離了人的精神與物質世界的基礎上,引申出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引申出國家(政府)權力的和個人權利的邊界,“它將一種抽象的、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個人作為政治哲學的出發點,將這種原子式的個人視為國家的基礎和本原,而國家只是個人的集合。它賦予個人以終極價值,個人是目的,國家是保障個人權利的工具。”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幾乎都將人始初的“自然狀態”和“自然人”作為其理論出發點。這一邏輯起點既可被視為一種理論假說,更是與基督教文化中的創世學說以及基督教神學家們在此基礎上所發展出的關于人的自由、平等、獨立等學說一脈相承。因此自由主義者們雖然拋棄了神學政治中有關人的基本權利是來自于上帝所賦予的思想外殼,但依舊承認每個人天生都具有某種基本的權利如生命、自由、財產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等,它是人性的要求,是自然權利,人們在組成國家時并沒有將這些權利交予國家,因而國家也無權剝奪這些權利。這一理論一方面構成了社會契約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則為劃分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的界限奠定了理論基礎。但自由主義理論內涵的側重點和前提首先在于保障個人權利,是通過個人權利的設定來劃分國家權力。由此出發,國家(政府)的權力被嚴格限定在一個不可逾越的紅線之內。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說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即人民主權學說及其社會契約論被視為一種理論假說。但之所以能夠成為資本主義革命最重要的理論武器,與歐洲歷史上基督教文化所造就的宗教情結有關。也就是說,歐洲人的思維方式中始終彌漫著濃厚的個人主義情結,基督教文化帶給人最大的啟示,在于人始終是獨立的,特別是宗教改革以后,由于每個人都被視為一個獨立個體,獨立為自己負責,獨立尋求上帝的恩典與救贖,無論是教會與國家,都無助于個人價值的最終實現。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思想得以植根和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恰恰是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文化現象中所沒有的,這也是憲政文明和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制度能夠首先在歐洲資本主義條件下率先生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
雖然說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以后,神權政治逐漸退隱幕后,教會開始偏安一隅專注于人的精神生活,且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后人們對宗教生活的熱情大大降低,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大不如前,但二元社會的政治文化傳統已深深植根于人的思想深處。或者說,基督教文化積淀所造就的自由主義精神使他們對國家、對政府、對政權權力性質的認識上始終保持著不信任的態度,在選擇國家制度及設計權力體系的思維方法上始終把政治權力的邊界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
17、18世紀自由主義理論的產生,客觀上可以被視為商品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的發育為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政治和社會權力過程中法權要求的理論體現,但其社會基礎則在于傳統的基督教文化排除了血緣政治和地緣政治觀念,這是與東方文化的一種本質區別。
參考文獻:
[1]徐大同總主編,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杜,2006
[2]蔡拓,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體學說[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1
[3]程乃勝,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憲政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陸耀明,基督教與西方市場經濟的互動與互補[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6]萊茵霍爾德·尼布爾,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蔣慶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7]叢日云,在上帝和凱撒之間——基督教:元政治觀近代自由主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責任編輯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