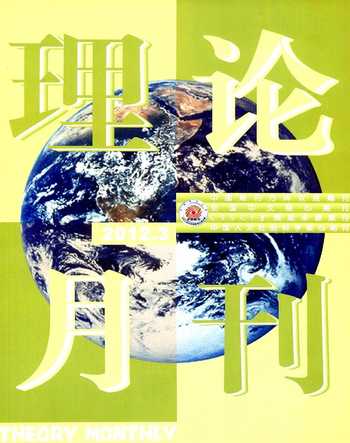都市化的困惑
喻進芳
摘要: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都市小說以其獨具的風采占據了文壇的一席之地,并逐漸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創作中最活躍的題材領域之一。都市小說的繁榮,是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在文學創作領域的一種反映,不斷變化的都市生活為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而都市小說,也在相當程度上成為都市人面對社會轉型而產生的豐富的心靈世界的真實寫照。急速的現代化變革在給人帶來物質富足的同時也伴生著精神上的困惑。
關鍵詞:20世紀90年代;新生代;都市敘述;困惑
中圖分類號:I207.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3-0092-04
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過去的十年里,文壇上有長篇小說的振興、文學期刊的改版、歷史題材創作的紅火、后現代思潮的涌入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而在這多元化的格局中,都市小說以其獨具的風采占據了文壇的一席之地,并逐漸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創作中最活躍的題材領域之一。都市小說的繁榮是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在文學創作領域的一種反映,時代的進步給都市小說的興盛提供了契機。不斷變化的都市生活為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而都市小說,也在相當程度上成為都市人面對社會轉型而產生的豐富的心靈世界的真實寫照。20世紀90年代中期,文壇崛起了一個小說創作群體,該群體被評論界稱為“新生代”或“晚生代”,其成員大體包括邱華棟、何頓、李馮、鬼子、沈東子、韓東、朱文、丁天、陳染、徐坤、海男、張欣、唐穎、張梅等人。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寫過以都市生活為背景的作品,也因為這個作家群的出現。給90年代都市小說的創作帶來了新的景觀,并傳達出新一代都市人的精神脈動。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主要以描繪城市的象征物或以某種時尚為代碼來折射城市生活的“新感覺派小說”:也不同于20世紀90年代初王朔等的小說對于都市外觀的描寫,新都市小說之“新”在于其作品注重的是表現現代都市意識在城市生活中的滲透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都市人的價值觀念、社會評判標準的改變。
20世紀90年代都市小說表現世俗生存狀態與心態所形成的潮流吻合了轉型期都市大眾文化的升溫情景。的確,消費意識對社會的滲透已經無處不在,后現代文化已不可避免地滲透于中國文化中,都市小說所出現的無中心、不確定、自相矛盾、無序性等特征,既是都市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農業走向工商、從傳統倫理走向現代科技過程中價值體系、觀念行為、生存方式不斷解構與更新的真實狀態的反映,也體現了都市小說家在“失范”的社會環境中茫然困惑和找不到意義的無所適從。如果說都市化是現代化的主要標志之一的話,那么,作家們無論是邱華棟筆下的都市邊緣青年,何頓筆下的都市普通市民,還是張欣筆下的都市白領女性,無不表現出同一主題: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困惑。不僅是他們筆下的人物面對陌生的都市感到困惑,而且邱華棟本身作為城市的“闖入者”,何頓自己作為都市的普通市民,以及張欣作為長期居于都市的女性同樣對急速的現代化變革感到困惑。概括起來,都市人的困惑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失落的憂慮
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使被淹沒的“現代化”底蘊水落石出。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對于長期束縛于集體中心主義的中國人,首先具有解放意義:它把人們從單一的集體中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投放到了非中心的市場自由運動中。邱華棟筆下的人物從某個暗淡的異鄉闖入都市,用知識換取財富;何頓筆下的普通市民在市場經濟時代奮發謀財而暴富:張欣筆下那些在經濟大潮中搶灘的城市白領麗人,他們都是改革開放自由空間的擁有者,通過自己的奮爭表達了個人或個人化的存在。但是,作為現代化生存最基本內容——市場,在為人提供自由競爭的同時又以技術進步和數量統計對個體生活進行全面的滲透與控制,最后市場或市場性以它無限地擴張。在為個體提供可能性的無限空間的同時,又成為對個體現實的壓抑。因為當20世紀80年代的欲求在90年代變成現實,并且被超越需求地給予時,現代化就表現出它的負面影響:自我的失落。生命在張揚的過程中受到物欲主義的阻礙和壓制,生命于是扭曲、變形,變得無奈和焦灼,變得無所謂,失去意義。邱華棟筆下的“拉斯蒂涅式”的青年,無論是編輯,畫家,還是詩人,都像《城市戰車》上的一個有機構成,他們隨著戰車一起飛旋,每時每刻都感受著一種自我放逐的清醒的痛苦。邱華棟曾說過:“我的許多朋友在外企、電臺、電視臺、大型國有企業里奮斗有成,月收入可觀,有房有車,在北京的所有場所都能呆,在這樣高的消費水平下他們不僅承受得起,而且過得挺好,他們似乎再也沒有什么煩惱。但是,有一天。我的一個年收入百萬元的朋友突然對我說:‘活著挺沒勁的。華棟,真虛無呀!”‘虛無這個詞很厲害。很可怕,從它的口里出來更是如此:他什么都有,他仍然感到虛無。人好像總是在得失之間,表面的得失下是否掩蓋了什么更為真實的東西?”邱華棟這里說的就是一種物的獲得與精神的失落。那些在物質性層面上已經生活得夠好的人,一旦進入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層面,他們的生活又不夠美好,他們沒有為自己找到精神的家園,他們仍然處在流浪的途中。《公關人》講述了一個闖入城市的成功者的故事。這樣的人物在邱華棟小說中不太多見,一般來說,他的人物多半屬于掙扎、沉淪加奮斗的一類。男主角w有著一個標準的成功者所擁有的一切:外企公關負責人的白領身份。年薪七萬元之巨的優厚收入和一個美滿的家庭。可W卻突然失蹤了,消失在它的面面俱佳的公司和家庭之外。“我”受W妻子的請求尋找他的下落,最后在一間裝滿塑料模特兒的屋子里找到了帶著面具死去的W。這個情節顯然有卡夫卡式的荒誕,小說揭示了W在其公關職業中被物化和內心迷失的狀態。表現了城市人的兩難心態:在對物的追求、時尚的追逐與對真我、個性的向往之間的矛盾。除此之外,《直銷人》中“我”的近乎瘋狂的對物的破壞都揭示了生存壓力減小或解除后,人的自我意識的泯滅、心靈感受的磨損和麻木。還有《哭泣游戲》中顯露出的女主人公對自身存在的遺忘等。總之,在邱華棟筆下,精神缺失造成的痛苦一點也不亞于物質缺憾帶來的困苦。
何頓小說的敘述者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或準知識分子,其語調并非熱烈亢奮而是低沉感傷,有時甚至伴隨著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和焦慮感。例如何夫作為啟光集團副總裁,當他那仍執著于藝術的大學同學從遙遠的西北來看他,他卻對之施以冷漠式的嘲諷,以凸現自我的“金錢身份”,而當大學同學走后,何夫的感覺是,“我為之興奮得連續幾個月不能正常入眠的那些——在此前稱得上是一幅美好藍圖的東西,忽然在心里變成了零零碎碎的瓦片”《生活無罪》。《我們像葵花》描寫了馮建軍的從商經歷。這個少年時代就有過不良記錄的孤兒先后被學校、工廠開除,為了滿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成了幸福街第一個開店做生意的人。最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