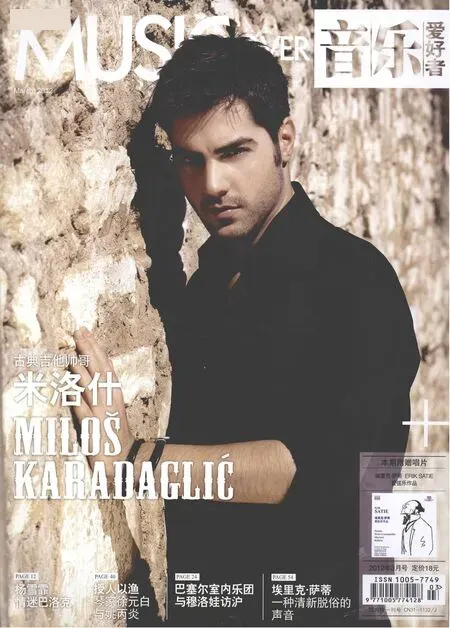王西麟VS肖斯塔科維奇
呂沁融



第一次聽王西麟作品是在2009年的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周《喜劇的對話》中,那棱角分明的音響刻畫和尖銳有力的反諷手法深深震撼了我。音樂會后,大家議論紛紛,有人說他的音樂聽不懂,只覺得辛辣和酸苦,但其抑郁、糾結、緊張和極端的悲憫情緒,卻讓我想到了另一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今天,我將這兩個名字寫在一起,用一些話題連接起來。
我的中國心
1992年,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音樂學博士赫洛波娃(Valentina Nikolayevna Kholopova)在聽了王西麟的《第三交響曲》(Op. 26)之后宣稱:“我在這里發現了世界音樂界尚未發現的我們偉大同胞肖斯塔科維奇傳統的真正生動的發展……兩個偉大民族悲劇的命運聯結在了一起。”
當時大部分中國音樂家接受過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傳統教育,他們的創作并非小眾,但只有王西麟,堪稱繼承了肖斯塔科維奇不屈不撓的“戰鼓”路線,并且,將這種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貫徹至今。
1937年出生于河南開封的王西麟,十二歲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工團,與廣大中國同胞一起經歷了日軍侵華、國共抗日、全面內戰、新中國成立等一系列大事,在炮火的洗禮中,他的心里埋下了堅硬的民族氣節,也造就了日后中國樂臺上的“硬漢”。
這顆紅紅的愛國之心,在他的音樂中表現為宏大的悲涼與反思。王西麟崇拜肖斯塔科維奇,他說當蘇聯、東歐土崩瓦解的時候,那些歌功頌德的作品頃刻之間成了過眼云煙,只有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樂作品,作為斯大林時代的一個見證,以頑強的人格和藝術家的智慧留存。
1985年為紀念肖斯塔科維奇逝世十周年,王西麟創作了《交響音詩二首》(Op. 22),包括《動》和《吟》。在這兩首交響音詩中,王西麟運用了充滿矛盾沖突的嚴謹結構,以及富有哲理性思考的長句式抒情。王西麟運用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風格展現了中、蘇兩位隔代作曲家的心靈共鳴。而完成于1990年的《第三交響曲》更是發展了肖斯塔科維奇的創作傳統,深刻的“沉思”旋律包圍了整部交響曲,在諧謔曲樂章中,帶有獨奏小鼓和打擊樂器的立體般的配器,將這些旋律瞬間變成了如熔巖爆發一般排山倒海似的音響。而那些大提琴的泛音或中音長笛的旋律流動,也表明了柴科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普羅科菲耶夫那些悠長如歌的優美的旋律曾經流過中國的山脈,在王西麟的音樂中留下了痕跡。
面對歷史,抹不去的淚痕
王西麟的音樂不會向你描繪陽光明媚,風光無限。他說,當代作曲家沒有責任和權力粉飾太平,藝術應該是深入最不可深入之事、之境、之情中的。
1999年,中國臺灣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邀請王西麟創作一首交響曲,表達他對即將過去的二十世紀的看法。王西麟深感過去的一個世紀,是迄今人類發展史上最嚴峻酷烈、最激烈動蕩也最富有顛覆意義的一個世紀。這部寫于二十世紀末的交響曲,不想給人以廉價的安撫,而是要撕開所有人的傷口,直面沉重的歷史。
《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的大賦格,效果類似于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描述人類對生命長河的追溯,交織著凄苦、迷離、困惑、思索和企盼,而突然間,樂隊鋪天蓋地一陣“猛砸”,將前面的賦格蹂躪殆盡。即使到了第四樂章,美夢破碎的嘆息聲中,和希冀的縹緲相對照的依然是壓迫得人難以喘息的狂躁勢力——讓人難以理解的如此執拗的“猛砸”,無休無止!
為何不表現希望?這是所有聽過《第三交響曲》和《第四交響曲》的人共同的詰問。面對質疑,王西麟做出了反思與解釋:“我反復思考,在我的心中希望是有的,因為生命在繼續,而生命是永恒的,人類只要有生命,就一定有希望;但希望不是盲目的,希望來自于反思。”他通過音樂有意在提醒聽眾:藝術不能回避真實的生活和歷史,對真理的憧憬必須建立在深刻的反思意識之上。老王在他的時代面前舉起了一面鏡子,鏡子里照出的是抹不去的淚痕。
保衛列寧格勒
對于俄羅斯來說,二戰時期衛國音樂的最高象征就是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Op. 60,1941年)。
1941年到1944年,是蘇聯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只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在被圍困的九百天中,城內饑餓倒斃者僅官方統計就有六十萬人。就是在這樣的極端環境中,肖斯塔科維奇創作了這部作品。樂譜被裝入戰斗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只來了二十個人,一半的樂手都是被擔架抬來的,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僅經過一次十五分鐘的排練后,《第七交響曲》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地完成了演出。
《第七交響曲》的聲音通過廣播傳到了每一個戰壕,對蘇聯軍民士氣的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斯大林將它宣傳為反法西斯的頌歌,并得到了盟國的好評。1942年7月19日,數百萬美國人在電臺里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宏的音樂,《時代》雜志將作曲家身著消防制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
面對高壓,戴著鐐銬跳舞
其實,當時肖斯塔科維奇在俄國的境遇遠比我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雖然他一度被認為是斯大林的御用文臣,但絲毫沒有寵臣的自由與歡愉。
1934年1月22日,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列寧格勒舉行首演,好評如潮,不久開始在歐美各國公演。他突破原作者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在小說中對女主角殺人犯形象的塑造,創造性地將卡特琳娜·伊斯梅洛娃詮釋為一個富有活力、智慧和美貌的女性,她的幻滅是陰暗、殘酷的俄羅斯商人以及農奴家庭的環境造成的,是社會犧牲品的代表人物。顯然,這部“悲情諷刺劇”中強烈的女權主義傾向和一種道德相對主義隱射了革命后的蘇聯并不理想,這惹惱了一個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很快就退場了。1月28日,一篇題為《混亂代替了音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自然主義情愛場景”“粗俗”“刺耳噪音”“資產階級偏狹趣味”等等,各大報紙和樂評人也紛紛對他口誅筆伐,各地的工人與農民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變成了“人民的公敵”。
在此之前,他一直計劃譜寫一部以社會寫實為主題、歌頌俄羅斯女性的、堪與《尼伯龍根的指環》相媲美的歌劇,而這一切都不再有可能——政治強壓下的藝術,稍有不慎就被列為反動,他那充滿活力的幽默諷刺與異想天開式的戲劇創造力,被無情地囚禁。《鼻子》(1928年)和《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成為了他歌劇領域的絕唱。憤怒、恥辱和緊張令他透不過氣,他對友人格里克曼說:“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斷,我還可以用牙齒咬住筆繼續譜寫音樂。”
肖斯塔科維奇如同戴著鐐銬的舞者,邊跳邊流血,卻忘我肆意。在他一生創作的十五部交響曲中,仔細聆聽,你會發現他們有除了官方給予的標題以外的東西。哪怕是《第五交響曲》,官方對它的定義是充滿歡欣與光明,但與肖斯塔科維奇處境相似的作協主席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聽出了異聲:“《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說與不說
王西麟和肖斯塔科維奇都不善于阿諛與粉飾,政治都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但性格上的迥異也造成了他們各自作品命運的不同。一個疏狂,一個冷靜;一個管不住嘴,一個則咬緊牙關。
王西麟是中國樂壇公認的狂人,也從來不計后果地表述他犀利的看法。“文革”期間,由于激烈批評當時的文藝方針,他受到了嚴酷的政治迫害,下放山西長治達十四年,其間被監禁、管制、勞役和批斗,一度喪失了作曲的希望。然而他并沒有吸取教訓,1999年,在北京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眼看《第四交響曲》就要隆重首演,他在演出前的一席演講,卻使這部作品再次冰凍,直到2004年才在“上海之春”音樂節悄悄上演。
“我鉚足了勁,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說出來!”——我想,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實隱藏對認同感的苦苦追尋。但是這種“非說不可”的態度,卻使得他的作品命運多舛。而肖斯塔科維奇則恰恰相反。
在風云變幻的時代,不表態成為一種最成熟也最無奈的政治姿態。肖斯塔科維奇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他給人的印象永遠是戴著眼鏡,淡薄無力,謹慎嚴肅。但沉默不等于無態可表,實際上,在他看似怯懦的外表下不時迸發出鋒芒。類似于中國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用懦弱偽裝無畏,他用機智化解暴君的猜忌。
肖斯塔科維奇一直“反戰”。1943年的悲劇交響樂《第八交響曲》,是他試圖表現人民的痛苦、反映戰爭可怖的重要作品。它在歐美各國受到重視,但蘇聯音樂界的反響卻極為冷淡。二戰一結束,他立刻寫出了大型作品《第九交響曲》(1945年),再次與戰勝國的期望唱反調,它并不是一部歡慶勝利的凱旋交響曲,而是具有古典主義和抒情喜劇色彩的諷刺音樂,其中充滿了對陣亡同胞的悼念以及對戰爭的反思。1955年,在被反猶太主義惡浪沖洗過的俄國,他公開發表了《猶太組歌》來為猶太民族發言。1958年9月,匈牙利暴動過去兩年不到,由葉普根尼·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在列寧格勒音樂廳奏響了他的《第十一交響曲》,自然主義的音樂寫作手法隱射了那個時代的人民與統治者的生存現實。這一部部尖銳的作品,不僅成功上演了,也如同投進專制體制的啞雷,悄無聲息地炸開了黑暗的深淵。
這些逆流悲歌,是用音符交織出的吶喊,是獻給全體受害者的墓志銘,其中充滿了肖斯塔科維奇對于普世大眾的愛。多年以后,這些作品里真摯的情感和精湛的技藝,終于讓西方一度側目的樂評家們肅然起敬。
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繪畫大師吳冠中曾說:“藝術觀點同政治觀點之間的矛盾,不是我能解決的,這是我痛苦的根源,也是我無奈奮斗的一個焦點。”是焦點,但不是全部。藝術家的痛苦和思考也許無法指向解決之道,但是藝術品的價值卻因此變得真實且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