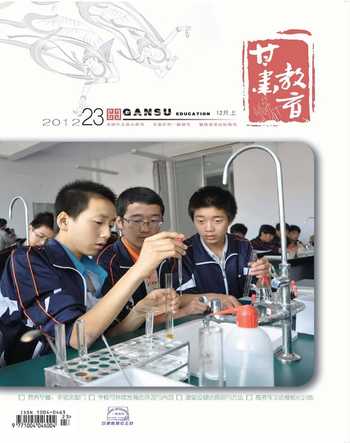“幸福”臆說
文雨
不知何種原因,一段時間以來,幸福與否成了各種媒體熱炒的話題,從央視記者滿世界地追著人問“你幸福嗎”,到一些地方政府把公眾幸福指數列入施政目標,讓人有了某種恍惚感,就像一個被忘卻了很久的事物,忽然被人不斷提及,一夜之間身價百倍。假如“幸福”是一種商品,可以被囤積,被炒作,被倒賣,一定會和大蒜、綠豆一樣,很快變成天價。
天天有人說幸福,也就不由你不去試著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但終究理不出個一二三來。也許幸福與否,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每個人只能根據各自的感受來做出判斷。況且生活原本就是五味雜陳,不管什么境況,沒有人能夠做到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感到自己幸福得不得了。對窮人而言,餓肚子的時候能吃上一頓飽飯,寒冷的時候能有棉衣穿,就會感到十分幸福;而對于一些富人來說,即使天天山珍海味、狐裘錦袍,可能也感受不到所謂的“幸福”。所以,硬要追著別人問“你幸福嗎”,本身就很無厘頭。
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幸福觀”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把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等物質的享受作為低層次的幸福的話,諸如公平正義、自由平等、人格尊嚴、人生價值、理想追求等,可能就屬于高層次的范疇。對于那些“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有識之士而言,常常是“進亦憂,退亦憂”,他們的“幸福指數”往往是與國家的前途命運、政治的清明與否、百姓的安危冷暖息息相關,而與自身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物質條件的好壞沒有多大關系。就像杜子美所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樣的品格和這樣的情懷,早已超越了個體意義上的幸福追求,注定只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了。
最近一項有關職業幸福感的調查顯示,既穩定又收入高的職業被認為是最具幸福感的,其中公務員排第一,其次是教師、藝術家、高管等。顯然這是一種趨利的選擇。公務員排第一毫不意外,從“國考”的火暴程度就能得到印證,幾千個人爭奪一個崗位的情況已經司空見慣。但要說當了公務員就一定幸福,那也未必。就像婚姻生活,沒有人不是奔著幸福去的,但持續走高的離婚率向人們展示,婚姻的幸與不幸也是因人而異的。“圍城”之說同樣適用于公務員這個職業,等你進去了,才會發現并沒有想象得那么盡如人意。在這個行當里,郁郁不得志者同樣大有人在,想要超脫實屬不易,更談不上什么幸福感。這和富人的幸福指數并不太高是一樣的道理。再好的職業,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就有“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可說是“此事古難全”。
但當下大學生在擇業上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是值得關注的。如果人人都把干得少、拿得多、有保障、無風險,作為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徑,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作為個體,無論做出怎樣的選擇,似乎都無可厚非,可一旦某種選擇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問題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簡單了。
面對央視記者“你幸福嗎”的追問,莫言說:“我不知道,我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說不幸福,那也太裝了吧?剛得諾貝爾獎能說不幸福嗎?”看來這個問題同樣讓他左右為難。按媒體設定的標準來看,莫言無疑具備了“幸福”的所有要素,之所以感到“不幸福”,是因為他已經不是原來的莫言,已經不能完全自我地、自由自在地進行創作或者不進行創作,作為諾貝爾獎得主的莫言,必須生活在人們的審視和期待中,能不憂慮、能無壓力嗎?自然也就難以安然享受一般人眼中的那種“幸福”。
所以,從世俗意義上講,你無法理解一個人為什么幸福,也無法理解一個人為什么不幸福,因為世上沒有想當然的幸福,也沒有想當然的不幸福。兩千多年前,莊子與惠子在濠梁之上討論的似乎也是這個問題。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曾聽老人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兩家人是鄰居,一家很有錢,但膝下無子;另一家則是家徒四壁,卻有四個兒子。一年的農歷六月初六,按習俗,富人把家里的金銀珠寶、錦緞裘皮拿出來晾曬,借以炫耀。窮鄰居看了,心里不是滋味,無奈之下,父親就讓兒子抬出一張八仙桌,自己端坐其上,由四個兒子每人抬起一條桌腿,在自家院中“巡游”取樂。見此情景,富人嘆曰:“我雖有金銀財寶,可這些東西都是死的,人家擁有的才是活寶啊!”聽了這則故事,該如何判斷他們誰更幸福呢?理性地講,應是各有各的幸福,也各有各的不幸。世上之事,大概難免“魚和熊掌難以兼得”之嘆吧!
記得我們小時候拿著自制玩具,穿著補丁衣服,整天半饑不飽,卻能昏天黑地地開心瘋玩,而現在的孩子大都錦衣玉食,物質條件優越,幾乎什么都不缺,卻不知道玩什么和怎么玩,也沒有多少時間可玩,兩相比較,到底誰的童年更幸福呢?
看來,要想說清“幸福”這檔子事,還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