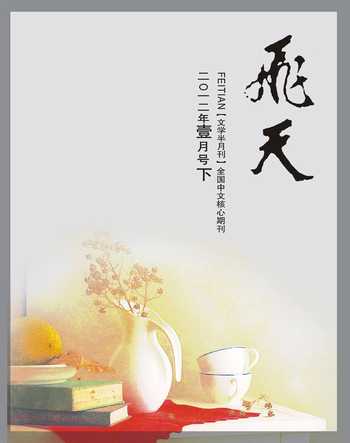從袁雪芬新越劇改革探索民族聲樂的發展思路
越劇形成是在浙東農村,但她的成長卻主要是在30年代的上海。當時上海已是中國人口最多、工商業最發達,又是市民階層人數最多的大城市,話劇、電影在上海出現一定程度的繁榮,為越劇提供了可以參照借鑒的藝術樣式。越劇的全女班在上海相當新鮮,在爭取婦女觀眾上很有吸引力;越劇的浙東語言,在上海完全能聽得懂,越劇戲曲音樂,曲調優美動聽而又比較簡單,利于傳唱,加之,同時期,昆劇的衰頹為越劇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
一、以袁雪芬為代表的新越劇改革
1942年10月起,在話劇、電影的影響下,青年越劇演員袁雪芬自發發起的新越劇改革,在越劇界首次建立起正規的編戲、排戲制度;廢除幕表制,使用完整的劇本;廢除衣箱制,參照古代繪畫,根據人物身份設計服裝;打破傳統的舞臺形式,采用立體布景、油彩化裝、燈光、音響,率先在中國戲曲中建立了編、導、演、音、美的藝術機制。使越劇從一個地方小劇種發展成為成熟的大劇種。
(一)傳統唱腔的革新
1942年10月,袁雪芬倡導越劇改革,劇目多數為悲劇,袁雪芬從人物出發,在傳統唱腔音調進行中,頻繁地、重復地運用變音,就是7音,形成一種悲哀哭訴的唱腔音調,逐漸形成一種激進的、下行的旋律的特點,呈現出哀怨深沉的唱腔格調。
(二)創造尺調腔
袁雪芬在1943年11月演出《香妃》時與琴師周寶才合作,初步形成了尺調腔的雛形,實現了在唱腔方面更大的突破。袁派就是在尺調腔的基礎上形成的,是越劇最早出現的流派之一。
(三)創造“男調”和“六字調”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劇目題材的擴大,袁雪芬在塑造新的人物的音樂形象時又有新創造。1950年演出《相似樹》的時候,袁雪芬與劉如曾合作,吸收越劇早期男班藝人唱腔因素,創造了能表達熱烈、急切、猶豫、不安等復雜感情的“男調”;1958年在演出《雙烈記·夸夫》時,又創造了新型的“六字調”。
(四)全方位的借鑒與改革
在音樂上發展基本曲調,基本曲調不夠用時吸收兄弟劇種的曲調以及鑼鼓經。利用“移植”、“嫁接”形成自己的腔調體系和藝術風格,大大豐富了音樂表現力。表演實踐和舞臺美術中,直接借鑒話劇和電影的表現手法,強調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個性表演;同時誠心向昆劇學習,努力加強舞臺動作的舞蹈化和姿態美,以加強動作的藝術表現力;同時注意表演風格的創新,努力發展個人在表演上的獨創性。
二、民族聲樂發展
對新越劇改革的借鑒
戲劇的問題同樣也是中國民族聲樂的問題。我國傳統民族聲樂來自于戲曲、民歌、說唱等民間藝術,多元化的民族聲樂豐富多彩,博大精深,是我國民族聲樂創新和發展的不竭源泉。但是,目前我國民族聲樂發展現狀存在著:“千人一面”“萬人同腔”,在同一種聲音,同一種腔調、同一種風格中比高低,演唱缺乏個性和創新。民族音樂和民族歌劇的題材也相對比較單一等,造成了和女子越劇時期相同的局面“無有新的創造”。探索新越劇改革和舞臺音樂實踐正好為中國民族聲樂傳承、創新和發展提供一種思路和借鑒。
(一)強烈的舞臺創作欲望
袁雪芬致力于唱腔的豐富和變化,不斷創作出眾多的如[尺腔調]一樣的新曲調。可見,創新欲望和創作沖動對民族聲樂舞臺表演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縱觀現在的民族聲樂在這兩方面都普遍存在著缺失,有的表演者以模仿他人為標準,在無形中形成了“隨大流”的演唱風格。還有的演員滿足于現有的成就,在藝術創作中他們自然會沿著原來已經設定好的人物音樂形象去機械的表演,就更不要提對與人物音樂形象的深刻理解后產生的人物創作欲望了。沒有對人物創作欲望的沖動即使給他們一個新的音樂人物形象,他們也只會按照作曲家給出的原譜進行機械的演唱,更不要說對人物創作欲望的沖動了,更不要說去思考對人物音樂形象解決的方案了。
(二)二次創作能力和實踐
袁雪芬說,“戲曲是聲腔的藝術,因為聲腔對塑造人物幫助很大。”她在自傳中的提出“要求演員在塑造人物語言唱腔能力上唱出人物的心聲”這取決于演員的二次創作能力。袁雪芬的這個主張具有前瞻性,就是要在深入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后用自己有分寸的演唱和表演(包括念白)來塑造人物,進而完成對人物的完整創造。
袁老還主張“演員要以獨特的潤腔來刻畫人物的內心”這個主張在中國的民族歌劇《白毛女》中充分體現。
袁老還主張“演員的唱腔貴在創新,不能吃老本,不能滿足與學會幾句流派唱腔,博得幾聲廉價的掌聲作為終生受用”。這個主張是對現在一些民族聲樂專業的演員的一種提醒。有的民族聲樂專業的演員,在演唱風格和唱腔處理上“吃老本”,他們滿足于自己在藝校和大學學習期間學習的一些演唱技巧和風格,覺得這樣已經足夠自己使用了,長期對自己一成不變的風格進行更新,沒有變化,更沒有革新,只是滿足于“博得幾聲廉價的掌聲作為終生受用。”
(三)傳承和創新是民族聲樂發展的兩大動力
著名聲樂教育家鄒文琴教授所言“民族民間藝術是民族聲樂專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寶庫”重視對民族民間藝術的學習才可能實現在民族聲樂藝術上的“原始積累”,推動事業向前發展。
袁雪芬能夠成為戲曲界的一代大師,就跟她兼收并學分不開。她在科班時期就大量學習紹興大班得武戲和大量的唱段,從而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紅伶,(解放以前)她堅持在演出之余盡量去觀摩其他劇種和話劇演出和觀看電影,從中吸取了大量的養份,將其轉化為豐富的音樂語匯,以使其在不同的人物身上的到較好的運用。在袁雪芬的新越劇改革中,較好的解決了繼承與創新的矛盾。中國的傳統戲曲沒解決寫實和寫意問題,而袁雪芬努力要求要演出真實情感,向話劇和電影學習,寫實一些。早期變革花樣翻新很多,有陣子還取消了水袖,后來又加上了,因為袁雪芬覺得,越劇不能是簡單話劇加唱。袁雪芬那陣子把昆曲“傳”字輩的演員都請到劇團,她覺得自己武術、舞蹈功底都不夠,所以專門從昆曲那里學表演,后來袁雪芬總說,昆曲和話劇是越劇的兩個奶媽。
因此我們在發展民族聲樂的時候,一方面要尊重和尊循既有的民族聲樂音樂藝術規范(即在民族調式的范圍內),另一方面,對既有的民族聲樂音樂規范進行創新發展和不斷的完善上,發展具有民族聲樂特色的花腔作品和具有時代特色的作品。
(作者簡介:劉珂嘉,四川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09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