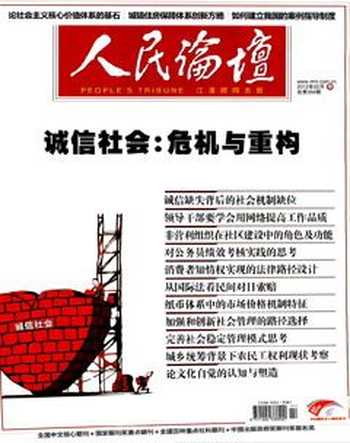美俄削減戰(zhàn)略武器新條約的局限性
趙騫
【摘要】基于建構(gòu)主義的有關(guān)原理,對(duì)美國(guó)和俄羅斯在冷戰(zhàn)后的關(guān)系以及美俄削減戰(zhàn)略武器合作的走向進(jìn)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美國(guó)與俄羅斯關(guān)于進(jìn)一步裁減和限制進(jìn)攻性戰(zhàn)略武器措施的條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美俄雙方難以達(dá)成對(duì)核武庫(kù)進(jìn)行較大規(guī)模實(shí)質(zhì)性削減的協(xié)定,其根源在于美俄各自對(duì)于對(duì)方“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身份的認(rèn)同。
【關(guān)鍵詞】美國(guó)與俄羅斯削減戰(zhàn)略武器新條約建構(gòu)主義身份認(rèn)同
2010年4月8日,美國(guó)和俄羅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簽署了《美國(guó)與俄羅斯關(guān)于進(jìn)一步裁減和限制進(jìn)攻性戰(zhàn)略武器措施的條約》(以下簡(jiǎn)稱“條約”),以取代兩國(guó)于1991年簽署并于2009年12月5日到期的《第一階段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美俄雙方于2010年5月《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huì)召開(kāi)前夕簽署削減戰(zhàn)略武器新條約,表達(dá)了雙方積極合作的意愿。但從建構(gòu)主義角度解析,筆者認(rèn)為美俄在削減戰(zhàn)略武器新條約中的沖突及博弈,其根本原因在于美俄間的“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認(rèn)同。
美俄“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身份建構(gòu)
建構(gòu)主義代表人物溫特認(rèn)為,物質(zhì)力量的重要性必須得到肯定,但物質(zhì)力量只有在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才有意義。建構(gòu)主義理論框架下的利益依賴于“認(rèn)同”,認(rèn)為“有目的之行為體的利益是由共同的觀念建構(gòu)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①。而“認(rèn)同”(或“身份”)指的是行為體通過(guò)與他者的互動(dòng)實(shí)踐而形成的自身所具有并展示的區(qū)別性形象,它由行為體共有的理解與期望建構(gòu)而成。建構(gòu)主義以“身份”界定國(guó)家利益,指導(dǎo)國(guó)家行動(dòng)。
條約簽署的延遲、條約中的模糊算法以及對(duì)超強(qiáng)核威懾力的保留實(shí)質(zhì)上是兩國(guó)沖突、制衡與不信任心理在條約中的體現(xiàn)。冷戰(zhàn)后,美國(guó)成為唯一超級(jí)大國(guó),維護(hù)其在現(xiàn)有世界格局下的超級(jí)大國(guó)地位并促進(jìn)世界格局朝著對(duì)其有利的方向發(fā)展成為其國(guó)家戰(zhàn)略的首要任務(wù)。就目前全球安全領(lǐng)域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而言,美國(guó)在總體上無(wú)疑擁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但在核領(lǐng)域,俄羅斯由于繼承了前蘇聯(lián)遺留的龐大核武庫(kù)而擁有制衡美國(guó)的資本,成為美國(guó)強(qiáng)有力的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因此,美國(guó)在核軍控領(lǐng)域始終堅(jiān)持遏制與削弱俄羅斯,擴(kuò)大自身優(yōu)勢(shì)的戰(zhàn)略。在此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背景下,美國(guó)重拾“軍控牌”是有其必然性的。
而俄羅斯在冷戰(zhàn)后陷入重重危機(jī),已經(jīng)失去超級(jí)大國(guó)地位,美俄關(guān)系也總體走向合作與緩和。但前總統(tǒng)小布什上臺(tái)以來(lái),美國(guó)在擴(kuò)大軍費(fèi)開(kāi)支、增強(qiáng)自身軍事實(shí)力的同時(shí),采取了退出《反導(dǎo)條約》,發(fā)動(dòng)阿富汗戰(zhàn)爭(zhēng)、伊拉克戰(zhàn)爭(zhēng)等單邊行動(dòng),并以“先發(fā)制人”國(guó)防戰(zhàn)略取代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威懾”戰(zhàn)略,這一時(shí)期的北約東擴(kuò)也將不少獨(dú)聯(lián)體國(guó)家納入,而獨(dú)聯(lián)體國(guó)家一直被俄羅斯視為自身勢(shì)力范圍,這都引起俄羅斯強(qiáng)烈的危機(jī)感與不滿。俄羅斯自前總統(tǒng)普京執(zhí)政以來(lái)在國(guó)防與軍隊(duì)建設(shè)領(lǐng)域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其軍事實(shí)力得到增強(qiáng),國(guó)民中的民族主義與大國(guó)心態(tài)也日益高漲,其擴(kuò)大地區(qū)影響力,恢復(fù)大國(guó)地位的戰(zhàn)略構(gòu)想必然與美國(guó)的遏制戰(zhàn)略發(fā)生沖突。
與此同時(shí),“9·11”事件之后,美國(guó)大幅調(diào)整全球戰(zhàn)略,防止恐怖主義和確保國(guó)土安全成為布什政府的頭等大事,美國(guó)需要俄羅斯在這些方面的合作與支持。因此美俄關(guān)系總體呈現(xiàn)競(jìng)爭(zhēng)與合作并存局面,但相較于90年代初期以對(duì)俄戰(zhàn)略思想“理想化”和確立以“伙伴關(guān)系”作為對(duì)俄基本政策時(shí)期的美俄關(guān)系,競(jìng)爭(zhēng)態(tài)勢(shì)已日益明顯。而“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國(guó)家身份建構(gòu)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美俄間的競(jìng)爭(zhēng)趨勢(shì)。
以建構(gòu)主義的觀點(diǎn)而言,在美俄關(guān)系的互動(dòng)過(guò)程中,當(dāng)一方把另一方確定為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后,就會(huì)采取相應(yīng)的政策和言行;而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政策和言行會(huì)進(jìn)一步刺激雙方的關(guān)系,形成競(jìng)爭(zhēng)性互動(dòng)。
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身份在美俄進(jìn)一步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中的體現(xiàn)與影響
建構(gòu)主義認(rèn)為,一國(guó)對(duì)他國(guó)的身份認(rèn)定將影響該國(guó)對(duì)他國(guó)的外交行為。從美國(guó)方面看,俄羅斯是其核領(lǐng)域的主要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以及核軍控領(lǐng)域主要的遏制對(duì)象,俄羅斯的身份是“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因此美國(guó)在核領(lǐng)域的對(duì)俄政策必然呈現(xiàn)“競(jìng)爭(zhēng)”與“遏制”的取向。俄羅斯規(guī)模龐大的核武庫(kù)及重建中的軍事投射能力都被美國(guó)視作潛在威脅,而其日益提高的國(guó)際地位及影響也被美國(guó)認(rèn)為對(duì)其霸權(quán)穩(wěn)定構(gòu)成威脅。當(dāng)前,美國(guó)意圖通過(guò)由“無(wú)核世界”倡議取得的道義制高點(diǎn)與輿論優(yōu)勢(shì)、美國(guó)自身的實(shí)力優(yōu)勢(shì)與全球影響力以及削減戰(zhàn)略武器談判的協(xié)商機(jī)制,迫使俄羅斯在條約談判中做出更大讓步,借機(jī)削弱俄羅斯的核力量,達(dá)到擴(kuò)大美國(guó)核優(yōu)勢(shì)以及對(duì)俄遏制的目的。
俄羅斯同樣基于美國(guó)是“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身份認(rèn)定,一直試圖將條約內(nèi)容以及條約的簽署與美國(guó)部署戰(zhàn)略導(dǎo)彈防御系統(tǒng)掛鉤。條約簽署前,俄羅斯外長(zhǎng)拉夫羅夫曾就反導(dǎo)問(wèn)題發(fā)出警告,若美國(guó)戰(zhàn)略導(dǎo)彈防御系統(tǒng)開(kāi)始對(duì)俄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性影響,俄羅斯就有權(quán)退出條約。即使在文件簽署后,俄羅斯依然可以在杜馬內(nèi)部利用程序廢止條約的通過(guò),足以說(shuō)明俄對(duì)美的不信任與防范態(tài)度。首先,俄羅斯對(duì)美國(guó)擴(kuò)大霸權(quán)的政策感到不安。作為前蘇聯(lián)主要繼承者的俄羅斯,昔日勢(shì)力范圍內(nèi)接連發(fā)生“顏色革命”、北約東擴(kuò)對(duì)原獨(dú)聯(lián)體國(guó)家的吸收、美國(guó)戰(zhàn)略導(dǎo)彈防御系統(tǒng)的部署以及前小布什政府時(shí)期美國(guó)單邊主義的外交戰(zhàn)略等都令俄對(duì)美的不信任情緒及防范心理日益加深。其次,俄羅斯在軍事領(lǐng)域,尤其是核領(lǐng)域擁有制衡美國(guó)的實(shí)力。俄羅斯擁有規(guī)模龐大的核武庫(kù)及先進(jìn)的核技術(shù),足以利用其軍事實(shí)力對(duì)美國(guó)的“遏制戰(zhàn)略”進(jìn)行反制,在維護(hù)自身安全的同時(shí)為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有利的國(guó)際環(huán)境。最后,俄羅斯希望利用其核實(shí)力以及削減戰(zhàn)略武器協(xié)商機(jī)制作為其提高國(guó)際地位、擴(kuò)大地區(qū)影響力、恢復(fù)大國(guó)地位國(guó)家戰(zhàn)略的一張牌。
雙方相互認(rèn)定為“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國(guó)家身份,在條約的談判進(jìn)程、內(nèi)容、簽署等方面均有體現(xiàn)。首先,條約需削減的核武器種類與數(shù)量有限,無(wú)損雙方超強(qiáng)的核實(shí)力。條約的性質(zhì)是削減進(jìn)攻性戰(zhàn)略武器條約,所謂進(jìn)攻性戰(zhàn)略核武器是指部署好的、隨時(shí)可以發(fā)射的現(xiàn)役戰(zhàn)略核武器,不包括非現(xiàn)役戰(zhàn)略核武器和庫(kù)存的戰(zhàn)略核武器及等待銷毀而尚未銷毀的戰(zhàn)略核武器。雙方出于對(duì)對(duì)方的制衡需要以及不信任心理,力圖同時(shí)維護(hù)兩國(guó)對(duì)于他國(guó)的超強(qiáng)核優(yōu)勢(shì),并未對(duì)所擁有的核武庫(kù)作“傷筋動(dòng)骨”的削減。其次,雙方在核彈頭計(jì)算方法上的規(guī)定可能使實(shí)際裁減數(shù)量少于宣布數(shù)量。最后,條約前途不明。俄雖在美國(guó)部署戰(zhàn)略反導(dǎo)系統(tǒng)問(wèn)題上做出部分妥協(xié),但并未改變其固有立場(chǎng)與抵制心態(tài),并“保留退出條約的權(quán)利”。
由于雙方的競(jìng)爭(zhēng)與制衡心態(tài),對(duì)條約“切實(shí)棄核”的期望是不現(xiàn)實(shí)的。迄今為止,美俄兩國(guó)對(duì)于條約內(nèi)容的制定已達(dá)成一致,條約業(yè)已批準(zhǔn)與生效,兩國(guó)在談判中表露出的協(xié)商意愿、對(duì)核武器的部分削減、對(duì)條約生效的積極推動(dòng)以及對(duì)長(zhǎng)期協(xié)商談判機(jī)制的確立,也確實(shí)不失為積極因素。但必須認(rèn)識(shí)到的是,若美俄雙方相互確立對(duì)方為“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身份認(rèn)同不改變,通過(guò)雙方協(xié)商談判達(dá)成的條約所具有的嚴(yán)重局限性就將長(zhǎng)期存在,雙方所擁有的巨大核力量就不能得到切實(shí)削減。
美俄削減戰(zhàn)略武器談判的未來(lái)走向
建構(gòu)主義認(rèn)為“‘利益是通過(guò)社會(huì)相互作用建構(gòu)而成的。換言之,自身的利益是在與其他人的關(guān)系中確定的,在考慮自身利益時(shí),必須也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②。美俄在削減戰(zhàn)略武器問(wèn)題上難以取得實(shí)質(zhì)性進(jìn)展的關(guān)鍵在于雙方并非以棄核為根本出發(fā)點(diǎn),而是以擴(kuò)大自身優(yōu)勢(shì)、實(shí)現(xiàn)對(duì)對(duì)方的制衡與遏制為目的。建構(gòu)主義把國(guó)家身份和利益看作是一個(gè)發(fā)展過(guò)程,在互動(dòng)性實(shí)踐活動(dòng)中既可以建構(gòu)亦可以分解,“國(guó)際關(guān)系的進(jìn)程是朝著和解和非暴力的方向發(fā)展,國(guó)家在這個(gè)進(jìn)程中可以創(chuàng)建新的國(guó)際體系文化,同時(shí),具有新觀念的國(guó)家也可以分解國(guó)際體系文化”。③美俄目前處于洛克文化體系,即合作與競(jìng)爭(zhēng)并存的文化體系,由于前布什政府執(zhí)政期間推行的霍布斯主義外交政策對(duì)洛克文化體系的存在造成威脅,美俄兩國(guó)關(guān)系在某些領(lǐng)域趨于緊張。但隨著兩國(guó)之間各自觀念的更新和共同利益的逐步增加,以及外部國(guó)際環(huán)境氣候條件的相對(duì)成熟,也不排除兩國(guó)關(guān)系走向康德文化體系的可能。
而在核領(lǐng)域,雙方關(guān)系的好轉(zhuǎn)也是完全可能的。首先,兩國(guó)正探索式地致力于實(shí)現(xiàn)更高程度的政治互信,而這是取得對(duì)核領(lǐng)域合作實(shí)質(zhì)性突破的基本前提。其次,核武器在國(guó)家戰(zhàn)略中地位的轉(zhuǎn)變也是促成俄美就削減戰(zhàn)略武器問(wèn)題達(dá)成實(shí)質(zhì)性協(xié)定的有利因素。核武器在當(dāng)前國(guó)際體系環(huán)境下被用于實(shí)戰(zhàn)的可能性越來(lái)越低,而核材料的遺失與外泄對(duì)國(guó)家安全造成的影響卻日益增大,因此規(guī)模過(guò)于龐大的核武庫(kù)并不利于維護(hù)國(guó)家安全。再次,國(guó)際體系進(jìn)程朝著和解和非暴力發(fā)展的趨勢(shì)不會(huì)改變。美俄在任何情況下爆發(fā)核戰(zhàn)爭(zhēng)都將導(dǎo)致人類的毀滅,因此推動(dòng)核軍控進(jìn)程是必然趨勢(shì)。目前雖然美俄達(dá)成的《進(jìn)一步削減進(jìn)攻性戰(zhàn)略武器條約》仍具有較大局限性,雙方互信依然脆弱,但可以期待的是,條約的達(dá)成將有助于核軍控領(lǐng)域長(zhǎng)期協(xié)商制度的形成與發(fā)展,促使雙方最終達(dá)成一致,對(duì)核武器有計(jì)劃、分階段進(jìn)行實(shí)質(zhì)性裁減。(作者單位: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院)
注釋
①范菊華:“對(duì)建構(gòu)主義的解析”,《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03年,第7期。
②袁正清:“建構(gòu)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國(guó)際政治與經(jīng)濟(jì)》,2004年,第9期。
③[美]亞歷山大·溫特:《國(guó)際政治的社會(huì)學(xué)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2002年,第23~24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