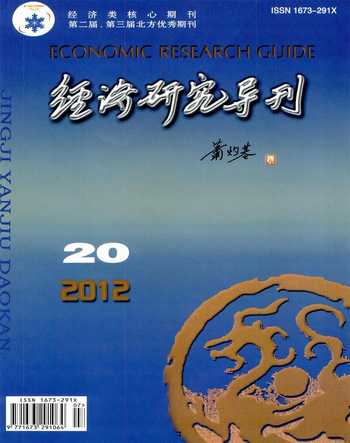論孟子的民本思想
侯佳君
摘要:儒家經典《孟子》一書包含著豐富的民本思想。首先,就民眾、君主及國家政權的關系而言,民眾為本,國君與政權為末。其次,君主和任何國家政權都不可能離開民眾而單獨存在。最后,民眾的安居樂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和前提。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對于鞏固君主政權、推行王道政治等都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孟子民本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時代價值。
關鍵詞:孟子;儒家;民本思想
中圖分類號:B222.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0-0199-02
一、 民本思想概述
中國古代并無“民本”一詞,多數學者認為,“民本”源于《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及《春秋榖梁傳·桓公十四年》中的“民者,君之本也”。“民惟邦本”一詞,孔穎達《尚書正義》注:“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人民是國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盡管中國古代沒有完整地出現“民本”一詞,但民本思想卻古已有之。早在殷周時期便出現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我們熟知的大禹治水,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多少便能反映出當時“領導者”為滿足民眾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作出的努力。周公之時,“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懷保小民”(《尚書·無逸》)等記載也表明統治者已經開始意識到惠民、保民的重要性。春秋時期,民本思想取得更大的發展,孔子以“仁”為基礎施行“德治”。孔子推崇養民的君子之道,《論語》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到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民本思想更是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子比較明確地提出民本思想,論述了“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說,孟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成者(劉夏:《孟子民本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內涵
《史記》記載:“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毋庸置疑,子思從孔子那里繼承和發展而來的思想學說必定對孟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就不乏“民本思想”。在《孟子》一書中未提到“民本”一詞,只是“民”字出現的頻率高達190次,可見“民”在孟子政治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梁惠王》(上、下)兩篇中,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引文皆出自這兩篇。通過與君王的一問一答,孟子系統地闡發了他的民本思想。至少包含三層意思:第一,就民眾、君主及國家政權的關系而言,民眾為本,居于主要、根本的地位;國君與政權為末,處于次要、從屬的地位。第二,君主和任何國家政權都不可能離開民眾而單獨存在。第三,民眾的安居樂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和前提。
(一)民本君末
《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認為民眾才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在封建秩序中,君民關系的本質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但傳統儒家卻認為君“為民父母”。《荀子》云:“夫君道,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君主是父母,民眾是子女,大臣官吏是保姆。孟子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下》)“人民”既被奉為三寶之一,足見其重要性。可以看到,儒家學說中“民”的地位始終不斷提升,關注民生已經被提到儒家政治哲學的理論高度了。而孟子的民本君末說恰為其民本思想定下了理論基調。
(二)天從民愿
君主和國家政權不可能沒有人民的擁護而單獨存在,失去民眾,就意味著國君權位的喪失甚至國家政權的覆亡。自古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說,這就是說統治者必須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保持政權的穩定性。《孟子》引《泰誓》之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引《大誓》之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皆在于說明天從民愿的道理。孟子認為,天下是“天與之”,而天的意志又代表民的意志。因此,可以這樣來理解:天下是“民與之”。孟子舉例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欲得天下則要得民心,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興亡。
(三)載舟覆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民眾只有安居樂業,社會才能安寧,政權才能鞏固;反之,民眾如果連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他們便會動搖甚至推翻現存政權與君主的統治。孟子推行王道,深知以民為本是關鍵,理解“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皋陶謨》)。因此,為了“本固邦寧”和避免“覆舟”之險,孟子認為統治者應做到以下幾點:
1.與民同樂。孟子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與民同樂則民樂,不與民同樂則民怨。因此,君王要得到民眾的擁護,必須與民同樂。孟子進一步指出,“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站在民眾的角度為他們分憂,難么離王道政治也就不遠了。
2.制民之產。對于統治者而言,人民的生活能否得到安頓和保障,直接決定了國家政權和君王統治地位能否得到鞏固。孟子認為,首先社會生產應做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其次施行“井田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做到這兩點,就可以達到社會安定。“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民有恒產,才有恒心,就能安于生活而不思犯上作亂。
3.保民而王。孟子認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愛護百姓,推行王道,(這樣的趨勢)沒有誰能夠阻擋(王天下),也沒有他國敢來侵犯,安邦定國是推行王道的前提。第一要“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善推其所為而已。”惠民政策要澤及于民,應當將恩澤推廣于天下百姓。國君若能做到這一點,則不僅國內安定,四海之內也就不會再有戰爭。第二,國君不能嗜殺。“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百姓皆愿意歸服不嗜殺人的君主,歸服之勢就如水往低處流的趨勢一樣不可阻擋。做到這兩點,則“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這樣的國家,人民“心向往之”,還有誰會犯上作亂呢?又還有誰可以來侵犯呢?
孟子的民本思想側重于對國君提出執政建議,這同時也是孟子推行王道政治的需要。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意義遠不止于此,下面再來談談孟子民本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幾點啟示。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當代啟示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今天看來依然不過時。首先是人才選拔問題。齊宣王問:“我怎樣才能知道我的屬下不賢而辭退他呢?”孟子認為應當審慎考慮,他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國君可以征求身邊人的意見,可以征求大臣的意見,但最終還應當根據民意來決定。國家機構在選賢任能的問題上也應當參考民意,聽聽群眾的呼聲。針對近年來公務員的選拔機制,有些專家提出了創新意見,他們將運作的主要程序設為:民主推薦—考察—醞釀—決定—上報(劉迎良:《當代中國公務員選拔任用方式研究——制度選擇中的理想主義誤區》)。其中,民主推薦階段中就設有群眾推薦環節。這種方式無疑可以看成是孟子思想的現代運用,通過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式將符合條件的優秀人才選拔到公務員隊伍中來。
其次是戰爭問題。從當今一系列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來看,世界仍不太平。孟子面對武力爭霸的君侯與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以為民請命的情懷和偉岸的大丈夫氣概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認為,戰爭的勝負取決于民,民心的向背決定了孰勝孰敗。當齊宣王問是否攻取燕國時,孟子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解救人民的戰爭即正義戰爭,人民為了“避水火”,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挑著熱騰騰的米飯、帶著保溫的水壺來迎接他的軍隊。非正義戰爭則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正如美伊之戰,盡管美國贏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但也失去了民眾的信任與支持。
最后是民生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70%。近年來,國家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保障民生的關鍵,又將提高農民的素質作為富民強國的保障。這個問題早在孟子那里也提到了,他認為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樣能贏得民眾。好的政令能夠使百姓畏服,好的教育卻能得到百姓喜愛。他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政令法治治人,教育德治治心。此外,中國對于“三農”的投入比重也在逐年上升。2012年3月5日,溫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擬安排12 287億元,比上年增加1 868億元,再創新高。可見,孟子民本思想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現代生活中。總之,孟子民本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理論內涵,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時代價值。
參考文獻:
[1]李存山.儒家的民本與人權,儒家傳統與人權、民主思想[M].山東:齊魯書社,2004.
[2]孔穎達.尚書正義[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劉夏.孟子民本思想及其現實意義[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140-141.
[4]司馬遷.史記[M].崔凡芝,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6]梁啟雄.荀子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陳戌國.尚書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
[責任編輯仲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