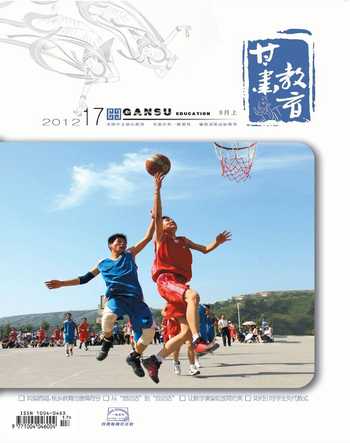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 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
周霞
〔關鍵詞〕 語文教學;對比教學;詩歌;李白;杜甫
〔中圖分類號〕 G63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463(2012)17—0057—01
回眸整個燦爛的唐詩星河,最耀眼的星辰是“瀟灑飄逸”的浪漫主義“詩仙”李白和“沉郁頓挫”的現實主義“詩圣”杜甫。探究他們生活的時代,李白生活在開元,即所謂“盛唐”時期。而杜甫所處的時代,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前后相差也不過數十年,但兩人詩風卻完全不同。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他們作品風格形成的原因,可以采用對比的方法,通過對比兩位詩人的心路歷程、出生背景、政治理想等來揭示其作品風格形成的深刻原因。
心路歷程不同
開元盛世,天寶年間的煙塵之中,謫仙人的豪放飄逸彌散在整個時空中。他行蹤飄忽,驚鴻一瞥。他在《行路難》里長嘆:“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他狂歌痛飲,仗劍遠游。盡管如此,詩人并沒有放任自流,沉溺墮落。他一生都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屢次用大鵬自比。“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盡管詩人一生際遇坎坷,仕途失意,始終未能實現他運籌帷幄、掌管經濟、建功立業的理想。但他內心世界拔俗不群,遺世獨立的特點使他繼屈原之后,開創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源流。
而在同時代,“沉郁頓挫”的詩圣杜甫一路顛沛流離,嘔心瀝血。他過著“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盡管如此,他仍將筆觸伸向腐朽的統治集團上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饑寒交迫的境況下,他也曾經想隱退做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然而他親眼看見了胡人的屠殺擄掠,并和人民一起感受國破家亡,他密切注視著戰局的變化。他的一生是“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一生,他的種種遭遇歷程注定了他風格的“沉郁頓挫。”
出生背景不同
我國古代從漢唐以來,就開始奉行“大一統”的儒家思想。對于工商走卒,在封建典制和文化意識中,乃是不恥之業。因此,商人雖然有豐厚的家資,但因為其所處社會地位較為低微,所以這樣的家庭不可能禮教森嚴,生活呆板專一。李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封建禮教不是他受的唯一的教育,還有“六甲”和“百家。”因此,他的才能和生活情趣是多方面的。“十五觀奇書,作詩凌相如”、“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劍術”。他在十五歲的翩翩年華中,是明朗健康、多才多藝的。這為他豪俠浪游、瀟灑不拘的性格打上了最初的烙印。所以他向往成就功名,卻不屑于像一般文人那樣參加科舉考試。他去國懷鄉,仗劍遠游,企圖一鳴驚人,一飛宏天,走“終南捷徑”達到自己的目的。
而杜甫則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在這樣一個世代詩書、禮教森嚴、門閥講究的家庭中,他接受的就是來自儒家的道德禮制教化。他不可能讓其他的“游”、“俠”、“道”根植于他的靈魂中,他“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這為他以后創作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政治理想不同
李白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希望通過隱居學道樹立聲譽,直上青云,而后功成身退。“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然而天真的詩人后來才明白這種供奉翰林的殊遇與他“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抱負實在相距太遠。他是點綴升平和宮廷生活的御用文人。政治理想破滅,他只有離開京都的繁花似錦,但他內心對京城的眷戀是溢于言表的。但盡管如此,詩人還是時刻注意在藝術創作和人格修養上不斷完善自己,李白的經歷說明他是一個有著“本我”型性格天真的詩人。他的創作是其“本我”天性的動機。因而,他在藝術上的追求也根本不可能同杜甫的嘔心瀝血,“語不驚人死不休”相同。他的瀟灑、飄逸是與生俱來的。
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則是通過參加封建科舉考試入仕,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他走的是讀書入仕的道路,他有著一顆傲然不群的心。政治生涯的失意及由此帶來的物質困乏使杜甫在詩歌創作上政治性加強。他不管“窮”、“達”,都要“兼濟天下”;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杜甫的一生,是艱難困苦的,也是名垂千古的。他的沉郁頓挫和憂世傷生也是發自生命本質的。
通過以上的比較充分說明了造成這兩位偉大詩人詩風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正如嚴羽在《滄浪詩話》里所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此為最貼切的評價。而我們在教學中了解了這些原因,則更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深刻內涵。
編輯:郭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