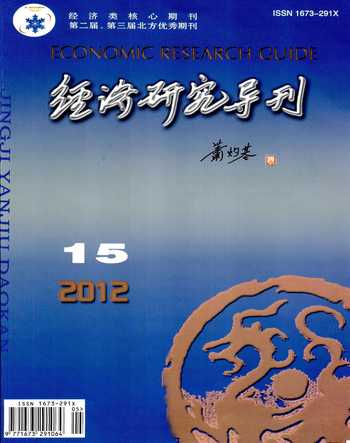新佃農理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路
林小明
摘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種變異的分成制,是中國農業制度的一大創新。它在過去三十年里有效地解決了農業生產中的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的沖突,促進了農業發展,但由于農村土地產權界定不清,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因此,農業經濟制度面臨著再次轉型。其中的諸多問題可運用張五常的新佃農理論予以解釋。
關鍵詞:分成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產權;集體理性;個人理性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043-02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是一種變通的分成制,即農戶的產品在農戶、集體和國家之間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但是,這個比例通常不是由農戶而是由各級政府和集體部門所確定的,而且確定的標準變動不居,從而致使農村居民稅負沉重[1] ,人心思變,因此,可以運用張五常的新佃農理論來解釋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一、張五常的新佃農理論
張五常認為,定額租佃制和分成租佃制是在土地產權私有條件下的兩種不同的契約形式,各自適應不同的經濟環境,本身沒有高下優劣之分。無論是從理論上而言,還是從經驗上來說,分成租佃制會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這種觀點都是一種錯覺。他的分析表明,在私人產權的條件下,無論是地主自己耕種土地,雇用農民耕種土地,還是按一個固定的地租把土地出租給他人耕種,或地主與佃農分享實際的產出,這些方式所暗含的資源配置都是相同的。換句話說,只要合約安排本身是私人產權的不同表現形式,不同的合約安排并不意味著資源使用的不同效率。但是,如果私人產權被弱化或否定產權的私有性,或者如果政府否決市場的資源配置過程,那么資源配置的效率便會不同[2]。
由此可見,張五常理論的核心是私人產權的清晰界定。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市場交易不論采取什么形式都同樣有效率,因此,各種削弱產權的行為和對市場自由競爭的干預,都會在無形中增加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不同契約的資源配置效率。
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產生及其效率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業改革的一個創舉。在此之前,中國政府組織了三次規模浩大的農業改革運動,即農業合作化、高級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運動。在今天看來,這些運動一方面不符合農業生產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有悖人民群眾的意愿,因此,它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就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運動而言,它主張一切生產資料歸集體統一支配,全體勞動者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人頭平均分配勞動產品。這種制度設計包含了一個囚徒困境:體現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尖銳沖突,因此,它的低效率運行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1976年之后,隨著人口的進一步激增,落后的生產方式所能提供的糧食與龐大的人口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全國人們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求生的本能激發了他們的創新和探索能力,他們尋求一種體制內的突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們在私下里自發地實踐了一種初級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干部與村民們約定,土地均分給各戶耕種,收割后各戶按照各自所應承擔的責任繳付國家和集體索要的利稅及相應款項,然后,剩余產品歸農戶個人所有和支配。這種制度很快便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并在全國范圍內加以迅速推廣,后來就逐漸演化成為現在規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3]。總的說來,這是一次誘致性制度變遷,是農民自下而上的創新活動及強烈的改革沖動與政府自上而下的因勢利導相結合的產物,因此,改革所遇的阻力較小,而所獲卻頗多。
自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中國農業生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78年以來,中國糧食產量穩步上升,尤其進入20世紀90年代,由于農業生產潛力的充分發揮,糧食產量更是呈現出加速度增長。為什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會促進中國農業產值的大幅度增長呢?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看,人民公社制度的生產關系根本不適應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因而它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生產關系與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適應,因而它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現階段發展。具體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界定了政府、集體和農戶之間的產權關系,使農民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地位,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決策主體,直接接受市場競爭的挑戰,自負盈虧,獨立承擔責任,最終收益與主體決策的科學性和努力程度成正相關關系。這樣一來,就消除了長期以來農業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4]。
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當前困境
農業改革三十余年來,絕大多數農民都實現了增產增收,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農民負擔過重,生活困苦的現實,日益凸顯在人們眼前。其中,最突出的莫過于所謂城鄉差距[5]。此外,由于教育產業化,醫療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廣大農民重新背負起新的三座大山:上學難、治病難和養老保險難。這就或直接或間接地加重了農村居民的稅收負擔[6]。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農民、尤其青壯年農民想方設法外出尋找門路,雖然這在一方面適應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要,但勞動力的過度外流,必然會對農業生產造成破壞。如今,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都呈現這樣的景象,即土地大面積拋荒,只有那些無法遷徙流動的老弱病殘滯留在土地上,生產嚴重萎縮。農業勞動力被大量吸納到各種非農業部門中。農林牧漁等農業表明的就業人口近年來呈下降趨勢,而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和郵電運輸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及餐飲業以及其他非農行業的就業人口則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這說明農民到非農部門就業的邊際收益要大于在農業部門的。這也間接地表明農業衰落的內在原因。
勞動力過度外流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主要農作物面積減少和產量下降以及農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全國水稻、小麥和玉米的總播種面積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處于起伏波動的狀態之中,并略微呈現出下降趨勢。與播種面積相對應的是,全國水稻、小麥和玉米的產量也很不穩定,其波動和震蕩的幅度比面積更大。從近年來統計數據來看,中國農業總產值并未減少,反而略有增加,其原因主要在于牧業、林業、漁業、副業和其他非主要糧食作物的產值有所增長所致。同時,我們還需注意到,雖然大量農業勞動力脫離土地,但主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并未顯著下降,而且糧食的總產值反而有所增長。這一方面固然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影響土地的邊際產出所致,但更重要的或許是農業經營在悄無聲息地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所致。這種轉變使得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增加。農業經營向資本密集型方向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化肥和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以及農戶所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日益增多等方面。
這種現象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即一方面農民由于土地產權界定不清[7]而不愿待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卻又舍不得扔下那塊土地,因此,他們路隔萬水千山,還是要往土地上投資。這說明農民對自己的前途命運沒有十足的信心,仍把土地作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最后一道防線。可是,相伴而生的問題是,由于農民的這種漂浮不定的處境,農業的投資和土地的改良必然會受到影響,從而影響農業的總產值,1996—2010年農業的總產值增長緩慢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四、新佃農理論對我們的啟示
為何曾經一度調動了更多群眾生產積極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現在效果不甚顯著,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滋生了農民的消極情緒?對此,可以作出如下幾個方面的解釋:
首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制度設計上存在產權界劃不清的缺陷。土地究竟歸誰所有,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現階段,中國農業實行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土地的所有權被賦予國家和集體,作為個體的農民被排除在所有權之外,但是,國家和集體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他們不可能直接出面行使所有權,而最終代表他們行使所有權的既可能是村社一級的,也可能是鄉鎮一級的基層政權,抑或是二者的聯合行為,這沒有一定之規。另外,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或以三十年,或以五十年為限,沒有永久性保障。如此一來,各級政權在很多時候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常常以收回土地所有權為手段去脅迫農民,胡亂征用農地,侵害農民的利益。這樣的暴行常常不知來自何方。在這樣的博弈之中,農民往往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佃農,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其次,為了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必須通過法律手段來保障農民在當前和未來的預期收益。張五常發現,臺灣的分成租佃制在20世紀50年代取得重大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當局把37.5%的地租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對那些采取補償性支付和合約再安排等手段來抵制法令的人,予以法律制裁。在中國當代,農業產品在農民個人與集體和國家之間的分割比例,是變動不居的,而主動權總是在國家和集體手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只有采取消極的手段抵制和發泄,沒有任何申辯和抗爭的權利。政府使財富分配的天平盡量地向自己傾斜,結果卻是財政收入并沒有顯著增加。拉弗曲線的政策含義告訴我們,稅率提高稅收的數學效應,最終會被它對生產者勞動積極性的負效應所壓倒。
最后,農業近年來的資本密集型轉型預示著,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非農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確可以反哺農業。但如何利用這一機遇,卻是問題的關鍵,尚需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秦海林.農村實際稅負變化與二元財政測度[J].財經論叢,2010,(5):31-37.
[2]張五常.佃農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0-82.
[3]蘭虹,馮濤.路徑依賴的作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與演進[J].當代經濟科學,2002,(2):8-28.
[4]陳愛娟,方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產生及其內在缺陷的經濟學分析[J].江蘇社會科學,2004,(4):69-72.
[5]汪守軍.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再認識[J].改革與戰略,2006,(4):37-39.
[6]秦海林.二元經濟中的二元財政測度與分解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7,(1):7-12.
[7]何一鳴,羅必良.產權管制、制度行為與經濟績效——來自中國農業經濟體制轉軌的證據(1958—2005年)[J].中國農村經濟,
2010,(10):4-15.
[責任編輯 劉嬌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