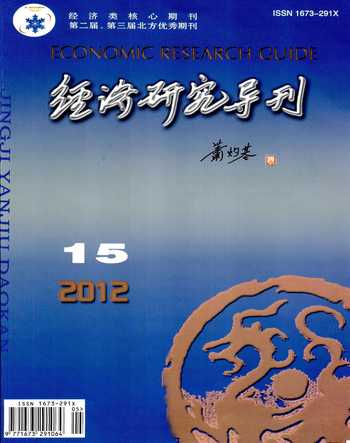從對(duì)人類中心論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的哲學(xué)批判看馬克思自然觀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李愛華,孫曉艷
摘要:國內(nèi)面對(duì)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形成的“人類中心論”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本質(zhì)上都是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學(xué)化的解讀。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完成了對(duì)作為“人類中心論”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之本質(zhì)的理性形而上學(xué)的清算,在本體論上確認(rèn)了歷史與自然的統(tǒng)一,在此基礎(chǔ)上的生態(tài)思想,才對(duì)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關(guān)鍵詞:人類中心主義;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生態(tài)危機(jī);自然
中圖分類號(hào):A8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文章編號(hào):1673-291X(2012)15-0223-03
怎樣處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當(dāng)前全人類所必須予以解決的最基本問題。20世紀(jì)后期,隨著人類社會(huì)進(jìn)入工業(yè)社會(huì)以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遭到愈來愈嚴(yán)重的破壞,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作為人類與大自然矛盾沖突的一種后果,開始凸顯出它對(duì)人類的嚴(yán)重威脅。人們已清醒的意識(shí)到,克服生態(tài)危機(jī),除了依賴經(jīng)濟(jì)和法律手段,還必須有理論支持。國內(nèi)在研究西方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兩種生態(tài)理論,“人類中心論”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①這兩種理論對(duì)研究和解決中國的生態(tài)問題有著積極的指導(dǎo)和借鑒意義,但是筆者認(rèn)為,這兩種理論都是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學(xué)化的解讀,對(duì)解決當(dāng)代生態(tài)問題不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境域?qū)Α叭祟愔行恼摗钡恼軐W(xué)批判
本文在廣義上,把舊人類中心主義、新人類中心主義和國內(nèi)新近提出的人類中心觀點(diǎn)統(tǒng)稱為“人類中心論”。之所以作此歸統(tǒng),是因?yàn)閹渍叩墓餐举|(zhì)乃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學(xué)。
西方近代形而上學(xué)的基本建制是主—客二元關(guān)系型。這是由西方近代哲學(xué)兩大流派共同創(chuàng)立的。經(jīng)驗(yàn)論的開創(chuàng)者培根首先提出了“知識(shí)就是力量”的口號(hào),主張通過對(duì)自然秩序、自然規(guī)律的認(rèn)識(shí)來獲得支配自然的力量。唯理論之父笛卡兒則以“我思”確立了主體對(duì)作為客體的自然的終極裁判權(quán)。前者使自然作為客體向人敞開,后者則使人作為主體登場(chǎng),并最終確立了其對(duì)于自然客體的至尊權(quán)威。這種主—客對(duì)抗的關(guān)系型作為西方形而上學(xué)的基本建制,實(shí)質(zhì)是確立了人征服自然的強(qiáng)勢(shì)態(tài)度,這正是后來人類中心論的濫觴。
新舊人類中心主義的概念,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哲學(xué)家布賴恩·諾頓(Bryan Norton)對(duì)“強(qiáng)式人類中心主義”(舊人類中心主義)和“弱式人類中心主義”(新人類中心主義)的區(qū)分,前者是“僅從人的感情偏好、感性意愿出發(fā),一味縱容和姑息人們那種把大自然視為滿足人的感性偏好的原料倉的掠奪性的開發(fā)方式”;后者是“從理性偏好出發(fā),理性偏好是一種經(jīng)過審慎的理智思考后才表達(dá)出來的欲望或需要,它不僅能滿足人的偏好,而且能根據(jù)一定的世界觀對(duì)這種偏好本身的合理性進(jìn)行評(píng)判,這就使得它能夠?qū)δ欠N一味掠奪大自然的行為提出批評(píng),從而從源頭上防止人們對(duì)大自然的隨意破壞”[1]。舊人類中心主義在它的時(shí)代對(duì)于突破以神為中心的宗教統(tǒng)治是有積極意義的,它讓人類發(fā)現(xiàn)了自己,充分展示了主體的力量,從此人類不再是被動(dòng)的接受自然的支配,有利于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但是這種主體性后來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對(duì)它的過分強(qiáng)調(diào)進(jìn)一步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緊張關(guān)系,引起了人類發(fā)展中更深層次的矛盾,即人與環(huán)境的矛盾,進(jìn)一步破壞了人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這種轉(zhuǎn)變根源于舊人類中心主義在本體論上對(duì)人類與宇宙萬物的中心與從屬、征服與被奴役的關(guān)系的確認(rèn),它也由此成為當(dāng)代生存危機(jī)的深層根源。新人類中心主義是在對(duì)前者批判的基礎(chǔ)上提出來的,也稱為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新人類中心主義主張應(yīng)從歷史觀和價(jià)值論的意義上來研究人類中心主義,而不再從本體論、認(rèn)識(shí)論意義上來使用這一概念。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人類整體利益和需要。在價(jià)值觀層面對(duì)“合理性評(píng)價(jià)”的引入,實(shí)質(zhì)是以理性對(duì)人類依據(jù)感性偏好隨意破壞大自然的行為作出限制,避免了前者僅強(qiáng)調(diào)人作為感性欲望主體的片面性主張。理性的限制的確有助于緩解人對(duì)自然無所顧忌的掠奪,但不能從根本上使生態(tài)危機(jī)得到解決。因?yàn)闊o論是感性的偏好,還是理性的偏好,終究是人的偏好,通過協(xié)調(diào)人的感性與理性,以感性與理性達(dá)到“和諧”的人去善待自然,仍然保留了人對(duì)自然先驗(yàn)的優(yōu)先權(quán)。這仍然沒有脫離近代形而上學(xué)之主體性哲學(xué)的窠臼。
國內(nèi)學(xué)界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基礎(chǔ)上提出的“人類中心”觀點(diǎn),否認(rèn)了一般存在論意義上“中心”的存在,這無疑是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的超越。那么,“人類中心”如果不是在存在論意義上的中心,它將在何種意義上成立呢?中國政法大學(xué)的李德順教授認(rèn)為,所謂“人類中心”的真實(shí)含義,只能是“人是人類全部活動(dòng)和思考的中心”,“人是人的世界的中心,人是人自己的中心”。這一定位的實(shí)質(zhì)是:盡管在事實(shí)領(lǐng)域,包括人在內(nèi)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成為中心,但在價(jià)值領(lǐng)域,人是必須居于最高的、主導(dǎo)的地位的。這種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基于這樣一種基本觀念:人類中心可以拋開現(xiàn)實(shí)世界,而在價(jià)值觀的領(lǐng)域獨(dú)立成立。筆者認(rèn)為,價(jià)值觀作為人對(duì)世界和自身的總體看法、目標(biāo)和理想,固然具有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獨(dú)立性,然而這種獨(dú)立性終究是相對(duì)的,以人本身為目的、尺度、標(biāo)準(zhǔn)和根據(jù)的實(shí)現(xiàn)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就是作為社會(huì)、歷史和自然相統(tǒng)一的外在世界的辯證運(yùn)動(dòng)。誠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沒有人感性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人的直觀能力也不可能存在,遑論人的價(jià)值觀念的成立。所以,馬克思批判費(fèi)爾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論的領(lǐng)域內(nèi)”[2],因?yàn)樗吹降闹皇窃诟星榉秶鷥?nèi)抽象的人,而全然不考慮人所處的社會(huì)聯(lián)系、生活條件等因素所構(gòu)筑的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系統(tǒng)。同樣,剝離了“世界存在與事實(shí)”(作為人的實(shí)踐活動(dòng),而非作為抽象的事實(shí)描述)的價(jià)值概念,也只是在理論領(lǐng)域的自圓其說,它仍然是形而上學(xué)的,實(shí)際上重返了費(fèi)爾巴哈。因而即便在所謂“應(yīng)然”的意義上,“人類中心”也是在現(xiàn)實(shí)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提這樣的舊形而上學(xué)概念,在今天根本沒有什么現(xiàn)實(shí)意義。
二、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境域?qū)Α碍h(huán)境倫理學(xué)”的批判
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潮興起于20世紀(jì)70年代,依照其立論基點(diǎn)的不同大致可分為生命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前者認(rèn)為所有生命個(gè)體都有維護(hù)自己生存的道德優(yōu)先性,因此主張把道德關(guān)心的對(duì)象擴(kuò)展到整個(gè)生命界。后者依據(jù)萊奧波爾德在《大地倫理》(1949)中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則“當(dāng)一事物有助于保護(hù)生命共同體的完整、穩(wěn)定和美時(shí),就是正當(dāng)?shù)模环粗褪清e(cuò)誤的”,認(rèn)為應(yīng)把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整體和整個(gè)生態(tài)過程都當(dāng)成道德關(guān)心的對(duì)象。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潮的興起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zhàn)和批判起過積極作用,它批判了人類是宇宙中心的論點(diǎn),批判了人類只圖自身利益而征服自然的利己動(dòng)機(jī),批評(píng)了人類過于自信的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作為唯一發(fā)展目標(biāo)的經(jīng)濟(jì)主義、消費(fèi)主義和人道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觀對(duì)于人類道德完善和道德實(shí)踐都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non-anthropocentrism)思潮中,環(huán)境倫理學(xué)居于主流[3]。① 按照多數(shù)學(xué)者的說法,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是指研究人與自然的道德關(guān)系和受人與自然關(guān)系影響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guān)系的應(yīng)用倫理學(xué)科。但是,這門學(xué)科在短短的歷史中已陷于實(shí)踐和理論的尷尬境地。這是其在理論上的片面性和烏托邦色彩以及實(shí)踐中的信仰主義特征共同導(dǎo)致的結(jié)果。從理論上講,倫理是指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huì)相互關(guān)系時(shí)應(yīng)遵循的道理和準(zhǔn)則。其主體是人,客體也是人及與人相關(guān)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倫理學(xué)將“自然、生態(tài)”當(dāng)做倫理主體來看待,這雖然對(duì)克服人類中心主義有積極意義,但是,本身卻違反了倫理學(xué)的基本原則。以生命或生態(tài)為中心,將生命和生態(tài)提高到超越人類的高度,單純強(qiáng)調(diào)自然、生態(tài)的利益而弱化人類的利益,力圖將人類消融在自然之中,雖然有著高遠(yuǎn)的境界和浪漫的情懷,卻忽視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與自然關(guān)系背后的人與人及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忽視了不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同社會(huì)地位、不同文化所帶來的人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理解的差異。這些現(xiàn)實(shí)情境上的差異,使現(xiàn)代人的價(jià)值理念在當(dāng)前時(shí)代在一定范圍內(nèi)還具有正當(dāng)性和自我更新的彈性,然而,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卻對(duì)此采取斷然否定的態(tài)度,拒絕考慮這種現(xiàn)實(shí),這使其不僅在理論上陷入困境,在實(shí)踐中也難以施展。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目前在實(shí)質(zhì)上還只是作為激進(jìn)環(huán)境主義運(yùn)動(dò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在少數(shù)組織范圍內(nèi)被遵奉,難以對(duì)主流社會(huì)的環(huán)境決策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性影響。
總而言之,《中國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研究二十年》對(duì)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具有根本意義: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是“傳統(tǒng)倫理學(xué)在環(huán)境問題上的應(yīng)用,它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只是把環(huán)境、生態(tài)、自然當(dāng)做人對(duì)人履行道德義務(wù)的中介;如果說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倫理學(xué)還必須關(guān)注基于環(huán)境上的人的義務(wù)、基于自然可持續(xù)利用上的當(dāng)代人對(duì)后代人的義務(wù),而這恰是傳統(tǒng)倫理學(xué)所忽略的地方”。這一評(píng)價(jià),一方面指出了其理論與實(shí)踐上的烏托邦和信仰主義特征,另一方面肯定了其把自然生態(tài)原則引入倫理領(lǐng)域的積極意義。
三、人與自然在實(shí)踐關(guān)系中的和諧共生——馬克思自然觀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人類中心主義與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的共通之處在于,二者都是以“中心化”為基本的思維方式。而中心化正是形而上學(xué)的根本特征。海德格爾把形而上學(xué)的本質(zhì)概況為“超越”之思、“根據(jù)”之思、“人本”之思、“存在者”之思,由此可以歸結(jié)出形而上學(xué)的根本標(biāo)志——為世界設(shè)定一個(gè)終極根據(jù)。在西方哲學(xué)中,無論是第一原則、邏各斯、神,還是先驗(yàn)理念、絕對(duì)精神,都是為世界設(shè)立的終極根據(jù)。“中心”作為世界的“公分母”,把作為其分子的一切事物不能與之通約的部分都無情切除。人類中心意味著,凡是不符合人類利益的“自然”,就要被犧牲掉;生態(tài)或生命中心同樣意味著,當(dāng)人類的利益與自然利益發(fā)生矛盾時(shí),人類的利益也要被放棄。可見,建基于形而上學(xué)的“中心化”思維模式之上的生態(tài)觀,不可能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在實(shí)踐中對(du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只能是破壞性的,這意味著對(duì)人類也終將是毀滅性的。因此,“去中心化”即超越形而上學(xué)、回歸生活世界,是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和諧生態(tài)觀的根本要求。
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使命不斷激發(fā)著哲學(xué)家的焦慮。然而,“中心”雄踞千年的歷史向我們宣告了“去中心化”而可持續(xù)發(fā)展之道路何等艱難,人類中心主義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盡管都難逃其臼,但是不可否認(rèn)其都是在這條道路上的一次(片面化的)嘗試。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次革命性變革,從對(duì)資本主義時(shí)代之形成的深刻理解中揚(yáng)棄了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產(chǎn)生存在論新視閾,以此確認(rèn)了生活世界本身之實(shí)踐批判的超邏輯性質(zhì):感性意識(shí)的解放與革命。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之建基的“實(shí)踐”概念,把人與自然共同納入在實(shí)踐關(guān)系中的感性存在,取消了人與自然作為“主體—客體”的抽象對(duì)立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的抽象“中心”。馬克思以感性存在為基礎(chǔ)對(duì)歷史與自然的統(tǒng)一所做的本體論論證,是馬克思生態(tài)思想的哲學(xué)根基,由此構(gòu)成了對(duì)上述形而上學(xué)生態(tài)觀的超越,從而使人與自然可持續(xù)的和諧發(fā)展成為可能。
首先,自然不是作為任人宰割的抽象客體,而是“現(xiàn)實(shí)的自然”,即“歷史的自然”。馬克思是在與抽象的自然界的對(duì)立中,來說明現(xiàn)實(shí)的自然界的。他在《巴黎手稿》中寫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duì)人說來也是無……正像自然界曾經(jīng)被思維者禁錮在他的絕對(duì)觀念、思想物這種對(duì)他本身說來也是隱秘的和不可思議的形式中一樣,現(xiàn)在,當(dāng)他把自然界從自身釋放出去時(shí),他實(shí)際上從自身釋放出去的只是這個(gè)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3]可見,抽象的自然界絕非現(xiàn)實(shí)的自然界。對(duì)馬克思而言,“現(xiàn)實(shí)的自然”即“歷史的自然”——“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huì)的生產(chǎn)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xiàn)實(shí)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yè)——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類學(xué)的自然界。”[4] 這表明,自然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不能與人相分離,自然是在與人的相互關(guān)系中生成著的存在,“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duì)人說來也是無。”[5]
其次,人不是作為自然統(tǒng)治者的抽象主體,而是“對(duì)象性關(guān)系中的主體性”。 “人靠自然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表現(xiàn)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lián)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身體相聯(lián)系,因?yàn)槿耸亲匀唤绲囊徊糠帧!盵5]這段話表明:第一,自然界是人類的無機(jī)身體,人類依賴自然而生存,破壞自然就是破壞人和社會(huì)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基礎(chǔ)。第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應(yīng)把人看做“自然存在”、并且是“活生生的自然存在”、“活動(dòng)的自然存在”[5]。所以,“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dòng)的自然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duì)象性的存在物,和動(dòng)植物一樣,是受動(dòng)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duì)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duì)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這對(duì)象是引起他需要的對(duì)象,是表現(xiàn)和確證他的本質(zhì)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duì)象。”[5]總之,自然本質(zhì)上是人的生命活動(dòng)的表現(xiàn),人作為“對(duì)象性活動(dòng)中的主體性”而存在。
概而言之,人通過實(shí)踐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對(duì)象性存在的活動(dòng),乃是一個(gè)歷史過程。這個(gè)歷史過程,既是人的產(chǎn)生過程,也是現(xiàn)實(shí)的自然界的生成過程。這兩個(gè)過程是同一個(gè)過程。馬克思以實(shí)踐即感性活動(dòng)為基礎(chǔ),把人作為“對(duì)象化活動(dòng)的主體性”,把自然作為對(duì)象化活動(dòng)中的“現(xiàn)實(shí)的自然界”, 從本體論上確認(rèn)了歷史與自然的辯證統(tǒng)一。并通過這一論證實(shí)現(xiàn)了人與自然在實(shí)踐關(guān)系中的和諧共生,使可持續(xù)發(fā)展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完成了對(duì)作為“人類中心論”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之本質(zhì)的理性形而上學(xué)的清算,在此基礎(chǔ)上的生態(tài)批判思想,才對(duì)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具有真正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單樺.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權(quán)利觀轉(zhuǎn)變[J].理論前沿,2006,(9).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G]//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陳劍瀾.非人類中心主義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批判[J].哲學(xué)門,2006,(4):178-179.
[4]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5.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178.[責(zé)任編輯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