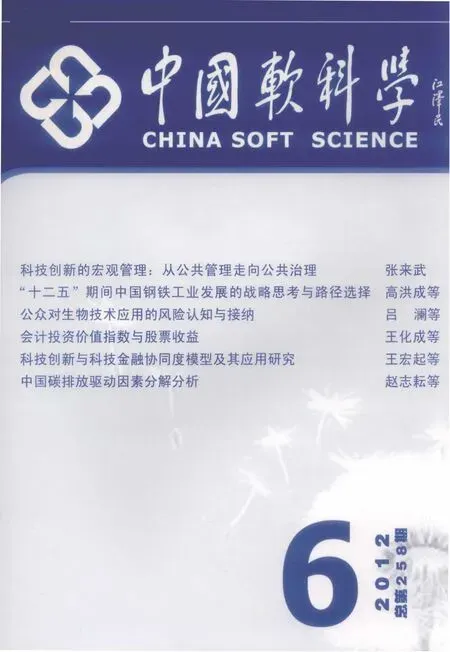技術進步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實證研究
李凱杰,曲如曉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此同時,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量也在不斷增加,據荷蘭環境評估局(MNP)的評估報告,2006年中國碳排放達到62億噸,超過美國,成為第一排放國,2007年為67.2億噸,占世界總排放的24.3%,增量占世界總增量的近60%,中國受到的國際減排壓力與日俱增[1],減少碳排放成為中國未來的主要任務之一。技術進步是影響碳排放的關鍵因素,其對碳排放的影響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技術進步可以促進能源強度降低減少碳排放[2],同時也會推動經濟增長增加碳排放,那么中國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影響如何?是否有效地減少了碳排放?本文將嘗試對此做出回答。分析技術進步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有助于深入了解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為科學制定減排政策提供依據,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早期的技術進步對環境影響的研究多是在假定技術進步外生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框架內展開。Nordhaus(1977)[3]分析了外生技術進步下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之后于1993年[4]構建了氣候變化和經濟的動態綜合模型(DICE),用于分析經濟增長和環境的相互關系。但是部分研究表明,技術進步不是外生的,多數技術進步是內生的,受需求的影響[5]。Newell等(1999)[6]發現能源價格對技術進步有顯著影響,證實了內生技術進步的存在。之后涌現了大量分析內生技術進步對環境影響的研究。Goulder和 Schneider(1999)[7]利用可計算模擬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了存在引致技術進步時減排成本的變化,發現存在引致技術進步時,實現減排目標所需成本更低。Nordhaus(2002)[8]構建了R&DICE模型比較了引致技術進步與要素替代對碳排放的影響,發現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要小于要素替代彈性的影響。Buonanno等(2003)[9]在RICE模型中引入了技術進步,發現技術進步可以顯著降低減排成本,Popp(2004)[10]構建了 ENTICE 模型,即考慮內生技術進步的DICE模型,發現忽略引致技術進步會高估減排成本。Grimaud 和 Rouge(2008)[11]、Acemoglu等(2010)[12]以及 Smulders 和 Di Maria(2011)[13]均考慮了內生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影響中國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彭水軍等(2006)[14]把與環境相關的科研課題經費投入和政府財政科研支出作為技術進步變量,發現技術進步導致中國污染排放增加。徐國泉等(2006)[15]、王鋒等(2010)[16]運用類似的指數分解法分析了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結論有所不同,前者認為經濟發展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成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后者發現中國碳排放增長的主要正向驅動因素為人均GDP、交通工具數量、人口總量、經濟結構和家庭平均年收入;主要負向驅動因素為生產部門能源強度、交通工具平均運輸線路長度、居民生活能源強度。孫建衛等(2010)[17]采用Laspeyres指數分解方法對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及其變化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GDP增長是碳排放總量增加的主要動力,技術進步因素是碳排放量降低的主導因素。林伯強等(2010)[18]運用協整的方法研究了現階段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發現能源消費強度、能源強度和城市化水平會影響中國碳排放。
綜上,國內外已有很多關于技術進步與碳排放關系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多是從靜態角度考察當期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未分析技術進步的累積影響。實際中,技術進步從新技術產生到技術的擴散和應用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僅從靜態角度分析會低估技術進步的作用,不能揭示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長期影響及動態關系。基于此,本文構建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應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模型)分析技術進步和中國碳排放的長短期動態關系。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
(一)研究方法
Kaya(1989)[19]通過因式分解的方法將溫室氣體排放與人口、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和單位能源消費聯系起來,提出了Kaya恒等式。本文在Kaya等式基礎上建立如下非結構方程來考察碳排放和技術進步的長期均衡關系:

其中,CEt、ISt、TFPt、PGt和 Pt分別表示碳排放量、能源結構碳強度、技術進步、人均GDP和人口。
通過上述非結構化方程,可以得到向量自回歸模型。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是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能較好地對具有相關性的時間序列系統進行預測,并可考察擾動項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其表達式如下:

其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向量,p是滯后階數,T是樣本個數。A1,…,Ap和B是待估計系數矩陣,εt是隨機擾動向量,為零均值獨立同分布的白噪聲向量。如果所選取的變量是平穩時間序列,可以直接使用VAR模型估計;但如果變量不平穩,就要考慮采用VEC模型,VEC模型要求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可以認為VEC模型是含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多用于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模型。
上式可以寫為:

式中每個方程的誤差項都具有平穩性,用誤差修正模型表示為:

其中,ecmt-1=β'yt-1是誤差修正項,反映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系數矩陣α反映了變量間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將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調整速度,所有作為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的系數反映各變量的短期波動對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短期變化的影響。
(二)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1)碳排放量(CEt),數據來源于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CDIAC,http://cdiac.ornl.gov/)。


(3)技術進步,用全要素生產率(TFPt)來衡量。技術進步是一個無形的變量,無法直接進行度量,目前文獻中通常采用三種指標間接度量技術進步:一是R&D投入,二是專利數量,三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統計年鑒上只有近幾年中國分省區的R&D投入數據,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沒有選取R&D投入;專利數也很難準確反映技術水平,因為某一個專利價值可能要遠遠高于其它專利的,一個專利價值可能是幾個甚至幾十個專利價值之和。最終,選取全要素生產率度量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最早由索洛[20]提出,是指要素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等導致的產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貢獻后得到的殘差,又稱索洛余值,用來反映生產者的技術水平。利用索洛余值表示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個隱含假設,所有生產者技術上都是有效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允許技術無效率的存在,因此廣泛地用于全要素生產率[21]、碳排放影子價格[22]以及能源效率[23]等估算。本文選取基于動態非參數前沿生產面的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方法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該方法是根據包含多個決策單元的平衡面板數據,應用投入產出數據,識別出技術效率最好的經營決策單位,以其為基礎構造生產前沿面,通過生產過程的實際投入或產出值與最優值的比較得出技術效率水平指數。Malmquist指數又可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DEA-Malmquist指數法的關鍵是投入和產出變量的選取。要素投入選取物質資本和勞動力兩個指標,物質資本用各地區資本存量表示,勞動力指標選擇各地區從業人口數量,產出指標用經過價格指數(1978=100)平減的地區GDP表示。勞動力和產出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新中國55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2004)》。資本存量數據借鑒張軍等(2004)[24]所采用的“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張軍等人是以1952年價格估算的各省資本存量,本文的基期為1978年,因此需要以1978年價格重新估算的各省資本存量。選取各省1978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為其初始資本存量;統計年鑒上沒有1990年之前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選取各省零售價格指數來代替;其余指標選取及估算方法均和張軍等(2004)[24]相同。將中國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①為保持口徑統一將1996年開始分離的重慶數據并入四川省,西藏則因數據缺乏不包括在樣本內。作為決策單元,采用投入導向的DEA方法,運用DEAP2.1軟件,得到全國以及各地區每年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具體結果見表1,限于篇幅,只列出了樣本期內全國各省及東、中、西部地區②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0個省自治區。的平均Malmquist生產率指數。
(4)人均GDP(PGt),反映了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其碳排放量也有所不同,用經過價格指數(1978=100)平減的實際人均GDP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5)人口(Pt),人口變化會對碳排放帶來顯著的影響,人口的增加可能會帶來碳排放量的增多,人口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本文樣本區間為1978-2008年。為避免數據的劇烈波動并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各個變量數據分別取自然對數,記為:lnQt、lnISt、lnTFPt、lnPGt和 lnPt。
三、模型估計和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現代計量經濟學要求計量模型建立在變量平穩的基礎上,而現實中許多經濟變量通常不是平穩的,使用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易產生“偽回歸”問題。因此,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確定其平穩性及單整階數。常用的方法有擴展的Dichey-Fuller(ADF)和非參數的PP法,本文采用ADF檢驗,結果見表2。

表1 中國各省1978-2008的平均Malmquist指數

表2 ADF平穩性檢驗結果
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變量 lnCEt、lnISt、lnTFPt、lnPGt和 lnPt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ADF統計值都大于其相應的臨界值,表明五個變量都是非平穩的,而其相應的一階差分序列ADF統計值都小于臨界值,表明五個變量的差分序列是平穩的,即這些變量是一階單整的。
(二)協整檢驗
建立VEC模型前,首先要驗證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只有存在協整關系的變量才可以建立VEC模型。時間序列分析中,每一個序列單獨來說可能是非平穩的,但這些序列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有不隨時間變化的性質,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說明變量間是協整的,意味著這些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協整檢驗要求變量是單整變量,且單整階數相同,由上述平穩性結果知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變量,因此可以對變量進行協整關系分析。常用的協整檢驗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回歸殘差的協整檢驗和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協整檢驗。前者適合對兩變量的模型進行協整檢驗,后者適合對多變量模型的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極大似然法對多變量系統進行協整檢驗。
在進行Johansen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的合理滯后階數。滯后階數的選擇既要有足夠的滯后項,又要有足夠的自由度,使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又能消除誤差項的自相關。通過估計一個無約束VAR模型并使用赤池(AIC)和施瓦茨(SC)信息準則來選取最優的滯后階數,通過多次檢驗發現,當滯后階數為2時,AIC和SC值最小,再結合LR統計量,最終選定無約束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基于VAR模型的協整檢驗滯后期是無約束VAR模型一階差分變量的滯后期,因此確定協整檢驗的滯后期為1。根據數據特點,選取序列有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檢驗形式。協整檢驗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在不存在協整方程和最多存在一個協整方程的原假設下,跡統計量值均大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而其他假設條件下的跡統計量都小于5%水平的臨界值,所以接受變量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的假設,最大特征值檢驗也得到同樣的結論,綜上,變量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根據經過標準化后的協整系數,選取一個能準確反映變量間關系的協整方程,其表達式為(括號內為標準差):


表3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表4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結果
其中ecm為誤差項,需要對誤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協整關系的平穩性,ADF檢驗結果顯示,誤差項的ADF統計量值為-3.28,小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2.97,所以其在5%顯著水平下是平穩的,即協整關系平穩有效。
協整方程表明,1978-2008年間,中國的碳排放總量與能源結構碳強度、技術進步、人均GDP和人口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所有變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過t統計量檢驗,且模型具有較高的擬合度。從協整結果來看,長期內,能源結構碳強度、人均GDP和人口同中國碳排放呈正相關關系,技術進步同碳排放呈負相關關系。能源結構碳強度、人均GDP和人口每變動1個百分點,分別帶動碳排放同向變動4.53、2.07和1.55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每變動1個百分點,帶動碳排放相反方向變動1.75個百分點。這和國內大部分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能源結構碳強度、人均GDP和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碳排放,技術進步則減少了碳排放。
(三)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如果系統變量不平穩,不能直接利用VAR模型來考察變量之間的關系。VEC模型可以較好地克服VAR的不足,系統變量不平穩且存在協整關系時可以通過建立VEC模型來考察變量間的相互調整速率及短期互動影響并觀察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在進行VEC檢驗之前,先對模型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通過檢驗,發現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單位圓內或圓上,表明VEC模型穩定,模型得出的結果也較為可靠。表4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
由表4估計結果可知,模型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說明模型具備誤差修正機制,進一步證明了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表5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短期來看,(1)人均GDP、能源結構強度和人口的增加都會增加碳排放,且效果顯著;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會降低碳排放,但t統計量的值不顯著,即短期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效果不明顯,這可能是因為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要考慮其時滯和積累問題,在短時期內很難將技術進步快速轉變為碳排放的減少。(2)人均GDP受到能源結構的影響,其他變量的影響不顯著。因為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階段,主要的燃料仍以化石燃料為主,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能源的大量消費,所以能源結構的提高(即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在整個能源結構中比重上升)推動了人均GDP的增加;技術對人均GDP影響不顯著是因為創新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且創新后的擴散和應用卻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體現出來,短期內技術進步對人均GDP的作用還不能顯現出來。(3)人均GDP增加會推動技術進步。隨著經濟發展,對創新的要求越來越高,會推動一國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碳排放、能源結構強度和人口的變化對技術沒有顯著影響。
(四)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
協整關系的存在并不表明變量之間必然存在有經濟意義的因果關系,需要用Granger因果檢驗來考察變量間的因果關系。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變量必須是平穩的,直接對時間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會造成偽回歸,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中的變量具有平穩性特征,從而保證了Granger因果檢驗的有效性。因此可以采用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檢驗來考察變量間的短期關系,結果見表5。
由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知,短期內人均GDP和能源結構強度是碳排放的單向Granger原因,而技術進步則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這也驗證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得出來的結論,即短期內人均GDP和能源結構強度對碳排放有顯著影響,人均GDP和能源結構強度的提高會帶來碳排放的增加,而技術進步對碳排放沒有顯著影響。人均GDP的提高是技術進步的Granger原因,這也符合誤差修正模型所得出的結論,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技術進步。
四、結論與進一步工作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數測算了中國1978-2008的技術進步,在VEC模型的基礎上檢驗了中國碳排放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長短期關系,根據上述分析,得到了以下結論:
(1)中國碳排放和能源結構強度、人均GDP、技術進步和人口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能源結構強度、人均GDP和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碳排放的增加,而技術進步則會減少碳排放,按影響大小依次為:能源結構強度、人均GDP、技術進步和人口。
(2)短期內,能源結構強度和人均GDP對碳排放有顯著影響,而技術進步并不能顯著減少碳排放。能源結構強度反應了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一旦能源結構改變,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費量中比重減少,清潔能源比重增加,碳排放量會明顯減少;人均GDP反映了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所需的資源消耗不斷增加,碳排放量顯著增加;技術進步短期內對碳排放沒有顯著影響,是因為新技術研發后的擴散使用需要較長時間,技術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才能起到減排的作用。
未來經濟增長仍是中國的主要任務,由此帶來的碳排放會不斷增加,因此只能通過改善能源結構和技術進步來減少碳排放。短期內,可以通過降低化石燃料消費比例,改善能源結構減少碳排放。長期內,技術進步是減少碳排放有效的手段,應加大技術研發投入,推動中國的節能技術與低碳技術的發展,加快技術的擴散速度,盡快將新能源技術投入到使用,減少碳排放。
本文采取了時間序列分析方法,且由于數據的可得性,樣本區間只有31年,因此僅考慮了經濟增長、能源結構、人口和技術進步的因素,而實際影響碳排放變化的因素還包括產業結構、地區差異以及政策差異等因素,未來研究可以利用面板數據控制更多的影響碳排放的因素,進一步地分析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影響。
[1]林伯強,蔣竺均.中國二氧化碳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預測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27-36.
[2]王淑新,何元慶,王學定.中國低碳經濟演進分析:基于能源強度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10,(9):25-32.
[3]Nordhaus W D.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The Case of Carbon Dioxi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341-346.
[4]Nordhaus W D.Optimal Greenhouse-Gas Reduction and Tax Policy in the DICE mode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313-317.
[5]Grubb M,Chapuis T,Ha-Duong M.The Economics of Changing Course:Implications of Adaptability and Inertia for Optimal Climate Policy[J].Energy Policy,1995,(23):417-431.
[6]Newell R G,Jaffe A B,Stavins R N.The 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cal Chang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941-975.
[7]Goulder L H,Schneider S H.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2Emissions Abatement[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1999,(21):211-253.
[8]Nordhaus W D.Modeling Induced Innovation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J].in Grubler,A.;N.Nakicenovic,and Nordhaus,W.D.ed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ress,Washington,DC.2002.
[9]Buonanno P,Carraro C,Galeotti M.Endogenous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Costs of Kyoto[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3,(25):11-34.
[10]Popp D.ENTICE: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DICE Model of Global Warming[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4,(48):742-768.
[11]Grimaud A,Rouge L.Environment,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Policy[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8,(41):439-463.
[12]Acemoglu D,Aghion P,Bursztyn L,Hemous D.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R].NBER Working Paper,No.15451,2010.
[13]Smulders S,Di Maria C.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under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R].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Climate Change Workshop Working Paper,2011.
[14]彭水軍,賴明勇,包 群.環境、貿易與經濟增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15]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實證分析:1995-2004[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6,(6):158-161.
[16]王 鋒,吳麗華,楊 超.中國經濟發展中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研究[J].經濟研究,2010,(2):123-135.
[17]孫建衛,趙榮欽,黃賢金,等.1995-2005年中國碳排放核算及其因素分解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10,(8):1284-1293.
[18]林伯強,劉希穎.中國城市化階段的碳排放:影響因素和減排策略[J].經濟研究,2010,(8):66-78.
[19]Kaya Y.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GNP Growth:Interpret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R].Presentation to the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Response Strategies Working Group,IPCC,Paris,l989.
[20]Solow R 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21]傅曉霞,吳利學.前沿分析方法在中國經濟增長核算中的適用性[J].世界經濟,2007,(7):56-66.
[22]劉明磊,朱 磊,范 英.我國省級碳排放績效評價及邊際減排成本估計:基于非參數距離函數方法[J].中國軟科學,2011,(3):106-114.
[23]孫廣生,楊先明,黃 祎.中國工業行業的能源效率(1987-2005)——變化趨勢、節能潛力與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11):29-39.
[24]張 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