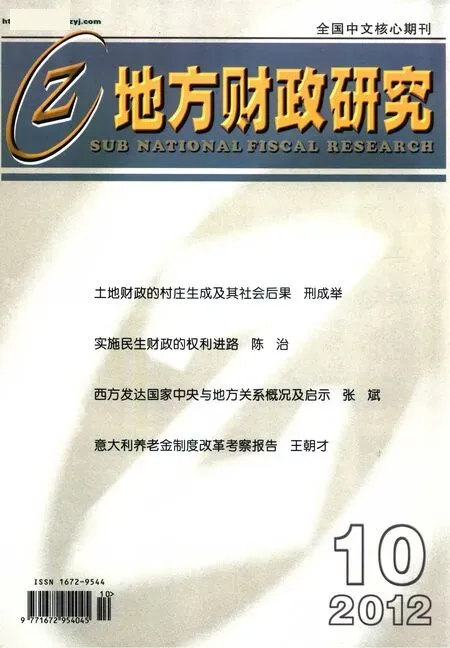土地財(cái)政形成的博弈分析
辛 波 于淑俐 楊海山
(山東工商學(xué)院,煙臺 264005)
在土地財(cái)政的形成過程中,存在著四個(gè)相關(guān)利益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fā)商以及居民。不同的利益主體有著不同的選擇和戰(zhàn)略,這些選擇構(gòu)成了復(fù)雜的博弈關(guān)系。我們試圖對各個(gè)利益主體的收益函數(shù)、戰(zhàn)略選擇以及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過程和博弈結(jié)果展開分析,以揭示土地財(cái)政形成的演化過程和必然性。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
(一)基本假定
我們假設(shè)中央政府有兩個(gè)目標(biāo),一個(gè)是經(jīng)濟(jì)增長,另一個(gè)是分配公平①實(shí)際上就是平等與效率。尋求二者的統(tǒng)一一直是中央政府的目標(biāo)。。這兩個(gè)目標(biāo)體現(xiàn)在財(cái)政制度上,就是分權(quán)與集權(quán)的選擇。如果中央政府更加傾向于經(jīng)濟(jì)增長,則傾向于財(cái)政中的分權(quán),即在財(cái)政分配上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權(quán)力,以刺激其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的積極性;如果中央政府傾向于分配公平,則傾向于財(cái)政中的集權(quán),通過集權(quán),中央政府將掌握更大的財(cái)政收入比例,并通過轉(zhuǎn)移支付來解決各地區(qū)的發(fā)展不平衡問題。

地方政府也有兩個(gè)目標(biāo),一個(gè)是控制收入的最大化,一個(gè)是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前者的含義是:在給定中央政府選擇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何通過選擇來實(shí)現(xiàn)自己所能控制收入(財(cái)政收入或其它非財(cái)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的含義是:如何通過選擇,實(shí)現(xiàn)最大政績以得到提拔,或者在提拔無希望的情況下,得到一定的“權(quán)力租金”,以此來彌補(bǔ)未被提拔的遺憾。當(dāng)然,政績的顯著與否和租金的大小實(shí)際上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政績越明顯,提拔的可能性就越大,權(quán)力就越大,可能得到的租金就越多②這并不意味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道德水平之間的差別,而是基于委托代理關(guān)系而形成的必然邏輯。。表1就展示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目標(biāo)結(jié)構(gòu)。
(二)博弈過程
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我們做了一些如下的假設(shè):
第一,假設(shè)中央政府的財(cái)政收入是FINC,地方政府的財(cái)政收入是FINL,且財(cái)政收入全部由稅收收入構(gòu)成,沒有其它收入①這當(dāng)然不符合現(xiàn)實(shí),但不妨礙問題的討論。,則中央政府的財(cái)政收入與地方的財(cái)政收入之和為FIN,于是有:FIN=FINC+FINL。假如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則中央政府財(cái)政收入為FINC1;地方政府財(cái)政收入為FINL1。假如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則中央政府財(cái)政收入為FINC2;地方政府財(cái)政收入為FINL2。另外,再假設(shè)分權(quán)后,地方經(jīng)濟(jì)活力增強(qiáng),則 FINC1+FINL1>FINC2+FINL2以及 FINC2>FINL1。
第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jiān)督有兩種,一種是觀察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一種是觀察其行為是否為短期行為。如果中央政府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不努力工作,則要實(shí)施一定的懲罰,設(shè)為T1;如果中央政府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的行為僅僅是短期行為,例如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隨意拍賣、轉(zhuǎn)讓土地,則要實(shí)施一定的懲罰,設(shè)為T2。但是,中央政府實(shí)施監(jiān)督要花費(fèi)一定的成本,設(shè)為C。當(dāng)然,如果中央政府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努力且合法地工作,則要提供一定的獎(jiǎng)勵(lì),設(shè)為K,可以理解為地方政府官員獲得提升。
第三,如果地方政府努力工作,會使地方財(cái)政收入增加,設(shè)增加量為X;同時(shí)也會帶來中央財(cái)政收入的增加,設(shè)增加量為Y(中央只有嚴(yán)格監(jiān)督才能得到這個(gè)Y);如果地方政府尋求地方財(cái)政之外的收入,例如土地財(cái)政,則設(shè)為LAN②設(shè)這個(gè)收入只能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增加,同時(shí)帶來權(quán)力租金,但不影響中央政府收入。,但要面臨中央政府的監(jiān)督。
在這些假設(shè)前提下,我們將博弈過程分為多個(gè)階段:第一階段開始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的時(shí)期;第二階段則開始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高的時(shí)期;依次類推。
1.第一階段的博弈。設(shè)中央政府先動,戰(zhàn)略為“分權(quán)”與“集權(quán)”;地方政府后動,戰(zhàn)略為“努力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努力但不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以及“不努力”,可以簡稱為努力合理(設(shè)為A)、努力不合理(設(shè)為B)、不努力(設(shè)為C)。中央政府再次進(jìn)行選擇,戰(zhàn)略為“嚴(yán)格監(jiān)督”和“松散監(jiān)督”。其中,地方政府“努力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可以理解為地方政府不依靠土地財(cái)政而是正常地發(fā)展經(jīng)濟(jì),“努力但不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可以理解為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cái)政來發(fā)展經(jīng)濟(jì)。決策樹如圖1。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A,即努力合理地工作,則如果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Y-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X+K。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X(因?yàn)橹醒胝缮⒈O(jiān)督,并沒有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在努力合理地工作,因此,地方政府也得不到獎(jiǎng)勵(lì))。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B,即努力但不合理地工作,則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LAN-T2。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LAN。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C,即不努力且不合理地工作,則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T1。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1,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1。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A,即努力合理地工作,則如果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K(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權(quán)限太小,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增加更多的財(cái)政收入)。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B,則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LAN-T2。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LAN。
如果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地方政府選擇C,則中央政府嚴(yán)格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C,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T1。如果中央政府松散監(jiān)督,中央政府的支付是FINC2,地方政府的支付是FINL2。
從圖1看,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時(shí)的最大收益是FINC1+Y-C或FINC1,選擇集權(quán)時(shí)的最大收益是FINC2,如果 FINC2大于 FINC1+Y-C 或 FINC1,中央政府應(yīng)該選擇集權(quán)。但中央政府不會這樣選擇。這是因?yàn)椋旱谝唬捎诖藭r(shí)處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的時(shí)期,中央政府考慮的是如何增強(qiáng)地方經(jīng)濟(jì)的活力,首要目標(biāo)是經(jīng)濟(jì)增長,或財(cái)政總收入的增長,即FINC1+FINL1>FINC2+FINL2。在此前提下,即使 FINC2大于FINC1+Y-C,中央政府也會選擇分權(quán)。第二,同樣,由于此時(shí)經(jīng)濟(jì)發(fā)展較為落后,地方政府的努力也會帶來較顯著的經(jīng)濟(jì)增長,因此,Y大于FINC2-FINC1+C。故中央政府必然會選擇分權(quán)。
給定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地方政府會考慮中央政府是否會嚴(yán)格監(jiān)督,實(shí)際上這取決于Y與C的比較,如果Y大于C,則中央政府會嚴(yán)格監(jiān)督,如果Y小于C,則中央政府會松散監(jiān)督。因?yàn)閅大于C,中央政府會嚴(yán)格監(jiān)督。
給定中央政府選擇嚴(yán)格監(jiān)督,地方政府會比較FINL1+X+K與FINL1+LAN-T2的大小,實(shí)際上就是X+K是否大于LAN-T2。如果地方政府的合理努力能夠很快收到回報(bào),或中央政府的懲罰力度較大,則地方政府會選擇努力且合理地工作。基于同樣的理由,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的時(shí)期或在經(jīng)濟(jì)起飛的初期,地方政府的合理努力能夠很快收到回報(bào),因此,地方政府會選擇A。這樣,最后的均衡結(jié)果就是[(分權(quán),嚴(yán)格監(jiān)督),努力合理]。
2.第二階段的博弈。仍然設(shè)中央政府先動,戰(zhàn)略為“分權(quán)”與“集權(quán)”。地方政府后動,戰(zhàn)略為“努力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努力但不合理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以及“不努力”。決策樹見圖2。
圖2與圖1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于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后其財(cái)政收入變?yōu)榱薋INC3,且FINC3要高于FINC1和FINC1+Y-C。原因在于: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高后,中央政府發(fā)現(xiàn)僅僅追求效率將會帶來各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不平衡,并最終將導(dǎo)致區(qū)域間的的貧富差距,于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點(diǎn)會從追求經(jīng)濟(jì)增長轉(zhuǎn)化到對社會分配的調(diào)整。而要做到分配公平,中央政府就必須要擁有比例較大的財(cái)政能力,于是中央政府會選擇集權(quán)。

給定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地方政府就會考慮中央政府是否會嚴(yán)格監(jiān)督。實(shí)際上,在中央政府收緊財(cái)權(quán)后,地方政府就會在合理增加地方財(cái)政收入方面失去信心,其原因在于即使地方政府增加了稅收,其大部分比例也會被中央政府拿走。或者說,地方政府的合理努力不會帶來Y的大幅度增加,因此Y<C,即中央政府在自己選擇集權(quán)后的最高支付是FINC3,即松散監(jiān)督。
給定中央政府選擇松散監(jiān)督,則地方政府會選擇B。這樣,最后的均衡結(jié)果就是[(集權(quán),松散監(jiān)督),努力不合理]。
3.第三階段的博弈。在第三階段,中央政府經(jīng)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經(jīng)驗(yàn),即如果中央收緊財(cái)權(quán),地方政府會尋找其它的收入來源,例如土地財(cái)政,由此會導(dǎo)致很多問題,例如房地產(chǎn)泡沫增加、耕地減少、經(jīng)濟(jì)缺乏長期發(fā)展動力等。于是在第三階段,中央政府又會考慮放松財(cái)權(quán),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財(cái)權(quán),避免形成地方政府對土地財(cái)政的依賴。見圖3。
在這一階段,由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高,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后的最高財(cái)政收入為FINC4+Y-C(此時(shí),Y要大于C)遠(yuǎn)遠(yuǎn)高于原先的FINC1,同時(shí),F(xiàn)INC4+Y-C也會高于FINC3。鑒于以前的經(jīng)驗(yàn),中央政府會對依賴土地財(cái)政的地方政府以較嚴(yán)格的監(jiān)督,在這種前提下,地方政府會選擇A,即努力合理。這樣,最后的均衡結(jié)果就是[(分權(quán),嚴(yán)格監(jiān)督),努力合理]。

4.第四階段及之后的博弈。可以想象,在第四階段,中央政府會選擇一定程度的集權(quán)和一定程度的松散管理,地方政府會選擇努力但不合理的行為。第五階段,中央政府會選擇一定程度的分權(quán)和一定程度的嚴(yán)格管理,地方政府會選擇努力且合理的工作。依次類推:在奇數(shù)階段,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和嚴(yán)格監(jiān)督,地方政府選擇努力且合理地工作;在偶數(shù)階段,中央政府會選擇集權(quán)和松散管理,地方政府會選擇努力但不合理地工作。于是,中央政策在集權(quán)和分權(quán)之間搖擺,地方政府則在合理與不合理之間搖擺,至于是否能達(dá)到最后的均衡,要看國家經(jīng)濟(jì)的整體發(fā)展趨勢以及進(jìn)一步改革的走向。
究其根本,中央政府的選擇是基于對平等和效率的考慮,地方政府是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從邏輯上來講,這完全是委托——代理問題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在這里,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代理人,我們無法要求委托人的思想與代理人愿望相一致,也無法達(dá)到代理人的行為與委托人的要求相吻合。其實(shí),地方政府選擇努力工作已經(jīng)是一種次優(yōu)的選擇,如果地方政府選擇不努力工作,消極怠工,則會出現(xiàn)一種大家更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
以上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我國財(cái)政稅收體制改革與發(fā)展軌跡的。從歷史上來看,我國財(cái)政稅體制的改革與發(fā)展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后到1978年之前,主要實(shí)行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財(cái)政集中體制;第二階段從1978年到1993年,中央政府逐步放權(quán),實(shí)行分成和財(cái)政包干體制;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進(jìn)入第三個(gè)階段。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財(cái)政稅體制變化的路徑就是在集權(quán)——分權(quán)之間來回?fù)u擺,相信在不遠(yuǎn)的將來,還會走向分權(quán)的道路。
二、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的博弈
在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之間,也存在多階段博弈,且每個(gè)階段的博弈結(jié)果有所不同。在此,我們先做一些基本假定,然后再逐一討論。
(一)基本假定
第一,如前,設(shè)地方政府有兩個(gè)目標(biāo),一是控制收入最大化,一個(gè)是自身收益最大化。在博弈中有兩個(gè)戰(zhàn)略,一個(gè)是正常、合法地拍賣;一個(gè)是私下協(xié)商轉(zhuǎn)讓;簡稱為“拍賣、協(xié)商”。
第二,設(shè)有N個(gè)開發(fā)商,實(shí)力相當(dāng)。我們討論其中一個(gè)代表性開發(fā)商A,該開發(fā)商只有一個(gè)目標(biāo),即利潤最大化。在博弈中有兩個(gè)戰(zhàn)略,一個(gè)是尋租,一個(gè)是不尋租,即(尋租,不尋租)。
第三,設(shè)一塊土地的價(jià)值為V,如果正常拍賣,按V的價(jià)格出售。開發(fā)商得到土地后轉(zhuǎn)手賣出的價(jià)格為V1,V1-V是開發(fā)商在合法情況通過拍賣得到土地后所獲得的利潤。但由于有很多開發(fā)商在競爭這塊土地,開發(fā)商A得到土地的可能性為1/N。因此,A可能獲得的利潤為(V1-V)/N。而如果開發(fā)商選擇尋租,則尋租后協(xié)商土地價(jià)格大幅度下降為V2,V1-V2是開發(fā)商在不合法情況下所獲得的利潤。另外,尋租費(fèi)用為R。
第四,即使政府選擇拍賣,開發(fā)商A也可能有尋租行為,不過這時(shí)尋租費(fèi)用為R1,且R1小于R。
(二)博弈過程
1.第一階段的博弈。觀察表2。其中值得解釋的是地方政府的收益,該表左上角中地方政府收益為(V+R1),其含義是地方政府在得到控制收入V后,政府相關(guān)人員自身得到權(quán)力租金為R1。同樣,該圖右上角中地方政府收益為(V2+R),其含義是地方政府在得到控制收入V2后,政府相關(guān)人員自身得到權(quán)力租金為R。
如果地方政府選擇拍賣,開發(fā)商A會選擇不尋租,因?yàn)椋╒1-V)/N大于(V1-V)/N-R1。如果地方政府選擇協(xié)商,開發(fā)商A會選擇尋租,因?yàn)閂1-V2-R要大于0。
現(xiàn)在來看地方政府的選擇。如果開發(fā)商A選擇不尋租,則地方政府無疑要選擇拍賣,因?yàn)閂大于0;如果開發(fā)商A選擇尋租,地方政府選擇拍賣后的控制收入為V,租金收入為R1。如果地方政府選擇協(xié)商,則地方政府的控制收入為V1,租金收入為R,至于控制收入與租金收入如何選擇?這要看地方政府究竟如何看待這兩種收入,前者顯示的是政績,后者則可能裝進(jìn)了官員的腰包。

在實(shí)施土地財(cái)政初期,地方政府可能會更加關(guān)注政績,因?yàn)槿魏我粋€(gè)官員在開始都有一種得到上級認(rèn)可的偏好與干一番事業(yè)的沖動,于是在博弈的第一階段,地方政府一般會選擇拍賣。給定地方政府選擇拍賣,開發(fā)商就會選擇不尋租,這樣,土地市場就是比較透明的。
2.第二階段的博弈。在這一階段,各種支付與上一階段雖然沒有什么不同,但最后的均衡結(jié)果卻不一樣。隨著土地開發(fā)進(jìn)程的加快他與土地財(cái)政額度的逐漸增加,地方政府的官員會從土地出讓中感受到里面隱藏的巨大利益,于是他們可能最終無法抵抗誘惑,并使之追求的目標(biāo)從政績的提升轉(zhuǎn)向自身收入的增加。
如果地方政府選擇拍賣,開發(fā)商A會選擇不尋租,因?yàn)椋╒1-V)/N大于(V1-V)/N-R1。如果地方政府選擇協(xié)商,開發(fā)商A會選擇尋租,因?yàn)閂1-V2-R要大于0。
如果開發(fā)商A選擇不尋租,則地方政府會選擇拍賣,因?yàn)閂大于0。如果開發(fā)商A選擇尋租,地方政府在拍賣后協(xié)商中間選擇,最終會選擇協(xié)商。
這里存在兩個(gè)納什均衡,一個(gè)是(不尋租,拍賣),一個(gè)是(尋租,協(xié)商),那么必然存在一個(gè)混合戰(zhàn)略納什均衡。
設(shè)地方政府選擇拍賣土地的概率為P,選擇協(xié)商轉(zhuǎn)讓土地的概率為1-P。開發(fā)商A選擇尋租的概率為q,選擇不尋租的概率為1-q。
則開發(fā)商選擇尋租后的預(yù)期收益是:P·[(V1-V)/N-R1]+(1-P)·(V1-V2-R);開發(fā)商選擇不尋租后的預(yù)期收益是:P·(V1-V)/N;二者應(yīng)該相等。即:
P·[(V1-V)/N-R1]+(1-P)·(V1-V2-R)=P·(V1-V)/N
解這個(gè)方程,得到:

可見,當(dāng)R越大即租金越大時(shí),1-P即地方政府選擇協(xié)商的概率越大。租金越小時(shí),地方政府選擇協(xié)商的概率越小。R1越大時(shí),地方政府選擇拍賣土地的概率越小,R1越小時(shí),地方政府選擇拍賣土地的概率越大。
同樣,也可以解出開發(fā)商選擇尋租的概率。地方政府拍賣的預(yù)期收益是:q·(V+R1)+(1-q)·V。
地方政府協(xié)商的預(yù)期收益是:q·(V2+R)。
于是有,q·(V+R1)+(1-q)·V=q·(V2+R)。
解這個(gè)方程,得到:

可以發(fā)現(xiàn),V2越小,則開發(fā)商越愿意尋租,因?yàn)閂2越小,利潤就越高;V2越大,開發(fā)商尋租概率越小。
3.第三階段及以后的博弈。在第三階段,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已經(jīng)不再關(guān)心政績,而僅僅關(guān)心自己的租金收入,見表3。如果開發(fā)商選擇尋租,則地方政府直接選擇協(xié)商,因?yàn)镽大于R1;如果開發(fā)商選擇不尋租,則地方政府對于拍賣和協(xié)商是無所謂的,開發(fā)商的支付不變。
看起來結(jié)果仍然是兩個(gè)納什均衡,一個(gè)是(不尋租,拍賣),一個(gè)是(尋租,協(xié)商)。但是,實(shí)際上只會有一個(gè)納什均衡。因?yàn)榈胤秸畷靼祝绻_發(fā)商不尋租,則自己的收益是0,因此,地方政府會希望開發(fā)商尋租,那么如何讓開發(fā)商堅(jiān)持尋租呢?地方政府會堅(jiān)持協(xié)商,這樣就可以得到R,于是(尋租,協(xié)商)就成為唯一的占優(yōu)均衡。

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修改自己的支付矩陣,將(不尋租,拍賣)后自己的收益改變?yōu)樨?fù)值,其含義是通過某些途徑暗示不愿公開拍賣,這樣(尋租,協(xié)商)就會變?yōu)槲ㄒ坏恼純?yōu)均衡。見表4。第三階段之后的博弈無須再做過多的分析,因?yàn)榻Y(jié)果都是一樣的。開發(fā)商總是選擇尋租,地方政府總是選擇協(xié)商,雙方皆大歡喜。

三、開發(fā)商與居民的博弈
我們首先分析居民,居民的購房需求有兩種:一種是剛性需求,即無論價(jià)格高低,總是需要購買,例如結(jié)婚需要等方面,這樣,剛性的需求曲線為一條垂線,即需求價(jià)格彈性為零。另外一種是投資需求,即買房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投資,這種需求有一個(gè)特點(diǎn),即價(jià)格越高,購買需求越大,因此,其需求曲線為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結(jié)合兩種需求,目前我國的房地產(chǎn)需求曲線應(yīng)該與一般需求曲線不同,為向上傾斜的曲線。實(shí)際上,只要房價(jià)上漲,剛性需求也可以轉(zhuǎn)化為投資需求,從而使得需求曲線向上傾斜。見圖4。

在圖4中,居民在特定情況下的需求曲線為D,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的供給曲線為S,兩者相交在E點(diǎn)。但是這個(gè)均衡是不穩(wěn)定的,當(dāng)價(jià)格高于P0時(shí),需求大于供給,價(jià)格會進(jìn)一步提高。價(jià)格低于P0時(shí),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以成本為由不再提供產(chǎn)量。于是價(jià)格總是處于上漲之中。開發(fā)商有兩個(gè)戰(zhàn)略,一個(gè)是高價(jià)出售,一個(gè)是低價(jià)出售,高價(jià)出售的利潤為Y,低價(jià)出售的利潤為Y1,Y大于Y1。假設(shè)居民在購買到高價(jià)格的房產(chǎn)后轉(zhuǎn)手賣出,獲得利潤X,購買到低價(jià)格的房產(chǎn)后轉(zhuǎn)手賣出,獲得利潤X1,X1大于X。如果居民不購買,則開發(fā)商利潤為-Z(要還銀行貸款或利息)。開發(fā)商與居民博弈的得益矩陣如表5所示。
如果居民決定購買,則開發(fā)商決定高價(jià)出售,獲得利潤為Y;如果居民決定不購買,則開發(fā)商高價(jià)出售和低價(jià)格出售無差別,都是零。

如果開發(fā)商決定高價(jià)出售,則居民決定購買,獲得利潤為X;如果開發(fā)商決定低價(jià)出售,則居民決定購買,獲得利潤為X1。也就是說,無論開發(fā)商的價(jià)格如何,居民都會購買。給定居民會購買,開發(fā)商自然選擇高價(jià)出售,(購買,高價(jià)格)成為唯一的占優(yōu)策略均衡。這可能也是房產(chǎn)價(jià)格不斷提高的重要原因。
四、結(jié)論
根據(jù)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土地財(cái)政產(chǎn)生的基本邏輯,即: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地方政府財(cái)權(quán)減少——轉(zhuǎn)向土地財(cái)政——協(xié)商轉(zhuǎn)讓土地——房地產(chǎn)商人高價(jià)賣出——居民追漲,這也是近些年中國房地產(chǎ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真實(shí)寫照。
具體來說,就是:第一,土地財(cái)政的形成與中央政府目標(biāo)的變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標(biāo)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當(dāng)中央政府選擇分權(quán)時(shí),地方政府財(cái)政自主權(quán)較大,此時(shí)不會形成土地財(cái)政;當(dāng)中央政府選擇集權(quán)時(shí),地方政府財(cái)政自主權(quán)較小,此時(shí)較易形成土地財(cái)政。第二,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之間的博弈取決于地方政府官員的選擇,如果他們更加關(guān)注政績,則會形成較好的土地拍賣機(jī)制;如果他們更加關(guān)注自身收入或租金收入,則容易形成不透明的土地市場。第三,在居民與開發(fā)商之間,由于居民具有較為特殊的房地產(chǎn)需求曲線,即需求曲線向上傾斜,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dǎo)致房地產(chǎn)價(jià)格的不斷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