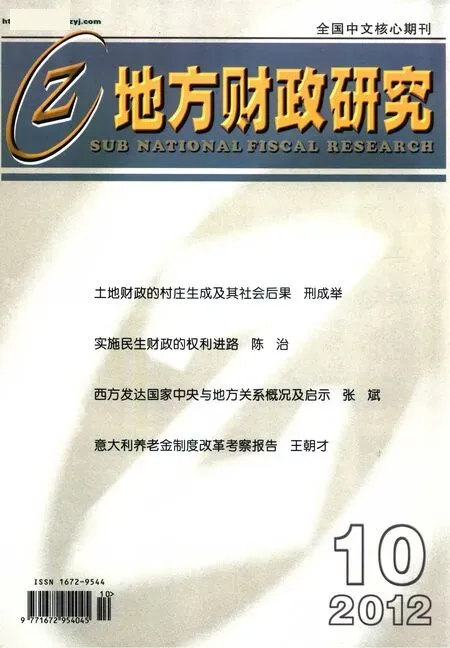我國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財政原因探析
李雅軒 諶業美
(1.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1100;2.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193)
2006年8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社會保障費用不落實的不得批準征地”。在此情形下,各省份紛紛出臺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截至2009年9月末,內地除了青海和西藏外的29個省份均出臺或轉發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實施辦法,12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中新網,2009)。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城市化的一項重要配套措施(楊翠迎,2004),階段性地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問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征地矛盾、推進了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陳頤,2000)。
然而,各地政府在出臺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時,卻有意增加失地農民和集體的出資比例、限定保障人數、減少保障內容、降低保障標準等。盧元海(2009)指出,僅靠地方政府的一次性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和新增財政收入,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難以保證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和長遠生計。經費是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重要支撐,在現行征地補償標準遠低于足額支付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所需費用的情況下,中央對地方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和地方政府自身財力直接影響著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保障水平。
一、各省份被征地農民社保政策及其財政原因
(一)保障模式的選擇及其財政原因

各地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模式大體可以分為四類,詳見表1。模式一是指納入城鎮社會保險后,被征地農民的保障內容、保障標準都將參照城鎮職工執行。該模式標準固定,操作空間小,財政支出大,因此較少省份采用模式一;模式二要求將被征地農民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國務院2009年正式出臺《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2009年之前,我國各地的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基本沒有建立,且被征地農民在就業和收入方面與有地農民有很大區別,僅將其納入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很難接受,因此模式二也較少被采用;模式三要求將被征地農民納入小城鎮社會保險制度。該模式的有效實施必須以發達的經濟條件為前提,財政支出大,因此目前只有上海市采用;模式四屬于新生事物,保障內容等與之相關事項缺乏固定標準,采用這種模式,各省份自主空間大,能自主設定各出資主體的出資比例、保障對象認定標準、保障內容和保障標準等,即此種模式的采用為降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財政支出預留了足夠空間,因此各地采用最多的正是模式四。
(二)社保資金來源的設定及其財政原因
《關于做好被征地農民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一般由“個人、集體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資:村集體和個人承擔部分,分別從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中列支和抵繳;政府補貼部分從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中列支。
表2對28個省份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情況進行了匯總,由表2可見:2005年以前,各地政府出資比例均不超過被征地農民社保資金的30%,社保資金以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為主;2005年以后,各地政府出資比例有所增加,大多超過30%,但仍以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為主要來源,且社保資金全部來源于被征土地的相關收益。
中央規定,征地時必須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各省份只能照此執行,但為了減少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很多省份將被征地農民和集體的出資比例設得較高。同時,政策梳理時還發現,有些地區會從財政拿出部分資金用于被征地農民社保資金補貼,只是其所占比例小;還有些地區建立了風險準備金或調劑金制度,設立政府儲備基金,但補充資金明顯不足。
(三)保障對象的認定及其財政原因
很多省份在認定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對象時,會在《通知》基礎上附加一些限定條件。例如,天津、海南和北京規定人均耕地面積必須低于某一標準或低于所在地區平均人均耕地面積的某一比例;新疆和寧夏地區規定,社會保障只針對城市規劃區內的被征地農民;遼寧規定只針對農轉非被征地農民等。通過這些限定條件,地方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參保門檻,導致更多的失地農民被擋在社會保障之外。符合參保條件的被征地農民減少了,各省份對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也就相應減少了。
(四)保障內容的設定及其財政原因
“三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問題是失地農民最為憂心的焦點所在,其中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險種。在統計的28個省份中,只有約29%的省份同時建立了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約71%的省份僅對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做出了安排(見表3)。

“社保實施方案”是征地審批的要件,但社會保障內容越完善,建立的經濟成本越高,因此很多省份在建立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時,只涉及了基本養老保險,對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險進行了回避,這樣既滿足了國家征地報批的要求,又能減少政府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的財政投入。
(五)繳費方式和保障待遇標準的設定及其財政原因
大多數省份的繳費都采取一次支付、從征地補償費直接劃入社保賬戶的方式繳納15年的社保費用。實踐中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待遇則主要分為四種情況:采用“模式四”的地區,保障水平主要參照當地低保水平確定;采用“模式二”的地區,保障標準參照農保;采用其他模式的大部分地區,待遇水平主要參照城鎮企業職工待遇水平的最低檔;還有一些省份的保障水平與繳費掛鉤,依照計發系數、平均余命確定。
失地農民是有別于一般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勢群體,其文化素質較低,因此其失地后難以獲得穩定收入,加上失地農民主觀上并不愿意支付社保費,因此為了預防“拒繳”情況的大量發生,導致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收支失衡,給政府帶來財政風險,很多省份采用一次直接劃撥的繳費方式。同樣,我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為了減少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使社保支出與社保繳費盡量平衡,防范新的財政負擔,各地政府大都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待遇限定在較低水平。
二、地方政府對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與地方財政的關系及其原因
大多數省份在出臺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時,都會采取某種或幾種方式減少財政支出,像新疆這種財政收入較少的省份表現得尤為突出,政府明確的出資比例為零;但像福建、重慶這類財政收入較多的省份,政府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的投資比例卻很高,能達到70%-80%(見表2),而且有些省份會主動從財政拿出資金用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補貼,只是數額很小而已。這些都說明政府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的資金投入量與政府的財政收入是有著密切關系的。因此,本部分將對“政府人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與人均財政收入”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分析。
各省份被征地農民社保政策出臺年份并不統一,因此本部分只選取表2中2008年出臺政策的有關省份(四川、湖南、河南、云南、廣西、寧夏、重慶、江西和福建),將其2008年政府人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與其人均財政收入做一個簡單的相關性分析。人均財政收入涉及數據均來自2008年統計公報,政府人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按照“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5×政府出資百分比”的簡單方式計算得出。結果見圖1,從R2=0.81可知,政府人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與政府人均財政收入相關性較大,且地方人均財政收入越高,政府人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費出資額也越大。

由此可以得出,政府采取不同方式壓縮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財政支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投入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可見,只要財政收入足夠充裕,地方政府是愿意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投入足夠資金的。
本文認為當下限制政府對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出資的財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通過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央集中了大量地方財政收入,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比由“正四六”變為“倒四六”——地方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接近80%迅速下降到1994年的45%左右,此后十多年一直在這個水平徘徊;同時,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劃分比例卻呈下降趨勢——地方財政支出比重,1993年約為72%,2011年則升至85%左右,詳見圖2,即分稅制沒有根本改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格局;圖3顯示,分稅制后,地方財政收支由財政盈余轉為財政赤字,且赤字差額逐年遞增,即分稅制加劇了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平衡。
二是近些年,被征地農民數量迅速增長,2007年,我國被征地農民數量累計大約4500萬人左右,根據我國城鎮化發展速度以及建設用地需求預測,到2020年,我國新增被征地農民大約4200萬人左右,預計到2030年,我國被征地農民數量累計超過1億人(2007,何平),為了化解大量失地農民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潛在危機,中央政府出臺政策強制地方政府建立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但中央政府對此只有政策支持,并無固定的財政投入,在沒有中央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大量失地農民的保障,將極大地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加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等。
三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是統一的,其中一項出現缺口時,就要用另一項的收入加以彌補,因此各地政府在出臺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時,都努力實現征地補償費和社保費的收支平衡。

這些都很好地說明了圖1得出的結論:財政收入少的省份,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投入越多,其財政壓力就越大,所以其在社會保障中的投入較少;反之,財政收入多的省份,對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也就更多。
三、小結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府可以被當作一個“經營空間的企業”——通過為其行政邊界里的經濟人(居民、企業)提供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法律保障、公共安全等),獲取經濟收益。政府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獲得收益。第一是對行政轄區內的經濟活動收稅;第二是直接出讓配套了各種基礎設施的土地。一般來講,稅收主要用于經常性的公共服務,如社會保障、法律、治安、教育、消防、基礎設施維護等;土地收益則用于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如七通一平。因此,地方財政收入的多少直接決定其在公共服務上的投入,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關系失地農民的生存,是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地政府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中的資金投入量自然會受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制約。分稅制改革已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中央卻企圖在零財政投入的情況下,僅倚靠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便解決大量失地農民的社保問題。地方政府為防止財政赤字差額進一步擴大,只得采取各種方式降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財政支出,由此引發大量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問題,形成這種中央與地方博弈的局面。
〔1〕中國新聞網.中國1300多萬被征地農民納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EB/OL].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09/12-24/2037067.shtml,2009年 12月 24日,2011年12月24日.
〔2〕楊翠迎.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分析與評價——以浙江省 10 個市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4(5):61-68.
〔3〕陳頤.論“以土地換社保”[J].學海,2000(3):95-99.
〔4〕盧海元.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的基本情況與政策取向[J].社會保障研究,2009(1):10-20.
〔5〕李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文獻綜述及對策探討[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0,21(8):128-130.
〔6〕何平.我國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J].中國勞動,2007(1):10-14.